作者:楊·阿斯曼(Jan Assmann)
譯者:北公爵
版本: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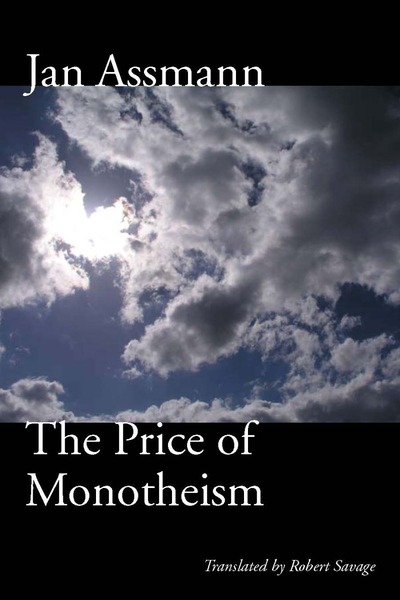
譯者序
《一神教的代價》是阿斯曼在 2003 年以德文出版的著作,2010 年由羅伯特·薩維奇(Robert Savage)將其翻譯成英文,並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此中文譯文基於薩維奇的英文版本。
《一神教的代價》承接了作者的前一本著作《埃及人摩西》,雖然作者本人聲稱它不是對後者的延續,但是由於主題上的連續性,所以先讀《摩西》會有助於理解作者在這本書提出的觀點。而《摩西》一書也回應了弗洛伊德的《摩西與一神教》,它既綜述了與之相關的歷史背景,也回顧了相關研究的歷史。
正如阿斯曼所說的,在《摩西與一神教》中,弗洛伊德的歷史考據雖然站不住腳,但是時隔二十年後,他還是再次引起了對一個問題的廣泛關注,那就是,猶太教的真正起源到底是不是在埃及?這也是我關注阿斯曼的作品的主要動機。在《埃及人摩西》一書中我沒有找到任何實證歷史方面的線索,所以我並沒有興趣翻譯它,但是在這本書中,作者輕描淡寫地提及了埃赫那頓宗教改革時期,往來於埃及與巴勒斯坦地區的書信,這些出土的文物被稱為“阿瑪納書信”,它證明了巴勒斯坦地區積極地參與了埃赫那頓的激進的一神教改革。另外我也注意到,《劍橋聖經史》也提到了阿瑪納書信。


以我對華人世界的了解,完全可以預見到最終有人會來竊取我翻譯這本書的果實,甚至直接拿去作為自己的功勞出版也不足為奇,因為這種事情曾經發生在我身上。所以,我現在想簡單介紹下翻譯這本書的時間線,我從 2023 年 10 月開始翻譯這部作品,在 2024 年 1 月下旬完成了初稿,後來在 3 月初得知原作者阿斯曼先生在 2 月下旬與世長辭的消息。我對初稿並不滿意,但是由於缺少動力,於是擱置了一段時間,直到 4 月初才開始審編,這次幾乎是重新翻譯,而且我也意識到初稿的翻譯中,我對有些英文原文的理解有誤。我準備公開的第一版的最終定稿是在今天,2024 年 5 月 25 日。
如果讀者有翻譯上的建議,我非常歡迎討論,此博客有我的郵箱地址。
目錄
引言
第一章:摩西的宗教區隔與寬容問題
《聖經·舊約》背後有幾個宗教?
什麽是真理?
不寬容、暴力、和排他
異己的建構:宗教諷刺
第二章:一神教 —— 反什麽的反宗教?
一神教較之多神教
埃赫那頓與摩西:埃及的一神教與《聖經》的一神教
一神論作為反宇宙神論
一神論作為政治神學:倫理、正義、自由
“異教”世界的法律和道德,以及一神教對正義的神學化
第三章:記憶的沖突:偶像崇拜與毀像主義之間
麻風病人的傳說與埃及的阿瑪納創傷
毀像主義與偶像崇拜
上古神學與摩西區隔的廢除
摩西區隔的反撲與異教研究的興起
第四章: 弗洛伊德與智性的進步
猶太選項與希臘選項
一神教的創傷:分析闡釋學與記憶歷史
禁止造像是一種智性進步
第五章:一神教的心理歷史影響
經文轉向”:從儀式到經典
走進“地下室”
內在自我的構建
反宗教與原罪的概念
結論
譯者註
譯後記
引言
在遠古歷史的某個階段——專家們提出的年代範圍從青銅時代晚期到古典晚期——發生了一次轉變,它對我們當今世界的影響比任何政治動盪都更深遠。 它就是從“多神論”宗教到“一神論”宗教的轉變,從儀式宗教到經典宗教,從文化特定宗教到普世宗教,簡而言之,是從“原始”宗教到“次生”宗教,後者——至少在它們自己看來——並不是通過演化過程從原始宗教中產生的,而是通過革命性的行動背離了它們。
“原始”宗教和“次生”宗教之間的區別可以追溯到宗教學者狄奧·桑德梅爾(Theo Sundermeier) 的一個提議。 在跨越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時間長河裡,原始宗教在單一文化、單一社會以及通常也是單一語言中進行歷史演變,並最終與之緊密交織在一起。這類宗教包括埃及、巴比倫和古希臘古羅馬等等的祭祀和神靈的世界。與此相反,次生宗教是在神的啟示下被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它們建立在原始宗教的基礎上,並通過譴責它們為異教、偶像崇拜和迷信來區別於後者。 所有次生宗教,同時也是經典宗教、普世宗教(除了佛教可能是個例外)和一神教,都將原始宗教視為異教。
儘管在“融合性文化適應”(syncretistic acculturation)的過程中,這些“次生”宗教可能同化了許多“原始”宗教的元素,但在它們的自我理解中,它們仍將其視作“對抗性文化適應”(antagonistic acculturation),並且對與其所宣稱的真理(或正統)不相容的事物有著強烈的意見。這種轉變不僅在神學上產生影響(因為它改變了人們思考神性的方式);它還具有政治維度(因為它將文化特定的宗教轉變為普世宗教)。宗教,從一個與社會的制度、語言和文化條件深深綁定的系統——一個不僅與文化相輔相成,而且幾乎同生一體的系統——變成了一個自主系統——一個可以從這些條件中解放自己、超越所有政治和種族界線並移植到其他文化的系統。這種轉變至少也具有媒體技術的層面。如果沒有書寫的發明和隨之而來的將啟示的真理編纂成書,從儀式宗教到經典宗教的轉變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一神論宗教,再加上佛教,都以一套神聖經典為基礎。此外,還有進一步的心理歷史層面,尤其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引起我們注意的方面:轉向一神教,以其倫理要求、對內在自我的強調以及其作為“父權制宗教”的特徵,帶來了新的心智和新的靈性,它們決定性地塑造了西方人的形象。最後,這種轉變涉及世界觀的改變,即人們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方式。這種轉變在以下這兩個方面得到了最徹底的研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的“軸心時代”概念將這一轉變解釋為通向超越的突破,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理性化概念則將其解釋為一個祛魅的過程。
我用“摩西區隔”的概念來指稱這種轉變中最重要的方面。對我來說,關鍵似乎不在於唯一神和眾多神之間的區別,而在於宗教中的真假區別,真神和假神、真教義和假教義、知識和無知、信仰和不信之間的區別。這種區隔被劃定出來,然後又被抹去,只會在以後的某些場合中以加劇或減輕的形式重新被引入。因此,與其說是一個具有明確的“之前”和“之後”的單一“一神教轉變”,不如稱其為“一神教時刻”同樣恰當,在這些時刻中,摩西區隔被嚴厲地劃定——包括: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條誡命、金牛犢的故事、尼希米時代強制終止外族通婚、基督教晚期對古代異教神廟的摧毀——然後在決定宗教生活日常實踐的不可避免的妥協中被淡化甚至幾乎被遺忘。這一點在第一章中更詳細的討論。現在,我想集中討論時間性的問題。摩西區隔不是一夜之間徹底改變世界的歷史事件,而是一種規範性觀念,它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地發揮著改變世界的影響。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談論“一神教轉變”。它在任何可定義的方式上都與摩西隔不重合,當然也與任何歷史人物“摩西”的傳記細節無關。 在這種轉變之前,只有隨著時間演變而來的部落崇拜和“多神論”崇拜以及民族宗教。之後,出現了一些新的宗教,它們與這些歷史演變而來的宗教競爭並逐漸取代它們,其中一些在今天的各種文化中仍然存在。這些新興宗教都是一神教、經典宗教(或啟示宗教)和普世宗教,儘管有人可能會對佛教是否真正一神教、猶太教是否真正普世宗教,甚至基督教是否真正一神教和經典宗教提出爭議。所有這些宗教的共同點在於它們都強調真理的概念。它們都建立在真理宗教與謬誤宗教的區別之上,宣揚一種與其他真理不互補的真理,反而將所有傳統或競爭的真理歸入謬誤的範疇。這種排他性的真理是真正的新事物,其新穎、排他性和排斥性的特點在傳播和編纂的方式上清晰地反映出來。它聲稱已經一勞永逸地(將真理)啟示給人類,因為沒有任何純人類創造的道路可以從無數代人積累的經驗中達到這個目標;它被存放在神聖經典的書籍中,因為沒有祭祀或儀式能夠在悠悠歲月中保存這一啟示的真理。這些新興的或次生的宗教從這種真理揭示世界的力量中汲取對抗性的能量,使它們能夠辨別和譴責謬誤,並在一個由規範、教條、行為準則和救贖教義構成的規範性構建中闡述真理。正是從這種對抗性的能量以及對與真理不相容事物的明確認知中,真理獲得了它的深度、清晰的輪廓以及指導和指揮行動的能力。因此,也許用“反宗教”這個術語來概括這些新興宗教更為恰當。對於這些宗教,也僅對於這些宗教而言,其宣揚的真理才伴隨著一個要與之鬥爭的敵人。只有它們才知道異端和異教徒、錯誤的教義、派別、迷信、偶像崇拜、魔法、無知、不信、異端,以及其他任何用來指稱它們譴責、迫害和禁止的、被視為謬誤表現的術語。
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詳盡描述我剛才提到的從多神教到一神教、從原始宗教到次生宗教的轉變,而是想通過面對一些批評性的回應和反對意見來澄清和進一步闡明我在拙著《埃及人摩西》一書中提出的觀點。然而,我的意圖並不是增補或為那本書辯護,更不是要寫續集。相反,我想更集中、更全面地處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寫作那本書時,只在我的思維邊緣或書的邊緣地帶引起了我的關注,但是批評家對那本書的接受首先讓我意識到它們正是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和主題。文學理論教導我們區分文本的“作者意圖”和它的“意義”。作為《埃及人摩西》的作者,我親自體驗了這種區別的合理性。只有在批評家對那本書的接受中,摩西區隔的論題才出人意料地成為其語義核心和關注要點。這本書幾乎被普遍理解為對宗教批判的一種貢獻(即便不是對一神論宗教普世主義或特別是基督教的正面攻擊)。最初,我想通過聲明這不是我的意圖來為自己辯護。相反,我的出發點是要闡明西方對埃及接受歷史中一個以前不為人知的章節。文藝復興時期因重新發現《赫爾墨斯文集》、赫拉波羅的神秘象形文字書籍和羅馬方尖碑而引發的埃及熱潮廣為人知,並得到了相對深入的研究;同樣,18 世紀對埃及獅身人面像、方尖碑、金字塔和共濟會神秘主義的迷戀也如此;最重要的是,繼拿破崙的埃及遠征及其催生的《埃及志》巨著之後,19 世紀席捲歐洲的“埃及熱”。然而,17 世紀和 18 世紀圍繞“埃及的摩西”這一人物展開的插曲幾乎無人知曉,最終形成了一個大膽的猜想,即《聖經》一神教的根源在於埃及,並代表了埃及神秘學的重新編碼。我想追溯西方對埃及記憶歷史中這一新浮現的章節,從其古老起源一直到它當今的後果;也許是我被發現的興奮沖昏了頭腦,誇大了我的觀點。但從本質上說,我想嘗試進行歷史或“記憶歷史”的重建,而不是捲入神學論戰之中。
我現在認識到,這樣的辯論完全偏離了重點。這裡重要的是文本中所包含的潛在意義,而不是作者的“主觀意圖”(無論它是什麼),這種潛在意義通過不同的解讀而釋放出來,並在文本和讀者之間的互動中得以實現。順便說一下,這一觀點與《埃及人摩西》一書中的“記憶歷史”方法論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我也沒有追問過《聖經》和其他文本的主觀意圖,而只是關心它們能夠在讀者中釋放出什麼樣的語義潛力。經過長達五年的圍繞《埃及人摩西》的激烈辯論,我很感激有機會探討不同的解讀形成的不同的潛在意義。我首先想解決的,是由“摩西區隔”概念引發的各種問題。
這本書受到了兩方面的批評。有些人責備我引入了“摩西區隔”的概念,另一些人則責怪我想要廢除它。 在第一種情況下,有人反對我將一種區隔及其排他傾向強加給《聖經》宗教(如果我可以這樣概括古代以色列宗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話),因為這種區隔及其排他傾向與《聖經》宗教的本質格格不入;而在第二種情況下,相反地,人們則反對我去質疑一個構成《聖經》宗教及其所基於的所有西方價值觀的區隔。儘管這兩種反對意見截然相反,但卻都將我視為反猶太主義者:一種觀點認為“摩西區隔”的概念隱含著不容忍;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要求取消“摩西區隔”是在呼籲重返埃及,是主張多神教、泛神論和世界的再度魅化。羅爾夫·倫道夫(Rolf Rendtorff)辯稱“《聖經》中沒有‘摩西區隔’……”,因此我強加給《聖經》的是一個與《聖經》完全無關的構建。克勞斯·科赫(Klaus Koch)則堅持認為, “摩西區隔” 不過是“借用現代宗教理論的對立概念……它真的適用於本質的基本定義嗎?” 實際發生的轉變是流動的,多神教和一神教在許多方面重疊,為了分析目的而將它們截然分開,與歷史現實相悖。“摩西區隔” 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構想,沒有“真正的歷史及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作為基礎。埃里希·曾格(Erich Zenger)和格哈德·凱澤(Gerhard Kaiser)更進一步,他們認為這個構想代表著一種墮落。曾格寫道:“根據阿斯曼的說法,‘摩西區隔’簡直就是宗教和文化史的原罪。從埃及的角度來看,‘摩西區隔’似乎首次將原罪初帶到世界上。”如果說將“摩西區隔”(真理宗教與謬誤宗教之間的區隔)強加給一神教宗教在歷史上站不住腳,那麼質疑這個區隔並敦促撤銷它在神學上也是值得懷疑的。卡爾-約瑟夫·庫歇爾(Karl-Josef Kuschel)寫道:“揚·阿斯曼想用宇宙神論取代《聖經》一神論。他這樣做把自己置於他自己用‘鍊金術、卡巴拉、赫爾墨斯神秘主義、新柏拉圖主義、斯賓諾莎哲學、自然神論和泛神論’等關鍵詞描述的傳統之中。”曾格將以下“基本主張”歸因於我:即“‘摩西區隔’給世界帶來了如此多的苦難和暴力,它應該最終被廢除。人類歷史到目前為止為此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了。”
這些都是有分量的反對意見。它們並非毫無道理,正如我不得不承認的那樣,關於我書中的幾段文字,它們值得仔細審查。此外,它們觸及到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寫《埃及人摩西》時並不完全清楚。事實上,我必須承認,有一些觀點至今對我來說仍然不清楚,儘管它們與“反猶主義”無關。因此,對我來說,我要在這場辯論中發表自己的聲音,就顯得尤為重要。我絕無意用我花了數十年研究的宇宙神論取代《聖經》一神論(這正是我所繼承的智性和靈性的遺產),儘管我也知道,這類學術研究如果沒有最起碼的同情心和尊重就無法進行。
這本書不僅要回應批評家在討論、評論和信件中提出的反對意見,還要回應我多年來自己思考過的反對意見。此外,它們還概述了我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四年前提出的觀點的地方。然而,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仍然會嚴格遵循《埃及人摩西》一書的主題限制。自從這本書出版以來,我學到的任何其他知識都應該感謝我的批評者。這本書在如此多的不同學科領域都收到了評論,我覺得這是一份厚禮,尤其是因為我對大部分我冒昧涉足的領域都不熟悉,這份厚禮就更珍貴了。
第一章:摩西的宗教區隔與寬容問題
《聖經·舊約》背後有幾個宗教?
從原始宗教到次生宗教的轉變就發生在《聖經》自身的內容里。《聖經·舊約》背後不只有一種宗教,而是兩種。原始宗教與同時代的其他主要宗教幾乎沒有區別,它崇拜一位至高的神,他支配並遠超其他眾神,但並不以任何方式排斥他們,這個神創造了世界及萬物,他關心他的創造物,促進群畜與田地的豐饒,馴服各種自然之力,指引著他的子民的命運。那些被歸為“祭司”傳統和整編主線的典籍以及文本層次,主要是由這種宗教塑造而成。而次生宗教與其周邊環境的其他宗教則截然不同,它要求排他地崇拜它的獨一神,禁止制造神像,並主張一個人能否獲得神的恩寵更多地取決於他的行為是否正直和是否遵守神所賜予的——通過經文確立的——律法,而不僅僅取決於祭祀和儀式。這種宗教出現在先知書中,以及“申命”傳統線上的典籍和文本層次。如其名所示,“申命”傳統線以《摩西五經》中的《申命記》為中心。這本書充滿明顯的說教和講道精神,也激發了其他典籍和特定的編撰層次。歸為祭司傳統的文本並沒有明確的像《申命記》那樣的中心,而是分散在摩西的前四本書中。盡管如此,它們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占據更加顯著的位置。這些文本屬於以聖殿儀式為中心的宗教,面向專業的神職讀者,而申命傳統則針對更廣泛的受眾。“申命書”如格哈德·馮·拉德(Gerhard von Rad)所言,“有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但它也以不厭其煩的自我解釋來充實人們的頭腦。簡而言之,它完全迎合了它的讀者或聽眾以及他們對神學的理解能力。而這種解釋的耐心在祭司的作品中完全看不到。他們的任務基本上限於編纂、篩選和在神學上對相關材料進行分類。” 祭司典籍構成了為聖殿崇拜提供基礎的手冊,《申命記》則是一本指導性的教科書和指南,旨在為整個社區的社會生活實踐奠定基礎。然而,除了這些風格和功能上的不同之外,這兩種傳統線似乎源自兩種不同類型的宗教體驗。與祭司典籍相關聯的宗教旨在使其人民在世界中安居,將所有人類及事物整合到自然的神聖秩序中,它宣揚的宗教要求人們在儀式和祭祀中擁抱世界,並熱切地接受被創造的秩序;而在申命傳統中宣揚的宗教旨在超越這個世界,將人們從這個世界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將他們與律法的超自然秩序緊密聯系在一起。原始宗教要求其人民通過崇拜和祭祀來融入世界,在這些儀式中,他們熱烈地讚頌被創造的神聖秩序;而對次生宗教而言,最重要的是,其信眾刻苦專研那些記錄神的旨意和真理的經文,並以此來擺脫、背離這個世界。
這兩種宗教並不僅僅並列存在於希伯來聖經中。相反,它們在一種緊張的關系中相互對峙,因為一種宗教正是另一種宗教所否定的。這種對抗之所以沒有引發公開矛盾,是因為在《聖經·舊約》中,兩種宗教都沒有完全以其純粹和嚴格的形式展開。試圖讓其信徒在世界中安居的古老多神宗教只能以碎片的形式呈現給我們,因為它已經被一神教的修改覆蓋。我們無法更進一步重建它,只能以粗糙的輪廓為基礎,並借助從鄰近宗教中繪制的眾多相似之處來了解。至於其後的世界性救贖的一神教,它僅僅表現為《聖經·舊約》中的普遍趨勢,直到後來的拉比猶太教和教父基督教的文獻——它們也建立在舊約基礎之上——出現,它才表現得更加明顯,其中最為顯著的表現就是嚴厲地譴責其他宗教為異教。在希伯來聖經中,這兩種宗教可以共存於這種不同時而並存的狀態,即“不再”和“尚未”。事實上,《聖經》內在的這種高度緊張的對抗無疑代表了其全球性成功的秘訣之一。
在與這兩種完全不同形式的宗教的關系中——一個是多神教,另一個是一神教;一個面向世界,另一個背離世界;一個是以祭祀為中心的宗教,另一個是以經典為中心的宗教——希伯來聖經就像一幅拼圖一樣:首先是一幅圖像,然後是另一幅圖像移至眼前,全憑我們如何看它。這兩種解讀,任何一個都不能說獨自成立。有些人根據《聖經》與其他中東宗教的諸多相似之處,將其描繪為與之相同的中東宗教——正如伯恩哈德·朗(Bernhard Lang)在他最近的著作《聖經上帝:肖像》(Jahwe der biblische Gott: Ein Porträt)中所做的那樣——但無論如何,這種看法都與那些僅僅根據其接受史來閱讀它的人一樣偏頗,正如我在我的作品《埃及人摩西》中所說的那樣,它宣揚的是獨一神,並根據摩西區隔,將他的宗教定性為真理並將所有其他宗教置於謬誤的黑暗中。這兩幅圖像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單獨地充分反映希伯來聖經,但兩者被都包含其中。
這種固有於希伯來聖經的二元性,這個帶有雙面性的“雅努斯面”,它所引起的廣泛的注意,不僅限於來自神學家。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關於摩西的著作,我將在第四章中更詳細地討論。弗洛伊德區分了兩種摩西形象,一個是“埃及人摩西”,一個是“米甸人摩西”。前者代表著崇高的一神教,代表著這里所謂的“反宗教”,希伯來聖經的現代層面。弗洛伊德認為後者是火山神雅威的信徒,代表著典型的部落宗教;因此,他代表著《聖經》的古老層面。
由於遠非源自向一神教的過渡,《聖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前一神教時期的宗教形式。然而,一神教已經可以在《聖經》中看出端倪,並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其中被編輯過的文本跨越了這個分界,既見證了多神教的出發點,又見證了一神教的最終狀態,尤其見證了從一個到另一個的過渡中產生的沖突。因此,一神論宗教並不是從古老宗教有邏輯性地演變出來的;一神教和古老宗教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革命,而非演化。因此,我的論點是,在《聖經》中被拼合在一起的兩幅圖像之間的一神教轉變,以一種斷裂的形式出現,與過去劃清了真理與謬誤的界限,並在隨後的接受過程中,產生了猶太人和外邦人、基督徒和異教徒、基督徒和猶太人、穆斯林和異教徒、虔誠信徒和異端的區分,表現在無數的暴力和流血沖突中。《聖經·舊約》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核心段落已經敘述了這種暴力事件。這個方面將在下文更詳細地探討。
作為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僅討論一神教世界),在次生宗教的經驗領域和摩西區隔所創建的精神空間中生活了數百甚至上千年,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區隔是自然、正常和普遍的宗教形式。我們傾向於不假思索地將它與宗教等同起來,然後將它投射到所有陌生和早期文化上,這些文化對真理宗教與謬誤宗教之間的區隔則一無所知。若根據這種宗教概念來衡量,原始宗教必然會顯得貧瘠:它們沒有“正統”的概念,幾乎無法將自身與其他文化領域區分開來,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神與自然現象、有個人魅力的上師與規範性原則之間的界線也不清楚。在這些方面以及其他諸多方面,它們還不算是“正統”的宗教。在這種內隱而根深蒂固的信仰背景下(當然,這不是一個明確闡述的宗教理論問題),像“反宗教”這樣的概念必然會引起反感。什麽?以最崇高、最純潔、宗教可能達到的最先進的形式呈現給我們的一神教,竟然被稱為不是“宗教”而是“反宗教”?多麽荒謬!
什麽是真理?
我想用科學作為平行參照來闡明應該如何理解“區隔”這個術語。正如一神論宗教建立在摩西區隔之上,科學建立在“巴門尼德”區隔之上。一個區分真假宗教,另一個區分真假認知。這種區隔體現在同一律、非矛盾律和排中律(tertium non datur)的原則中,通常與巴門尼德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他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紀。沃納·亞格爾(Werner Jäger)準確地稱之為一種“思維限制”或認知束縛:“正如他 (指巴門尼德) 一再——一次比一次更加有力地——強調,存在即是,不存在即不是。存在的東西不可能不是;不存在的東西不可能是—巴門尼德由此表達了他在意識到邏輯矛盾無法解決後建立的思維限制。” 通過在“狂野思維”——傳統的、神話式的構建世界的模式——和服從於非矛盾律的邏輯思維之間劃定界線,這種思維約束將認知、驗證和知識置於一個全新的基礎之上。希臘人引入的關於知識的這一新概念,其革命性不亞於猶太人引入的——並以摩西命名——關於宗教的新概念。這兩個概念都以前所未有的分化、否定和排外的動機為特征。自從科學出現以來,就有了基於真假認知區分的知識,這種知識將自身與錯誤區隔開來,並通過其推理方式向批判敞開大門,同時也就出現了諸如神話(muthos)與理性(logos)、智慧與知識之間的區隔,這些區隔正好對應於異教的偶像崇拜和一神教之間的區隔。科學知識是“反知識”,因為它知道與其命題不兼容的東西。只有“反知識”才能發展出一套規範性條文,來規定什麽才算是知識,什麽不算,即一種二階知識。
這就是為什麽——某種程度上說——古埃及或巴比倫的“科學”概念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就古埃及人和巴比倫人而言,“知識”一詞的含義與巴門尼德之後的希臘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然而,類似這樣的概念大體上仍然發揮了它們應有的作用。我們都知道,希臘人通過引入一種新的批判性的真理觀而徹底改變了世界,因此,每當我們面對那些對“前希臘科學”的引用時,都會采取謹慎的態度。然而,就宗教而言,這種意識卻遠沒有那麽深入人心。幾乎沒有人會想到關於埃及或巴比倫“宗教”的書籍實際上是以一種或多或少借喻的方式使用“宗教”這個詞。但是,我們的宗教概念以不帶有任何否定色彩的方式同時涵蓋了一神教和前一神論時期的宗教。可是,通過引入摩西區隔,猶太人至少像希臘人那樣徹底改變了世界。他們引入了一種新的宗教形式,它與所有傳統所謂的宗教大相徑庭,就像希臘科學與所有傳統所謂的科學大相徑庭一樣。
在我參與過的許多討論中,我的這個論點被貼上了“反閃族主義”的標簽。如果我將這種世界的變革解讀成為向更糟的方向而不是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如果我是要指責猶太人通過引入摩西區隔而終結了原始宗教的黃金時代,那麽這種指控或許是合理的。但在我看來這是荒謬的,實際上,其荒謬程度不亞於說我責備希臘人,責備他們通過引入科學思維而使世界不再神秘且可以訴諸理性解釋。在我看來,很明顯,無論是在科學思維中還是在一神教中,我們都遇到了最高層次的文明成就,我從來沒有想要拋棄它們。我既不主張回歸到神話,也不主張回歸到原始宗教。事實上,我並沒有主張任何事情;我的目標偏重於描述和理解。我將科學思維描述為“反思維”並將其追溯到巴門尼德對真理與謊言(或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區分,是為了引起人們對這種知識中固有的否定潛力的關注,而不是批評和抵制。坦率地說,科學知識是“不寬容”的。科學的真理或許在大部分情況下是相對的,並且有效性有限,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與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事物都兼容,因為它們有自己的有效性、可驗證性和可證偽性的標準,它們必須遵守這些標準。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已經變得如此不言自明,以至於它幾乎已經與我們的知識概念密不可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正如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言,我們將另一種不同類型的知識稱為“野性思維”和“拼湊”。
“反宗教”概念旨在強調次生宗教固有的否定潛力。盡管這些宗教本質上也是“不寬容”的,但此處同樣不應被視為一種譴責。250 年前,大衛·休謨(David Hume)不僅論證了多神論比一神論早得多,還進一步提出了相關的假設:多神教是包容的,而一神教則是排外的。這是一個古老的爭論,我在拙著《摩西》一書中無意重新審視。那些次生宗教必然是不寬容的,也就是說,它們必須對與它們的真理不相容的東西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以便它們的真理能夠行使它們所自詡的塑造生活的權威性、規範性和約束力。在每種情況下,反宗教都從根本上改變了它們所出現於其中的歷史現實。它們的批判性和變革性的影響力是由它們的否定性能量,以及摒棄和排斥的力量所支撐的。它們如何處理它們的結構性不寬容是另一回事。這不是我眼下關注的焦點,但我想順便指出,宗教應該嘗試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試圖否認它的存在。無可否認,近年來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重要進展。
科學的排斥性或否定潛能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能夠區分非科學知識和科學知識;另一方面,它能夠區分錯誤的和正確的科學知識。神話是非科學知識的形式,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錯誤的。科學錯誤是被證偽的科學知識的實例,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神話。當我們審視反宗教時,我們也會發現類似的情況。原始宗教是“異教”,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異端;異端是非正統的觀點和實踐,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原始宗教或異教。
宗教和科學之間的類比,以及摩西區隔和巴門尼德區隔——或甚至蘇格拉底區隔、柏拉圖區隔和亞里士多德區隔——之間的類比,都可以進一步展開。但這里涉及的遠不止是一個簡單的類比。新的知識概念的必然結果是,它同時也定義了一個與其自身同樣新穎的對立概念,即“信仰”。在這個新的語義下,信仰指的是堅信某個命題為真,即使我無法在科學基礎上證明其真實性,但仍然聲稱擁有最高權威的真理。知識並不等同於信仰,因為它關注的僅僅是一種相對、可辯證,且仍然可以確任和被批判驗證的真理;信仰也不等同於知識,因為它關注的是一種不可被批判驗證的,且仍然是絕對、不可辯證,和被神啟示的真理。在此區別之前,既不存在構成科學的知識概念,也不存在構成神啟宗教的信仰概念。知識和信仰曾經是一體的,因此科學和宗教,曾經也是一體的。像《希臘人的信仰》(烏爾里希·馮·威拉莫維茨-莫倫多夫;柏林,1931)和《古埃及人對神的信仰》(赫爾曼·基斯;萊比錫,1941)這樣的書名基本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只有在新的定義下,我們才有這種“無需求證(知其謬而故信之)便可信之”的信仰概念,可是原始宗教的神並不是這類信仰的對象,而是自然現象的產物,現象本身即被作為樸素且直接的證據,但這被一神教斥責為偶像崇拜和異教自然崇拜。像其他所有原始宗教的信徒一樣,古埃及人並不是“信奉”神,而是“知道”神,這種知識並不是用“真假”來界定的,而是允許在我們今天看來相互矛盾的陳述並存。
有四種簡單或原始的真理:經驗的真理(例如,“所有人都會死”),數學或幾何的真理(例如,“二加二等於四”),歷史的真理(例如,“奧斯威辛集中營”),以及有益於生活的真理(例如,“人權”)。摩西區隔引入了一種新的真理類型:絕對的、神啟的、形而上的或信仰(fideistic)的真理。這種第五種真理類型不屬於“簡單”或原始真理之列;它代表了一種革新。四種簡單的真理,特別是數學真理和歷史真理,曾是希臘科學革命的前沿;而在一神論宗教中則與之相反,被置於前沿的是與之一起問世的第五種真理:“我信仰獨一真神(Credo in unum Deum)”。
不寬容、暴力、和排他
許多批評者認為“摩西區隔”的概念對宗教不友好,甚至具有反猶太或反基督教的色彩,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一概念暗示著摩西區隔導致了仇恨、不寬容和排他。
當然,我並不認為原始宗教的世界沒有仇恨和暴力。相反,它充滿了各種形式的暴力和侵略,而隨著一神教宗教的興起,其中許多形式被馴化、文明化甚至完全消除,因為這些暴力與他們宣揚的真理並不相容。我根本不想否認這一點。但也同樣不能否認,這些一神論宗教同時也給世界帶來了一種新形式的仇恨:對異教徒、異端、偶像崇拜者及其神廟、儀式和神祇的仇恨。如果我們把這些思考斥為“反猶主義”,那就等同於任由這種對話語以及思想的禁錮以一種危險的方式限制我們對歷史的反思。如果一個人,由於害怕自己當前的立場被發現是偶然的、相對的,甚至與其初衷或沿途中拋棄的那些選擇相比更加不可取,便拒絕解釋自己選擇的道路,這便會滋生出一種新的不寬容。能夠歷史化和相對化一個人的立場是所有真正寬容的先決條件。
對於我的觀點——一神教建立在真理宗教和謬誤宗教之間的區隔上——持反對意見的人們堅持認為一神教不是區隔的宗教,而是大同和普世性的宗教。相反,是多神論劃定了區隔。每個民族、部落和城市都有自己的守護神,通過劃分相應的神界來表達其差異化的身份認同。每個神祇都代表了一種區隔。一神教撤銷並廢除了所有這些區隔。在唯一的神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神教遠非在人與人之間設立障礙,相反,它打破了這些障礙。因此,克勞斯·科赫(Klaus Koch)寫道:“多神教的神在本質上是特定的和區域性的。因為它們是根據崇拜它們的社群被社會化的,所以它們對一切不純和外來的事物即便沒有徹底地敵視,至少是持有輕蔑的態度……而效果論(consequential)一神教則預設一位在全天下對所有人都可觸及的神。這意味著一種對所有人都同樣適用的倫理道德,但前提是一神教的視野沒有被選中的子民的社群封閉性所限制。神越是排他,對人類就越包容。” 正如埃里希·曾格(Erich Zenger)所說:“一神教在其對話中尋求的是普遍適用,而非特立獨行。”漢斯·齊爾克爾(Hans Zirker)強調:“一神教的核心在於將現實構想成一個統一體,並假定普遍適用於全人類的歷史。一神教的主要含義不在於它聲稱只有一個神而不是眾多神,而在於它如何定義人類的世界,即這個世界不應該被卷入神權之爭和區域分封,也不應該陷入光明與黑暗、‘善’與‘惡’之間的不可逾越的二元對立,也不應該在好戰民族的自我陶醉中最終多極分化。” 這是基督教的看法。而基督教試圖廢除的真正區隔在齊爾克爾的列表中並沒有被提到:它是由律法規定的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界線,尤其以割禮為標志。基督教建立在摩西區隔的普遍化之上,現在不僅適用於猶太人,還適用於其他所有人。
因此,這種反對的聲音幾乎沒有從猶太人那里聽到。猶太教是一種差異文化。對於猶太教來說,一神教劃定了一個邊界,而猶太人有責任維護這一邊界,這是不言自明的。猶太教對同化的厭惡程度,不亞於基督教對區別對待的厭惡。因此,對於猶太讀者來說,摩西區隔的概念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在猶太教中,一神論固有的普世主義被推遲到了彌賽亞式的末世;在我們所知的世界中,猶太人是真理的守護者,而這一真理關乎每個人,但暫且先托付給他們,就好像他們是某種精神上的先鋒隊一樣。當然,對於基督徒來說,這個末世在大約兩千年前就已經到來了,自此不再需要這樣的區隔。這就是為什麽基督教神學對一神論的排他力量視而不見。猶太教是一種自我排斥的宗教。通過神的選擇,以色列將自己孤立出來(或被神孤立),遠離各民族的圈子。律法在被選中的子民周圍築起了一道高墻,它形成了一條隔離帶,用來防止來自周邊地區的思想和習俗對其造成的污染或同化。這種自我隔離的行為不需要訴諸暴力,或者至少不需要迫害那些持不同信仰的人。《聖經》中記載的大屠殺事件,比如對崇拜金牛的人實施的屠殺,或者奉以利亞和約書亞的命令對巴力祭司的屠殺,都是猶太人的內部事務;它們旨在消滅生活在“我們之間”、在我們當中和在我們心中的埃及人或迦南人;它們是指向內部的,而不是向外。“外邦人”(gojîm)可以自由地按照他們的意願以他們的方式崇拜他們的神。相比之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不承認這一邊界,因此它們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引發暴力沖突。“天選之人”的信仰要求猶太人自我孤立;然而,基督徒有傳播福音的義務,穆斯林也有迫使他人屈服的義務,這種義務使他們排斥異己。上帝通過選擇以色列作為他的子民,將其從所有其他民族中隔離出來,並禁止其采納周圍環境的風俗習慣。通過命令基督徒和穆斯林將真理傳播到世界的每個角落,上帝確保那些對這一真理閉目塞聽的人將被拒之門外。只有在這種形式下,一神教內在的排他潛力才會爆發成為暴力。
這些考量同樣適用於宗教包容的問題。不寬容源於不能或不願包容不同的觀點和由這些觀點產生的實踐。這不僅預設了自己和非自己的區別,還預設了通過真理和謬誤的區別建立的兩者之間的不相容性。寬容也建立在同樣的預設之上。嚴格以字面意義來說,我只有可能“容忍”與我自己的觀點相悖的事物,但我之所以能夠容忍,是因為我足夠強大或慷慨,不必將其視為威脅。因此,以古代異教的多神論而言,討論“寬容”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里並沒有不相容的標準;對於他各民族的宗教,沒有什麽需要“容忍”的。這就是為什麽我更願意談論“可轉譯性”而不是寬容,我指的是自蘇美爾時代以來便有記載的一種做法,即將神的名字由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進而由一種宗教翻譯成另一種宗教。其他民族的宗教被認為與自己的宗教基本兼容。這並不是說,持有這種看法的民族在彼此交往中克制了暴力,也不是說暴力是由摩西區隔引發的。這只是說政治暴力並沒有神學上的認可,至少不是在認為必須用武力強迫持有錯誤信仰的人改宗的意義上。例如,亞述人會請出阿修爾之神(Assur)來合理化他們對變節的附屬國施加的殘酷懲罰,並不是因為這些叛徒堅持崇拜他們自己的偽神,而是因為,一旦違背了以阿修爾之名所立下的忠誠誓言,他們便成為了他的敵人。事實上,外國人的誓言可以被接受的事實本身就假定了他們的宗教和神祇可以與亞述的神祇協調一致。美索不達米亞區域的多中心社會組織形式形成了多個城邦,各個城邦之間多樣化的溝通形式促進了這種轉譯的做法,令其在公元前的第三個千禧成熟完善。與其他國家的契約必須用誓言來封存,而見證誓約的神祇必須是兼容共存的。因此,神祇對照表逐漸被編制,並最終對接了多達六個不同的神祇體系。如果假定其他民族崇拜的神祇是虛妄和臆造的,這將是不可能的。所有契約都以雙方神祇的名義訂立。宗教成為一種溝通的媒介,而不是消滅和排斥。神名的可譯性原則有助於克服部落宗教的原始民族中心主義,建立文化之間的聯系,並使它們對彼此更加透明。至於這些聯系有時伴隨暴力和流血,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需要注意的是,摩西區隔的原則阻礙了這種可譯性。在一神教的原則下,“外幫人”仍然可以在時光的盡頭自由地信仰唯一真神,但他們當下對他的崇拜形式卻不被認可。朱庇特(Jupiter)無法被翻譯成亞威(Yahweh)。根據這個區隔,猶太人將不可能與亞述人結成盟約,因為在誓言下的盟約將會意味著阿修爾和亞威的等同性和相互可譯性。因此,摩西區隔具有實際和深遠的政治後果,我認為這些後果也在這種區隔被引入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猶太人來說,亞威無法被翻譯成“阿修爾”,“阿蒙”或“宙斯”。這一點是“異教徒”永遠也無法理解的。在經過數千年的轉譯後,人們開始相信所有神的名字都指向同一個神。瓦羅(Varro,公元前 116–27 年)認為無需區分朱庇特和亞威,“因為只要指向相同,名字就無關緊要”(nihil interesse censens quo nomine nuncupetur, dum eadem res intelligatur)。在其反對基督徒的小冊子(《真言》)中,塞爾修斯(Celsus)爭論說,“無論人們把上帝稱為‘至高神’(Hypsistos),還是宙斯,或阿多奈(Adonai),或萬軍之主(Sabaoth),或——如埃及人那樣——稱為阿蒙,或——如斯基泰人(Scythian)那樣——稱為帕帕約斯(Papaios),都無關緊要。”只有在可譯性受阻礙時,才有可能真正信仰某個神。如果無法進行翻譯,一個人就只能選擇一個名字來信仰,而不是一個最終即便不是與萬物等同,但也與所有其他神祇相同的“至高無上者”。
在古代晚期的異教信仰中,神祇的名字已經失去了意義:首先,因為它是約定俗成的,其次,因為異教徒同樣認識到,在眾多的神祇名字背後,其實只有一個神,既然他是唯一的,那便無需名字,因為只有在需要將一件事物與其他事物區分開時才需要名字(《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第 20 節,這一觀點後來被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引入基督教)。 另一方面,縱使猶太人和基督徒認為上帝的名字不可言說或必須避諱,對他們來說,這個名字依然發揮著決定生死的至關重要的作用。Qiddusch ha-Schem,即“成聖之名”,是猶太教中殉道的術語,而基督徒祈禱時會說:“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通過 這樣的做法,兩者都表明了對這個神的無條件信仰,而不是其他的神。
對於這種基於不相容的新認知而建立的不寬容形式,重要之處不在於施加暴力,而在於忍受暴力。人們必須準備好,即便為自己的信仰從容赴死,也絕不能認同與真理宗教不相容的行為或信仰。因此,重要之處不在於容忍不同的觀點和行為,在於拒絕執行他人要求的“無法容忍”的行為,比如食用供奉給羅馬帝國神權的肉類。羅馬帝國的大多數官員本無意成就殉道者,並且也願意向過於較真的人做出各種讓步,只要基督徒表現出最低限度的遵從,他們便可滿意。不寬容反而在受害者中間更為普遍,他們傾向於將任何輕微的讓步都看作是被“同化”的證據,視為背離了神。只有當基督教徒自己掌握了權力,基督教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後,被動的不包寬容才轉化為主動的不包容。他們當初對獻給異教神祇的肉類的排斥此時演變成為禁止這樣的祭祀。
一旦我們意識到根植於一神教的不包容性直接源自摩西區隔,最初以被動或殉教的偽裝形式出現——即拒絕接受被認定為是虛妄的宗教形式,且寧死不屈——那麽,我們便會明白,“一神教與暴力”這一問題不僅與施暴有關,它也與忍受暴力有旗鼓相當的關系。同樣,對於仇恨也是如此。說摩西區隔帶來了一種新形式的仇恨,即對“異教徒”的憎恨,令他們首先被認為是可憎的,進而被排斥,這話其實只道出了故事的一半。比起對被排斥者的仇恨,被排斥者們自己心中滋生的仇恨則更加重要。在《巴比倫塔木德·密釋納·節期篇·安息日禁忌·第 89 節 a 段》中,提出了“西奈”一詞的含義問題。按照其中所述,“西奈”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仇恨[1]正是由這座山降臨到了全世界各個民族。其他民族嫉妒猶太人在西奈山上接受了《妥拉》,成為被上帝選中的子民。今天,這個解釋遭到了反對,它認為這等同於讓受害者為自己的命運負責。但是,如果殉道種行為不是受害者為自己命運負責,那又是什麽呢?當然,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並沒有被問及他們是否信仰猶太教。但這不應該阻礙我們看到信仰的本質,也不應該妨礙我們認識到這一概念與摩西區隔是如何密不可分。我已經提到過一神教作為一種反宗教的敵對特質,它用來定義自身的那種排他性與排斥性否定——“沒有其他的神!”——不僅僅是外向性的,也尤其是內向性的。與其擔心其他人的異教信仰,更令人擔憂的是自己的教友們隨時可能屈服於虛假信仰。《聖經》本身就反映了真理與偽真理之間的沖突以及從原始宗教到反宗教的轉變過程。一神教將自身建立的故事編排成由一系列大屠殺穿插的暴力史。若要列舉一二,我所指的是金牛犢事件之後的屠殺(《出埃及記》第 32 至 34 章)、以利亞與巴力祭司的祭祀競賽之後對巴力祭司的屠殺(《列王紀上》第 18 章)、約西亞改革的血腥執行(《列王紀下》第 23 章 1 至 27 節),以及對外族通婚的強制終止(《以斯拉書》第 9 章 1 至 4 節;第 10 章 1 至 17 節)等等。 自啟蒙運動以來,這些內容和其他經文一直被批評者們當作一神教固有的暴力和不寬容的證據來反對基於《聖經》的宗教。不過,單純在此覆述這類批評既多余,也愚蠢,因為我們早已了解到,這些被記錄的暴行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至少就猶太教而言,從未有過對異教徒的暴力迫害。但在我看來,通過曲解這些經文以便維護一神教是一種超越所有差異的、包容且普世主義的宗教的做法同樣愚不可及。一神教通過借用各種暴力行為來講述自身建立和鞏固的故事,這肯定具有重要意義。在這里,我們也需要將視角轉變到記憶歷史。一神教在以色列到底是如何建立的,通過演變也好革命也罷,通過漸進的過度也好或是暴力的報覆也罷,這些問題將不再是調查的中心。相反,我們必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聖經》自身是如何記錄這個轉變的過程的。在我看來,試圖否認經文中蘊藏的暴力語境並不會獲得歷史或理論上的優勢。一神論是一種毀像主義[2]。這便是它對自身的認知,它在《聖經》文本中也是這樣呈現的,它在歷史上也是如此被理解的。與其頌揚一神教的普遍博愛而將這種暴力語義掩蓋起來,我們不如反思如何接納並應對這種暴力語境。
我的目的不是批判一神教,而是冒險對其革命性的特征進行歷史分析,探討其改變世界的獨創性。在這個背景下,決定性的重點是,在《聖經》中那些受到一神論啟發的段落里,一神教是通過一系列大屠殺來鞏固其自身的。我在這里所討論的是文化語境,而不是由真實事件構成的歷史。換句話說,一神教意識到其固有的暴力,並強調其引發的革命性轉變。我無意兜售廉價且“相當粗糙”(套用曾格(Zenger)的話)的“一神教本質上是和必然地是不寬容的”的論點,而是要展示潛藏於其內部的否定力量,即對抗性的能量,它能將真與假的區隔和排中律原則轉化為一個之前既未被發現,甚至也未被猜想過的領域:神聖和神的領域,既宗教領域。通過這種否定的力量,一神教獲得了反宗教的特性,通過驅逐無法與之調和的一切來確定其真理。在這個意義上,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迦南地區的宗教,甚至是《聖經·舊約》本身的原始宗教都不能像新宗教那樣被歸類為反宗教,這個新宗教的輪廓在《申命記》和其他受這一傳統影響的書籍中最為清晰地顯現出來。
異己的建構:宗教諷刺
正如我已經提到的,摩西的區隔是指真理宗教和謬誤宗教之間的區分。我的觀點是,這種區分代表了宗教史上的一項革命性創新。它是傳統的歷史演化宗教和文化所不知道的。在這里,關鍵的區別在於神聖與俗世、純凈與污穢之間。忽視一個重要的神明比崇拜偽神更為嚴重,這是次生宗教的主要關切事項。原則上,所有宗教都具有相同的真理價值,並且人們普遍承認外邦神祇與本族的神靈之間存在可轉譯的關系。因此,從原始宗教體驗到次生宗教體驗的過渡,必然伴隨著對身份和異己的新構建,這種建構阻礙了這種可轉譯性。在可以稱之為“轉譯的闡釋學”的地方,現在出現了一種“差異的闡釋學”取而代之,依據“每一個判定都是一種否定”原則,它通過與他者保持距離,來確保自己的身份。
在這里,引起我的興趣的,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新事物。每種身份的建構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異己的建構。這不足為奇。一個群體內部的聯系越緊密,它就越會在外部與世界劃清界限。但這只是事實的一半。當團結感有所提升,它便會導致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鴻溝被放大,為了彌合這道鴻溝,就必須要借助一些跨文化的理解手段。所有文化在建構它們的身份符號時,也會一起制定出一套關於他者的解釋體系和相應翻譯技巧。多神教的文化體系就是這樣一種翻譯技巧。通過將超自然的神秘領域解構為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它將某個群體的神祇世界轉換為一種與其他群體和文化的神祇世界相兼容的格式。部落宗教則不能以這種方式相互轉譯。在這方面,多神教代表了一項重大的文化成就。盡管在其他方面這些群體彼此之間可能格格不入,但在神祇方面他們仍然可以達成共識。摩西的區隔則帶來了重大的轉變,因為這里涉及的是“反向”身份認同,或者用喬治·德韋魯(Georges Devereux)的術語來說,是“敵對性的涵化”。這里的“異教徒”不僅僅是“他者”那麽簡單,而是一個批判性建構的產物。正如我已經闡明的那樣,摩西的區隔主要涉及到一個人自己的宗教,它在其中劃分了真與偽之間的區別;它的目的是在自身所處的群體和文化中根除異教傾向。然而,《聖經》中還存在著一種關注他人宗教的文體,這種文體刻意地用一種不理解的目光去看待他者的宗教實踐,再用諷刺性的描述加上尖刻和異化的語態來嘲諷它們,這就是宗教諷刺的文體。
這種文體形式的雛形已經可以在《聖經》中見到,比如在《耶利米書》第 10 章、《以賽亞書下卷》第 44 章和《詩篇》第 115 章的一些詩節中。這篇詩歌將《聖經》中上帝的無形與異教徒神像的可見性並列對比,揭示了在其浮華的物質性背後它們的虛妄和空洞:
為何容外邦人說:他們的神在哪裡呢?
然而,我們的神在天上。都隨自己的意旨行事。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卻不能言,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有鼻卻不能聞。
有手卻不能摸。有腳卻不能走。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诗篇》第 115 章第 2 至 7 節)
在這里,攻擊的對象不再是激起亞威嫉妒心的“其他神”,而僅僅是“偶像“(‘atzavim)——由異教徒在蒙昧狀態中創造的虛妄的神。《以賽亞書下卷》更加無情地嘲諷了這種圖像崇拜宗教的荒謬性:
制造雕刻偶像的,盡都虛空。他們所喜悅的,都無益處。他們的見證,無所看見,無所知曉,他們便覺羞愧。
誰制造神像,鑄造無益的偶像?
······························································································································
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用錘打鐵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錘成。他饑餓而無力,不喝水而發倦。
木匠拉線,用筆劃出樣子。用刨子刨成形狀,用圓尺劃了模樣,仿照人的體態,作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
他砍伐香柏樹,又取柞(或作青桐)樹和橡樹,在樹林中選定了一棵。他栽種松樹得雨長養,
這樹,人可用以燒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燒著烤餅。而且作神像跪拜,作雕刻的偶像向它叩拜。
他把一分燒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飽。自己烤火說,阿哈,我暖和了,我見火了。
他用剩下的作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這偶像俯伏叩拜,禱告它說,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他們不知道,也不思想,因為耶和華閉住他們的眼不能看見,塞住他們的心不能明白。
誰心里也不醒悟,也沒有知識,沒有聰明,能說,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燒了,在炭火上烤過餅,我也烤過肉吃,這剩下的,我豈要作可憎的物嗎?我豈可向木𢃼子叩拜呢?
(《以賽亞書》第 44 章第 9 至 19 節)
這段文字使用古老的東方職業諷刺體,來嘲笑偶像崇拜者的行為。這種體裁通過將某些職業特有的活動描繪為徒勞無功且荒謬的浪費時間,通過將其描述成一種無用的職業,只會令從業者困乏、畸變和弄臟自己,從而將他們排斥在社區之外,以及有社會意義的行為的規範之外。偶像崇拜者的活動之所以荒唐,是因為他們宣揚的偶像是虛構的產物、是並不存在的神明、是幻想出來的力量。諷刺手法依賴於一種異化的技巧。所描述的活動或操作方式被異化到了使其有意義的特定前提被有意無視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少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塊木頭自身永遠不會單純地被崇拜為神聖的形象,而必須首先在一場覆雜的儀式中被供奉,使其與神的世界相通,能夠成為神靈的臨時容器。將一個只能在高度覆雜的符號系統中“發揮作用”的宗教形象簡化為其純粹的物質性存在,這是一種異化的伎倆,意在使所有與之相關的行為都顯得荒謬。
諷刺“偶像崇拜的愚蠢”的主題在經外書《智慧篇》中得到得到了最充分的論述。這部作品中,至少有四個章節專注於這個主題,其中還涉及了一些有趣的劃分。經文首先處理那些跪拜自然現象的人,他們崇拜的是神的作品,而不是作品的創造者:
反而認火、風、流動的空氣、運轉的星辰、洪流的巨濤、天上的光體,為統治世界的神。
(《智慧篇》第 13 章第 2 節)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
……的罪尚较轻微,因为,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找到,却一时误入了迷途:
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所见的世物实在美丽,因此在专务研究他的工程时,只追求外表;
(《智慧篇》第 13 章第 6 至 7 節)
这些崇拜自然的人,被自然的证据和创造物的美所蒙蔽,无法认识到它们背后的创造者。但至少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像那些将希望寄托在“死物”上的人。至此,经文就用与《以赛亚书》相似的讽刺形式,将矛头指向了偶像崇拜者:
有些人真是可怜!他们竟将希望寄于死东西上,竟称人的手工、金银和艺术的创作、动物的肖像、或古人雕刻的无用的石为神。
设想:有个木匠,锯来一棵适用的树木,精巧地剥净树皮,熟练地施展技巧,制成一件日常生活的用具;
以后用工作剩余的碎木,煮饭充饥;
后来由那些剩下一无所用的废木中,取出一块弯曲多疤的木头,在闲暇无事时,辛勤地加以雕刻,本着自己熟悉的手艺,按图样将它刻成一个人像,
或做成一个卑贱的兽像,涂上丹砂,将外皮漆成红色,遮住一切疤痕;
随后,为它做一个适宜的居所,把它嵌在墙上,用钉子钉住,
预先加以照顾,免得它掉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件东西是不能自助的,不过只是偶像,需要人来扶助。
但是,他反不感羞耻地向这无灵之物祷告,祈赐财富、妻室和子嗣;
向这虚弱的东西,要求健康;向这死物,要求生命;向这无能的东西,要求援助;
向这有脚不能行的东西,要求旅行;向这有手而毫无动作的东西,要求发财、工作、事业成功的力量。
(《智慧篇》第 13 章第 10 至 19 節)
但是经文并未止步于嘲弄和讽刺,而是上升到了一种极度强烈的诅咒:
但是,人手造的木偶和木偶的制造者,却是可诅咒的:制造者,因为他造了木偶;木偶,因为虽是腐败的东西,竟被称为神。
不虔敬的人,与他行的不虔敬的事,同样为天主所憎恶;
所以,木偶与造木偶的,都必遭受惩罚。
为此,天主必要惩罚列邦的偶像,因为偶像在天主的造物中,成了可憎之物,成了人们灵魂的障碍,作了愚人脚前的陷阱。
(《智慧篇》第 14 章第 8 至 12 節)
在这里,经文通过“陷阱”一词引入了诱惑的概念。雕刻的偶像不仅是无用的,它们还引诱崇拜者去作恶。至于偶像的无用和虚构本质,经文指出偶像崇拜是一种次级的、派生的现象:“起初原无偶像,也不能永久长存;由于人的虚荣心,偶像才进入了世界”(《智慧篇》第 14 章第 13 至 14 節)。這個論點特別有趣,因為它預示了 17 和 18 世紀備受關注的圍繞自然宗教和原始宗教形式的討論。偶像崇拜的出現被追溯到兩個歷史來源:死者崇拜和統治者崇拜。
一個父親因他兒子的夭折,甚為悲傷,遂為自己早死的兒子立像,他雖是已死的人,如今卻敬之如神,並傳令家屬禮拜獻祭。
這種不虔敬的事,相沿日久,便成了習俗,以致守如法律;再加上君王的命令,雕像遂受崇拜。
住在遠方的人,不能當面尊敬國王,便由遠方設想君王的相貌,為所要尊敬的君王,制造一座可見的肖像,向那不在跟前的,殷勤獻媚,如同就在跟前一樣。
藝術家的野心,把那些不認識君王的人,也都誘來,為擴大這項敬禮;
藝術家原為討有權威者的歡心,就竭力運用自己的技術,使君王的肖像格外美麗;
民眾受了這精美手工的吸引,不久以前那當人尊敬的,現在卻奉之為神了。
(《智慧篇》第 14 章第 15 至 20 節)
這已不再是諷刺,而是一種初露頭角的宗教理論,其關於偶像起源的論點值得嚴肅對待。根據這一理論,偶像崇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對死者和統治者的崇拜,即墓葬雕像和政治肖像。在這篇經文寫作的時代,羅馬皇帝的雕像已經遍布世界。作為對帝國的忠誠的考驗,臣民需要對這些雕像頂禮膜拜,只要他們保持對羅馬帝國的忠誠,就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宗教、風俗和法律。通過崇拜皇帝的形象,他們公開展示了這種忠誠。一方面講,偶像產生“自下層”,是幸存下來的家庭成員與逝者保持聯系的願望,另一方面講,又是產生“自上層”的,政府機構需要忠誠能以可感知的形式呈現——也就是說,在它們整個國度需要一個可見的權威象征。
對宗教的這種批判的真正惡毒之處,不在於偶像崇拜的起源,而是它引起的後果。在這里,經文提出了最不可理喻的主張:
因他們祭殺孩童,或舉行秘密祭禮,或儀式怪誕的狂歡宴會。
誰也不顧及生活與婚姻的純潔,遂彼此陷害殘殺,以奸淫加害於人。
於是,混亂到處叢生:流血、殺人、盜竊、欺騙、缺德、失信、暴亂、違約、
陷害忠良、忘恩負義、玷辱靈魂、同性淫亂、婚姻混雜、通奸淫亂。
崇拜虛無的偶像,實是萬惡的起源、由來和結局。
(《智慧篇》第 14 章第 23 至 27 節)
對偶像崇拜者的指控已經發生了激進的轉變。《十誡》中的第二誡和金牛犢的故事對其他民族的宗教毫無興趣。這些宗教既沒有受到迫害也沒有被嘲諷;它們甚至不在視野之中。爭論的焦點是一個人自己的宗教以及應該如何正確地實踐它。不應崇拜雕刻的偶像,因為這意味著要向其他神明卑躬屈膝,而亞威作為一個妒忌心重的神,不會善待這種不忠的行為。其他民族是否為他們的神造像,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宗教的比較批評不是十誡關心的主題。然而,《智慧篇》是泛希臘化時代的產物,寫於猶太教(ioudaïsmos)和希臘化(hellenismos)之間的沖突時期。如今,昔日的狹隘視角已經發展到一種普遍的立場,即不僅拒絕猶太宗教自身的錯誤形式,而且將所有其他宗教都妖魔化並譴責為異教。只有此刻,偶像崇拜的議題才被賦予了宗教間和文化間不包容的嚴重性。以色列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差異被深化為真理與謬誤、祝福與咒詛之間的鴻溝。只有此刻,“偶像崇拜”的概念,在普遍有效的鑒別真理宗教的衡量標準的意義上,才首次出現。這種“偶像崇拜”的概念與排他的一神論共生共滅,排他的一神論不再滿足於僅崇拜亞威並禁止崇拜其他神,而是斷然地否認其他神的存在。因此,它聲稱所有其他宗教都崇拜幻象出來的、虛構的偽神,並且由於背離了正道而在邪惡、虛偽和犯罪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通過將一神論作為一種“規範理念”,這一批判的核心是崇拜偶像的宗教完全缺乏倫理導向。
第二章:一神教 —— 反什麽的反宗教?
一神教較之多神教
一神論和多神論的概念源自 17 和 18 世紀的神學辯論和爭議。因此,它們完全不適用於描述古代宗教。從未有一種宗教以多神概念為參照來定義自身,或以多神(polloi theoi)而非獨一神(heis theos)為座右銘。也從未有一種宗教不在人與神之間參雜任何像天使這種折中性的存在,而宣揚嚴格純粹的一神論——也許,至少直到伊斯蘭教在 13 世紀將神學激進化之前是如此。神的唯一性並不是一神論的發明,它其實也是多神論的核心主題。早在 17 世紀,英國的新柏拉圖主義者拉爾夫·卡德沃斯(Ralph Cudworth)已經辯護過這個觀點了,今天若要舉證,可以從許多古埃及讚美詩中找到證據。在用於描述和分類古代宗教的標準這方面,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對立幾乎毫無實踐價值。在這里,突出的標準不是上帝的唯一性,而是對“其他”神的否定。這種否定是一個神學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是由神學家們確定的神學信條的問題,然後以或多或少潛移默化的方式轉化為宗教實踐。
神學和宗教的區別涉及到另一個經常針對我的的觀點:即我以摩西區隔為根據所假設的那種一神教,在歷史現實中,或者至少在《聖經》中從未存在過。我的批評者通常會提醒我,在《申命記》之前以及之外,曾經出現過一類亞威崇拜,它們除了信仰亞威之外,同時還相信他有一個侍神(parhedros),比如在昆提拉特·阿什羅德(Kuntillat Ashrud)的亞舍拉-亞威(Ascherat JHWH)或者在象島(Elephantine)的阿納特-亞威(Anat JHW)[1]。或者,他們會將我的注意力引向“天上萬軍”和天使,它們都是後期猶太教信仰形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基督教而言,三位一體的教義則又常被掛在嘴邊。透過這些和與之類似的發現,他們的結論是,從未存在過純粹的一神教(也許伊斯蘭教除外),因此摩西區隔只是一個純粹理論的構建。還有在很大程度上與此類似的一個論點是:嚴禁造像的法令從未被嚴格執行過,以色列在古代和古代晚期都有雕像,基督教本身也完全回歸到了偶像崇拜。因此,摩西區隔的概念可能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內容。
正如我之前強調的那樣,摩西區隔,並不指代一個歷史性的轉變,而是——只要它確實被轉化為現實生活實踐——一個事件或時刻。就目前所知,這種一神教實現刻的最早例子可能是埃赫那頓(Akhenaten)在阿瑪納(Armana)時期發動的政變。考慮到國王和王後仍然與太陽神阿頓一起受到崇拜,還有,即使太陽神的神聖動物——公牛姆尼維斯(Mnevis)也是公然被容忍的,所以我要重申:重點不在於我們在討論的是否是一個“純粹一神教”的情況。真正重要的是,根據摩西區隔,傳統宗教的神祇和祭祀被廢除並遭到迫害。在公元前 14 世紀的埃及,在宗教問題上首次劃出了真與假之間的界線,並被付諸實踐——各種政治、文化、社會以及毋庸置疑的心理後果也接踵而至。當然,這次政變並沒有開啟一個持久的一神教轉變。它注定要成為一個孤立的一神教時刻,盡管它確實在宗教和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毫無疑問也代表了一個重大轉折點,盡管這個轉折點更趨近泛神論(pantheistic)而非一神論。在阿瑪納時期的一神教插曲之後,埃及文化並沒有簡單地回歸到傳統的多神教,而是試圖在神的唯一性的新觀念和傳統觀念中神祇的多樣性之間尋找一條折中路線。解決這個困境的方案是一個稱為“隱秘的獨一神”的概念,他以滲透在世界中(world-immanent)的諸多神祇來作為他的名字、符號、形象、肢體和各種可見的形式來展現自己。
《聖經》記載了幾個“一神教時刻”,隨後又回歸到多神論或融合信仰的實踐中。以古代以色列或早期猶太教中並不曾存在嚴格的一神教為由,來主張摩西區隔的理論在宗教史上缺乏支持,這並不能成立。摩西區隔存在於《舊約》的神學中,但不存在於以色列的宗教歷史中——至少不在約書亞之前,前提是我們願意承認約書亞的宗教改革(《列王紀下》第 22 至 23 章)具有歷史事實的基礎。我們無法為摩西區隔確定年代;它存在於經文之中,但毫無疑問,在埃赫那頓之後,它在許多情況下以不同程度的暴力轉化成為歷史現實;最終,在漫長的幾個世紀的過程中,它至少轉變了西方和伊斯蘭世界。
因此,摩西區隔的概念涉及一種精神立場,而不是歷史事實。就像神的唯一性一樣,禁止雕刻偶像也屬於神學範疇而非宗教事宜。任何宗教都會留有足夠的空間,以容納各種不同的立場,特別是《聖經》——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都具有幾乎無法超越的對多種聲調的寬容度。我心中有一個特別的聲音,和一句多聲部合唱中的台詞:這個聲音來自於被莫頓·史密斯(Morton Smith)和伯納德·朗格(Bernard Lang)稱為“獨尊亞威”的派別,即《申命記》和申命學派的立場,也就是《以賽亞書下卷》的聲音。我感興趣的不是這個派別的要求是否在歷史現實中得到完全滿足,而是它們被提出並被記錄下來的事實。雖然有些人認為在以色列仍然存在偶像崇拜,但這不能解釋為什麽造像的禁令在《聖經》中如此突出,而堅持認為《出埃及記》與偶像崇拜無關的人則忽視了金牛犢的故事。
因此,嚴格意義上的一神教,即唯獨崇拜某一個神的概念,可能是一個最終無法在制度上實現的規範性理念,而在諸如埃赫那頓或聖經先知這樣的個體看來,在“獨尊亞威”派別或申命學派所主張的宗教運動中,這個理念的實現都是迫在眉睫的要務。一神教的歷史是由一系列一神教時刻構成的歷史,這些時刻在摩西區隔的革命性潛力的推動下,釋放出一股改變世界的力量,然而,這種力量卻無法永久性地確立其自身,使之既不可逆轉也無法被撤銷。
讓我再次強調,這個理念的最初含義並不是說只有一個神而沒有其他神,而是說除了唯一真神之外,只有虛假的神,並嚴禁崇拜這些虛假的神。這是兩回事。堅信只有一個神與接受甚至崇拜其他神可能並不矛盾,只要神與神之間的關系被理解為從屬而非互斥。排斥才是關鍵,不是唯一性。
因此,與其談論一神論和多神論,倒不如討論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的宗教更合適,或者更貼切地說,神學。在這里,我們面對的是神學理念,而不是宗教。一神論,不同於多神論,就是這樣一種理念。它只是到現代才成為了一種理念。因此,問題並不是古代以色列的宗教是多神還是一神,而是否能在《舊約》的文獻中找到一神論的理念,並且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宣揚這一理念的個人和團體是否可以在歷史現實中被辨認出來。希伯來聖經是一個包含多重聲音的文本。幾乎每個聲音都有一個對立聲音。摩西區隔是由某個特別的聲音唱出的旋律,而不是一個永久確立的宗教的固定唱段。
這同樣適用於像“反宗教”這樣的概念,它也隱含了一神論和摩西區隔的概念。反宗教是一種聚合狀態,沒有任何宗教能夠長期維持在這種形態。這些次生宗教中沒有一個曾經能夠避免(也許甚至從未想過要避免)將它們譴責為異教的原始宗教的元素納入其自身。盡管如此,每個次級宗教內部都深藏在著一個“反宗教時刻”,在適當的條件下可能再次爆發。這類時刻包括:在文藝覆興時期曾出現將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融合((syncretism))的思潮,反宗教改革運動(Counter-Reformation)在回應這一思潮時所強調的摩西區隔;上個世紀末興起一種自由文化誓反教(liberal cultural Protestantism)的流派,由於其觀點以歷史主義的角度相對化了基督教主張的真理,作為回應,卡爾·巴特(Karl Barth)所發展的“辯證神學”(dialectical theology);除此以外還包括了近年來以不同的方式和完全不同的偽裝出現的各種現代原教旨主義(modern fundamentalism),這些原教旨主義可以被理解為是對世界的現代化、世俗化和“西方化”的一種敵對反應。
因此,我們所知的歷史上最早的一神教運動只是一段插曲倒也不足為奇:即阿瑪納宗教。在這里,在它們最早出現的地方,我們遭遇到了一神論的理念和毀壞神像的暴力,它們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由於無法永久立足,它們的退場幾乎就像登場一樣突如其來。我懷疑一神論的觀念無法以書面傳統以外的形式確立自身。我懷疑一神論的理念除了作為一種書面傳統形式以外,無法以其他形式確立自己。一神論的理念只有在作為文本語料庫(textual corpus)時才能保證其經久不衰,而不是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宗教,至少不能做到絕對的嚴格、純粹和源遠流長。這種“通過書面文字進行制度化”的形式在埃及從未實現,而是首先在以色列得以實現。
總而言之,“一神論”是一種規範性理念,而“多神論”指代的則是與這一理念相對立的宗教實踐。從未有一種宗教將多神論作為一種規範性理念並對其從一而終。多神論是一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僅適用於在討論一神教是一種反宗教時使用,因為一神教通過抨擊其他宗教並與之保持距離來樹立自身。雖然在歷史上,“多神論”的概念可能曾作為“偶像崇拜”——明顯具有爭議和辱罵性質——這個概念的中立性替代品,但它繼承了其前身所具有的負面含義,因為在外延意義上這兩個概念恰好有著相同的含義。
埃赫那頓與摩西:埃及的一神教與《聖經》的一神教
在逃離埃及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摩西區隔——對真理與謬誤宗教的區分——是如何形成並成為規範的,這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神教的創始神話。埃及代表著異教世界,一個原始宗教的世界,一神教與之劃清界限,並通過走出埃及拋棄了這個世界,將其永遠留在了它的身後。《聖經》賦予古埃及的象征意義使得這個問題對埃及學家而言非常有趣。如果站在埃及人的角度,也就是從一神教誕生並與世界割裂之前的視角來看待一神教,它的起源和表現形式會是怎樣的呢?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通向一神教,或者更準確地說,沿著不同的道路可以達到兩種完全不同的一神教形式。其中一條是演化的道路,它通向一種包容性的一神教,這種一神教只不過是多神教的成熟階段。另一條是革命的道路,它通向一種排他性的一神教,這種一神教無法通過任何演化過程到達,而只能通過與之前的一切徹底決裂而產生。真理與謬誤宗教的區分僅僅與這種排他性的一神教有關。
埃及宗教史讓我們見到了一神教的這兩種形式。公元前 14 世紀中葉,埃赫那頓法老發起的宗教改革完全摒棄了傳統宗教,代之以崇拜獨一的太陽與光明之神的信仰,他的改革只能被理解為一種排他性和革命性的一神教。隨後的拉美西斯時代的神學,則是在重新引入傳統的神祇體系的同時,發展了一個”隱藏的至高神“的概念,這個神只會顯現在多神論的光譜所折射出的世界,它可以被理解成為一種包容性和演化性的一神教;它與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印度宗教的晚期階段有著密切的相似之處。
同樣的,《舊約》的一神教也應該被歸類為一種革命性和排他性的一神教。它的排他性在第一戒中表現得再清楚不過。“其他神祇只不過是他隱匿了行蹤的那個世界的多彩折射”,這樣的概念與《聖經》對上帝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然而,究竟是什麽讓這種宗教具有革命性則更加難以確定。在這里,一方面必須清楚地區分以色列宗教的歷史發展,另一方面還要區分《聖經》文本的語義。宗教歷史令我們嚴重懷疑是否曾經存在過可與埃赫那頓那次相匹敵的一神教“政變”。正如我先前指出的那樣,盡管如此,這些文本仍然記載了一系列極其暴力的事件,其中至少有一次——約西亞的改革徹底清除了以色列所有前一神教的宗教痕跡,令這次改革帶有了一神教政變的印記。不論《舊約》的一神教實際是如何建立的,是通過演變還是革命,這些文本在事後的回憶中,都不可否認地將這個過程呈現為一項革命性的壯舉:必要要肅清大量的虛假宗教,才能夠使真正的宗教蓬勃發展。這種語義無不能簡單地被視為虛構。有些人將它們看作為“後期”的產物,認為它們產生自後流亡或甚至希臘化時期,這種看法也沒有帶來任何收獲。對我而言,從哪個時間點可以開始討論,甚至於歷史現實中到底是否“真正存在過”革命性的一神教,這都無關緊要;我真正感興趣的是,《舊約》神學中發展起來的一神教自認為是革命性的,並且以血雨腥風來推翻它認為是虛妄而拒絕的舊宗教。在這里,只有這種革命性、排他性的一神教才是我們關注的。只有它才是建立在我所稱之為”摩西區隔“的的概念之上的,即真理與謬誤宗教之間的區別,而在它背後,最終是神與世界之間的區別。
埃赫那頓顯然是第一個將這種區隔付諸實踐的人。與摩西話題中的(追溯投射性)神學不同,這次我們討論的是歷史。埃赫那頓並沒有下此命令:“除了唯一的光明和太陽神阿頓外,你不可崇拜其他神。”他只是廢除了其他神,而且之後不認為它們值得一提,甚至不值得去否認。他們的排斥發生在實踐層面,而不是在話語和理論層面上進行的。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理所當然地稱之為“摩西區隔”,而不是“埃赫那頓區隔”的原因。埃赫那頓所作的區隔從未成為歷史記憶中一個被充分闡述、被編纂成典集、成為一種規範的歷史記憶元素;相反,它卻被與摩西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將摩西對真理宗教與謬誤宗教所作的區隔視作一種隱性神學,將其歸因於埃赫那頓的改革。鑒於埃赫那頓一神教與摩西一神教所共有的基礎,它們之間的差異就顯得更為引人注目。
阿瑪納的埃赫那頓的一神教是一種認知上的一神論。其背後存在著一個新的世界觀,它將存在的一切,即所有現實的總和,都歸因於太陽的作用,太陽通過它的光芒產生光和熱,並通過它的運動產生時間。正是從太陽不僅產生光還創造時間的發現中,埃赫那頓得出結論,其他神祇在創造和維護宇宙方面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因此,它們實際上並不存在,只不過是謊言和欺騙。 這就是為什麽他下令關閉它們的廟宇、廢除它們的崇拜和節日、搗毀它們的雕像,並抹去它們的名字。這與摩西的計劃完全不同。摩西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一個新的宇宙觀。他使用的是立法、憲法、契約和契約義務的語言。他關心的是一種政治一神教,一種將人們聯系在一起的一神教。它的座右銘不是:“除了我之外沒有其他神”,而是:“對你們而言沒有其他神”,也即是,你們不可有其他神。與埃赫那頓的不同之處在於,這里承認了其他神祇的存在。否則,忠誠的要求就毫無意義。這些其他神沒有被否認,而是明令禁止。凡是向它們跪拜的人不僅僅是被蠱惑了,而且也是犯下了最嚴重的罪行。因此,對於埃赫那頓和摩西來說,“虛假”宗教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義。埃赫那頓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而在摩西看來這是背叛或更確切地說是違背契約的證據。一個是認知範疇,是關於知識的問題,另一個則是政治範疇,是關於相互義務的問題。《聖經》一神教在其核心是政治性的;這一點在《出埃及記》和《申命記》中非常明顯,但在《以賽亞書下卷》和其他相對較晚的文本中,它延伸到了認知和本體論領域,在經過幾個世紀的演變後,最終形成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只有一個神,而“異教徒”所崇拜的神——偶像——是不存在的神祇,而非“其他”神。
因此,一神教的意義首先是政治性的。一人不侍二主。我可以與上帝或法老中的任何一個立約,但不能同時兩者都選,正如猶大這樣的小國不能同時與塔哈爾卡(Taharqa)和亞述巴尼拔(Assurbanipal)結盟一樣。這種二者擇一在以往的宗教歷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一個人可以特別信奉某一位神明,而不會因此招致其他神明的憤怒和嫉妒,同樣地,向另一個神明獻祭也不會使自己喜歡的守護神不再眷顧。《聖經》中的神所表現的嫉妒是一種政治情感,源於契約對方的不當行為,而非愛人之間的背叛。盡管在這種語境下經常提到夫妻之愛和通奸——尤其是在《何西阿書》中——這些都只是對政治契約的隱喻。然而,契約本身並非隱喻。它正是事實本身,是宗教——神、人類、社會和世界之間的相互關系——被重塑的新形式。這種新的關系只能與一個神建立,因此是一神論。這並不是說不存在其他神祇,只是說,既然他們被排除在——在契約中立下的——與上帝的新關系之外,那麽他們在政治上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因此,正如《示瑪禱詞》在“亞威獨尊”(JHWH echad)中清楚表達的那樣,“一神教”應該被稱做“一亞威教”(monoyahwehism),才更為適當。亞威是獨一無二的,是以色列與之結盟的唯一神祇。
一神論作為一種反宇宙神論
只有通過理解一神教所排斥的多神教,我們才能理解它的那種革命性與排他性。因為這種一神教並非原生態地從多神教演變而來,而是通過譴責多神教為“異教”而與之決裂的方式。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這種一神教提出一個唯一的真神,他創造並維護世界,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盡管它通過用這個唯一的神取代傳統“異教”中多神教信仰的部落神祇和民族神祇,來支撐其普遍有效性,但是,在廢除多神教所劃定的諸多邊界的同時,它仍然確立了一個新的、更為重要的邊界:真理宗教和謬誤宗教之間的邊界。從此以後,何為“真”只能從何為“非真”的角度來理解,而在埃赫那頓和摩西的例子中,這被確認為“非真”的,就是埃及的傳統宗教。革命性或排他性的一神教是反對多神教的。但這實際上是什麽意思呢?
暫且不論我們是否信仰這位神,我們大家都對一神教的上帝擁有基本的認識。他是世界的創造者,他引導著世界的運行並維持著它的存在,是一位無形、隱秘、靈性的神,他超越時空的束縛。是摩西在阿諾德·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歌劇《摩西與亞倫》中所呼喚的上帝:
獨一無二,永恒常在,無所不在,
無法感知,也無法想象的上帝!
其實這並不是(或者說尚未成為)《舊約》中的神,但這一點在眼下也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勳伯格的上帝更接近於現代的、後啟蒙時代的誓反教和猶太教對神的理解,今天的讀者幾乎可以毫不費力地將這種理解投射回古代一神論,使自己能夠在閱讀《聖經》文本時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然而,多神論宗教的神靈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甚至無法去琢磨,更別說相信它了。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在兩千多年的一神教統治之後,我們已經喪失了這種理解力。在這方面,埃及學(Egyptology)研究或許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它在過去的 180 年中一直致力於讓我們更加了解埃及世界。它的貢獻既不應該被理解為對多神教的支持,也不應該被解讀為對一神教的批判。埃及學是一門文化科學,而非神學。它的目標是獲取知識和理解,並且避免做出任何規範性的評價。研究埃及涉及追溯人類文化發展——至少是西方文化發展——的道路。重構這條路徑並不意味著想要沿著相反的方向重新走一次,我認為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然而,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考慮這條路徑上的岔路口和交叉口,看看我們選擇了哪些選項,放棄了哪些選項,以及哪些選項塑造了我們。在拙作《埃及人摩西》一書中,我試圖展示西方世界從未停止過對古埃及的向往,將其視為被拒絕的另一條道路的縮影。
在我們熟悉的西方傳統中,只有一位上帝。那麽,與這位上帝相比,一個由眾神構成的世界有什麽獨特之處呢?如果我們將世界想象成一個由神、宇宙、人類和社會構成的平行四邊形,那麽我們首先會注意到,一旦上帝被眾神世界所取代,這個平行四邊形就會變成一個三角形。眾神的世界並不與由宇宙、人類和社會構成的世界相對立,而是把它們作為一種建立結構和秩序的原則,賦予它們意義。首先,眾神的世界構成了宇宙,後者被理解為一個由聚斂和沖突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協同過程。對於至少埃及而言,可以說宇宙並不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空間,而是一個每天都在諸神的合作中重新誕生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元性原則如何根深蒂固地被銘刻在這個世界觀之中。如果將宇宙過程理解為單個神的總體計劃,那麽它將失去其協同的特性。其次,眾神的世界構成了社會和國家,因為諸神支配著凡間事務。所有偉大的神祇都是各自城市的守護神;每個重要的定居點都受到一位神祇的庇護。崇拜不過是對作為城市統治者的神明理所應當的貢獻。在政治-宗教的維度中,神明的世界因此決定了社會的政治結構,社會中每個成員對市政、節慶和宗教社群的忠誠,以及定居點與城市之間、城市與省份之間、省份與王室都城之間的關系。通過這種方式,它定義了土地及其所有下轄區域——直至個體公民——的政治身份認同。在這里,我們同樣看到了多元性原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眾神被單一神所取代,那麽這種豐富多彩的社會政治身份將變得模糊不清,變成一個沒有特色的群體。第三,也許對我們今天來說最難以理解的是,眾神的世界構成了人類命運的世界,在它的歡喜和哀傷中、危機和化解中、時代和變革中,只有在與神祇的命運——即神話——聯系起來時,它才呈現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通過講述神祇的故事,神話為人類生活帶來秩序。這個賦予意義的基礎性功能也與多元性原則息息相關。諸神只有在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的情況下,才能演繹出各自的命運。因此,眾神的世界構成了一個宇宙的、政治的和神話的神學體系,它成為一種關於宇宙、市政和宗教律法,以及神話命運的敘述,在這個敘述中,神性首次見諸詞語。
這正是被一神教攻擊的神學體系。多元性無疑是爭論的焦點,但決定性因素並不是數量上的多元性原則,而是神性和凡塵生活的不可區分,正是由此多元性必然產生。世俗世界中的神性被銘刻在自然、國家和神話這三個維度中。多神論是一種宇宙神論(cosmotheism),即認為神性不可被剝離於世界之外。然而,一神論卻下定決心要做到這一點。神被解放,擺脫了對宇宙、社會和命運的共生依附,轉而作為至高無上的力量面對這個世界。與此同時,人也擺脫了與世界的共生關系,在與那位——既存在於世界之外但又面向世界的——獨一神的合作中,發展成為一個自主的(autonomous)——但更為確切地說是從屬於神權的(theonomous)——個體。這正是一神教在心理歷史方面造成的最重要的後果。這就是宗教意義上的“自由”。一神教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自我形象,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神的形象。僅此一點就足以解釋為什麽回歸多神教和古埃及宗教是不可能的。從我們在這個漫長的解放和差異化的歷史中當前所處的階段來看,我們根本無法做到這一點。作為西方人,我們無法生活在一個沒有被摩西區隔分割開的的精神空間中。走出埃及意味著切斷了一根臍帶,這條臍帶是無法被重新連接的。正是通過走出埃及,我們才獲得了自由:擺脫了《出埃及記》所描繪的法老壓迫,也擺脫了一種與世界的共生關系,這種關系在一神教看來,是一種與世界的致命糾纏。同時,走出埃及也意味著,神從其寄存於這個世界的宇宙秩序、宗教秩序、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中的內在性(immanence)中浮現出來。摩西的區隔最終意味著神與世界之間的區隔,從而確立了人與世界之間的區隔。
這種對世界共生關系的抹除,正是《埃及人摩西》德文版中所使用的“沈浸於世界”(Weltbeheimatung)和“拒絕世界”(Nein zur Welt)概念所指的內容,埃里希·曾格公開說這些概念“幾乎無法理解”。當然,曾格完全正確地指出了《舊約》的“時間聯系和現世導向”,並指出“土地”是“神的救贖的最高恩賜。”格哈德·凱澤(Gerhard Kaiser)和羅爾夫·倫道夫(Rolf Rendtorff)也同樣反對一神教否定世界的指控。這一切都是完全正確的,然而這並不等於相信世界的神性。隨著對神和世界的區隔,與世界的距離也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至少在潛在層面,對“世俗”之物出現了一種內在的排斥。
多神教對世界的完全沈浸現在被相對化了。任何以摩西區隔為立場的人,身處於這個世界將不再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從埃及的角度看,歐洲所走的道路是取消與神和世界的共生關系,轉而支持一個超越的神和被神啟示的真理。這條道路上的一些極端落腳點包括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對世界的徹底否定以及誓反教將世界視為“淚水之谷”的觀點。我很樂意承認,古代以色列宗教並不是一種救贖宗教。但這並不是說,在《舊約》的文獻中,有時不會表達出一些日後可以被用來發展出救贖宗教的思想。這樣看來,我們面對的,即便不是一種宗教,至少也是一種遠離塵世的神學——或者更謹慎地說,是神學的萌芽,這與埃及的宗教形成鮮明對比,後者是完全沈浸於塵世的宗教。
一神教的對立面不是多神教,甚至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宇宙神教,這種宗教信仰一位內在的神和一個隱秘的真理,這個真理在千千萬萬種意象中時隱時現,而這些意象之間,彼此並不排斥,而是相互映照,互為補充。我們現在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西方在選擇基督教和一神論時所作的抉擇,以及它所拒絕的選擇;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看到,被一神教驅逐的替代選項——即宇宙神論——一直以來都籠罩著西方的宗教和思想史,甚至在某些階段直擊其核心。例如,歌德的宗教信仰就是宇宙神論——即隱秘的關於神的內在性的真理——而他在這方面絕非個案。文藝覆興時期對古代宇宙神論世界觀的重新發現,以及對古代文本和藝術作品的重新發現,觸發了那些被壓抑的思想的回歸。“埃及人摩西”這個形象便代表著這種回歸。
一神論作為政治神學:倫理、正義、自由
一神教對自身做出的最重要的讚譽之一是其宣稱自己是正義的宗教。根據一神論宗教的普遍信念,道德和法律是隨著對單一神的信仰而首次在世界中出現的。“關鍵在於倫理正是通過《聖經》的一神論(十誡)首次在宗教中出現的——這是一種全新的發展,因為巴比倫、亞述或迦南的神明與這種意義上的倫理毫不相幹。” 在這種表述方式下,這句話並非完全錯誤;但是當作者漢內斯·施泰因(Hannes Stein)意圖將“在宗教中出現”理解為“在世界中出現”時,問題就出現了。首先,一神論是一項偉大的文明成就。異教的神祇規定他們的祭司必須保持聖潔,正確執行儀式,祭品豐富,而《聖經》中的上帝卻唯獨或主要關心正義。人們不是通過油脂豐富的燔祭來侍奉這位上帝不,而是通過公正和仁愛。先知們不知疲倦地強調這一點。的確,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人們很難找到類似的東西。不過,在中王國時期的一篇埃及文獻中確實可以找到以下非凡的句子:“義人的善行比惡人的牛更早被接納。”但隨後文獻繼續說到:“通過鋪滿祭壇的祭品與銘文,來為神行事,有一天他也許會回報你。”在埃及,為了神而行事意味著確保他的祭壇得到充足的供品,對於其他非《聖經》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在一神論中,為了神而行事意味著簡單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神同行”(《彌迦書》第 6 章第 6 至 8 節)。這也是為什麽——一個經常針對摩西區隔概念的反對意見認為——將一神論追溯到真理與謬誤的區別與現實並不相符。這里的關鍵並不是真理和謬誤,而是正義與不公,自由與壓迫。一神論使人擔負起道德責任。
這一異議是完全合理的。毫無疑問,《出埃及記》的主題不是真假宗教的區別,而是奴役與自由之間的對立。在《埃及人摩西》中,我的興趣點不在於《出埃及記》的主題,而是,其中發展起來的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對立是如何在記憶歷史的意義上被理解的,以及它是如何影響到西方傳統眼中的埃及形象的。然而,這個異議仍然很重要,值得更深入地討論,因此我想改變我的調查方向,從記憶歷史的角度轉向釋經學的角度。我同意《出埃及記》的核心是奴役和自由之間的區隔,我們至少可以達成共識,該書的主題是某種區隔。接下來,我要論證的是,《出埃及記》中引入的新宗教首先關注的是自由、法律和正義等主題,因此它關注的是政治神學,並且只有它被定義為真正的宗教。在宗教史上,正義、法律和自由第一次被宣布為宗教的核心議題,並且是上帝獨享的特權,這是摩西區隔的革命性創新之一。謬誤宗教可以通過其政治行為來識別,因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壓迫、專橫、跋扈和不義。一神論基本上是政治神學。我完全同意這一點。盡管,我們不應忘記,《出埃及記》中金牛犢的故事處理的是偶像崇拜而不是解放,但對造像的禁令也給神學-政治的解釋留下了空間,我將在下文中解釋。
當我們不再用“記憶歷史”的視角(即“它們一直以來到底是如何被閱讀的?”)來審視這些文獻,而是根據當前的文獻研究水平來考察它們所要表達的含義,我們就能夠看清一點:走出埃及的故事實際上是上帝啟動的一項政治解放行動。這是從奴役之所向自由之路的進發。雖然“自由”可能不是經文的詞語,也沒有在這個語境中出現,但在西奈山上與上帝立下的契約顯然意在擺脫束縛。在這一點上,我和我的批評者們意見一致,尤其是與克勞斯·科赫(Klaus Koch)和羅爾夫·倫道夫。但若要說摩西區隔只關乎“自由與非自由”有關,而非“真與假”,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自由與非自由”實際上涉及了將要被判定為“真理與謬誤”的內容。謬誤的宗教之所以能夠被識別為謬誤,是因為它征服、貶低和奴役他人。我不認為《聖經》一神教可以被簡化為法律和正義。當然,亞威對窮人受到的不公正感到憤怒,但在《出埃及記》中,讓他最為憤怒的事情是金牛犢,盡管在制作和崇拜它時沒有人受到壓迫和剝削。我的批評者對自由和正義的陳述都是正確的,但他們沒有道出事實的全部。
我的批評者們認為法律是擺脫埃及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束縛的工具,我也同意這種觀點。比起建立新的國家本身,更為重要的,是棄絕另一個國家的原則,以及建立一個抵制該國家的對立社會,令其影響在這個社會中被縮小到最低限度。這種敵視一個國家的沖動體現在反抗埃及的故事中。作為國家權威的縮影,埃及是奴役之所,而不是偶像崇拜之家。當以色列走出埃及並與亞威立下盟約時,它所切割的,並不是謬誤的宗教,而是謬誤的政治:法老的狂妄自大、壓迫性的統治、奴役、剝奪和虐待。提醒那些感到被法律強迫並限制的人:“要記得妳曾在埃及為奴。”從經文內部的角度來看,一神教最初和最主要是將猶太人從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它成為一種替代生活形式的基礎,在這種形式中,不再是一個人統治所有其他人,而是人們自由地組織在一起,服從於他們與神所達成的契約的權威。在敘事層面將一神教的建立與逃離埃及的故事聯繫起來之後,它便看起來像是一場由神支持的抵抗運動。並且,在人民從法老的壓迫中解脫出來的同時,神性和或救贖也被從政治權柄中釋放出來,成為一種神專有的屬性。在這裏,神首次握起左右歴史的權杖。這個故事至少表現出一種將救贖從世俗權力掌控中擺脫出來的傾嚮。從那以後,宗教和政治是兩回事。在協商它們該如何互動時必須謹慎小心,並且它們只能通過暴力才能統一。我完全同意羅爾夫·倫道夫等人將《出埃及記》的“政治神學”視為其主要關註點,而將偶像崇拜問題擺在次要的位置。但從記憶歴史的角度來看,情況卻並非如此。在希臘化時期和古典時代晚期,偶像崇拜作為典型的謬誤宗教,越來越成為關註的焦點;在 18 世紀的神學爭議中,與異教的概念聯繫更緊密的是偶像崇拜,而不是不公不義和壓迫。
這或許是人類歴史上第一個通過暴力將政治主權與宗教救贖強制結合在一起的案例,而巧合的是,它竟與摩西區隔的首次實現同時發生。在整個法老治下的埃及歴史中,沒有比阿瑪納宗教更極端的國家崇拜案例了。這正是埃赫那頓和摩西、埃及一神教和《聖經》一神教相互對立的地方。埃赫那頓用來取代傳統眾神世界的獨一神是太陽,是自然之力,是宇宙能量。在這方面,他仍然停留在宇宙神論的局限裏面。只有埃赫那頓能夠與這個非神話性的宇宙神祇建立個人聯繫。對於他的子民來說,這個神僅僅是太陽,所有的生命都源自於它;它並沒有提供道德導嚮,也不能被用來改變人民的命運——無論是朝著好的方嚮還是壞的方嚮改變。國王自己填補了由此產生的空缺。他將自己獻給人民,成為個體化和私人化的神。任何追隨他並嚮他敞開心扉的人能夠獲得救贖;但是,那些拒絕他的教導的人就要面對他的憤怒:
對於忽視他教誨的人,他展露震怒,
對於聽從他教誨的人,他示以恩寵。
這就是真與假、信徒與異教徒之間的區隔在埃赫那頓那裏的版本。埃赫那頓壟斷了神、人類和社會之間的聯繫,從而恢復並大大加強了對宗教的壟斷,這種壟斷一直以來都以神聖君主制的形式存在,但自公元前 15 世紀以來,在新王國時期出現的新理念削弱了這種壟斷,這些理念相信個體可以直接與神建立關繫並強調個人的虔誠。《出埃及記》的神話故事所針對的法老傲慢和國家崇拜,在埃赫那頓身上達到了最極端的地步。
這絕非巧合,歴史上首次記載的摩西區隔的實現便導致了政治權力和宗教救贖的強制結合。這表明了一神教從一開始就固有一種矛盾性。一方面,伴隨著真理與謬誤的區分,一神教也自然而然地區分了政治統治和救贖。超越凡塵的神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由俗世統治者代表;作為歴史的主宰,他獨自承載救贖的責任。當然,這不是埃赫那頓的太陽神,他既非超越凡塵的,也非歴史的主宰。盡管如此,即使在這裏,真假的區分還是導致了君權和救贖之間的聯繫被徹底改頭換面。獨一神被賦予了皇室頭銜,他的名字被寫在象形繭(cartouche)上,與國王一起共治天下。國王不再像以前那樣在凡間“代表”缺席的神;相反,兩者一同統治,一個是宇宙的力量,另一個是政治和道德的力量。因此,即使統治和救贖有所區別,兩者之間的聯繫也還是得到了加強。但在早期猶太教、基督教,尤其是伊斯蘭教的一神論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強制結合,無論是在神權政體(theocracy)、拜佔庭的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還是在精神領袖篡奪俗世權力的情況下。一神教一次又一次地從政治抵抗運動轉變為統治秩序,而當這種轉變發生時,它的政治神學便輕易地從對國家的批判轉變為對國家的合法化。
然而,如果從其起源來審視一神教,並且從其出現之前的世界的角度來看這些起源,那麽, 那麽摩西區隔的政治意義——或者說政治結果——就很明顯了,它就在於政教分離。埃赫那頓前所未有地強化了神權和救贖之間的密不可分、近乎自然的結合,而這正是摩西所拒絕的法老王權原則。作為神的兒子,埃及法老既是救贖的媒介,也是神在世界中的化身。通過使救贖成為神僅有的特權,並將其從世俗權力的掌控中撤回,一神教確保除了一個必須俯伏在《妥拉》面前並對其晝夜研讀的國王之外,幾乎再沒有什麽君權可言。本質上講,王權消失了;在猶太教中,它採取了彌賽亞主義的末世論形式,而在基督教中,它體現在耶穌基督的形象中,他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在這裏,與世界的象徵性關繫也結束了,不會有人再接受這個觀點:世界固有的神格屬性以政治統治的形式顯現出來。
“異教”世界的法律和道德,以及一神教對正義的神學化
就像“偶像崇拜”一樣,“奴役”也屬於對——站在摩西區隔的的另一邊的——“異教”的批判性構建的一部分。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埃及表現為一個“奴役之所”;但從埃及文獻的角度來看又是如何呢?令人驚訝的是,埃及也將自身看作是實現解放的機構與制度。和《聖經》一樣,埃及語中也沒有“自由”這個詞,但“救贖”這個概念接近於這個術語的含義。國家是“救贖正義”的捍衛者。在世上建立國家正是為了匡扶正義,讓弱者擺脫強者的壓迫。不同之處在於,在埃及,是國家讓人民從自然秩序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而在以色列,則是法律讓人們從國家的壓迫中解放出來。有這樣一篇關於禮儀或“崇拜神學”的古代論述,它討論了國王同時作為太陽神崇拜者的身份,其中的主題便是:國王(和國家)的救贖任務是從世間驅逐不公不義並建立法律。它的最後一段詩節寫道:
太陽神拉將國王扶持於
生者的土地
永遠及永遠,
為人民頒佈法律,滿足眾神,
實現瑪亞特(Ma’at ,正義),摧毀伊斯菲特(Isfet,不義)。
他[國王]嚮神靈獻上祭品
並嚮死者獻上祭品。
因此,國王在人間的任務在於實現瑪亞特並根除伊斯菲特。具體而言,這意味著為人民實施法律,並確保為眾神和死者提供充足的祭品以滿足他們。因此,在埃及人的世界中,正義的概念也被賦予了關鍵作用。然而,這種正義並不僅僅局限於維護“法律和秩序”。我們必須區分“自上而下的正義”和“自下而上的正義”。自上而下的正義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旨在保護統治者免於叛亂、保護財產所有者免於盜竊,以及維護各種秩序免於擾亂。相比之下,埃及的瑪亞特概念指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正義,一種救贖性的正義,它幫助窮人和弱者,那些諺語中所說的寡婦和孤兒。這種正義不是從上嚮下強迫的,而是自下往上推動的。根據埃及人的觀點,它不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國家的存在是為了在人世間實現正義。
《聖經》同樣關心救贖性正義,即自下而上的正義。這是由先知們提出的要求,他們代表神在國家面前發聲。在古代東方世界中並沒有與之相似的情況,這就是為什麽這個觀點看似成立:這種正義觀念是由先知們所宣揚的一神教首次帶來的。然而,在古代近東世界,有一些和針對君王的格言性的文本和鑒戒,提醒他國家的使命是在人世間建立救贖性正義。這些文本的作者不是以神的名義發聲的先知,因為他們只是提供了一些簡單、相對世俗的原則來規範個人和社區生活。在埃及,最著名的例子是一部名為《雄辯的農夫》的文學作品。它講述了一個居住在綠洲的人帶著可憐的幾樣產品前往埃及以換取糧食,在途中被搶劫,現在嚮當地的君主和執法者尋求補償的故事。他在九篇構思精巧、充滿詩意的演講中懇請他遵守瑪亞特原則。這種正義的自下而上的特點已經再明顯不過了。這個綠洲人行使著與《聖經》中的先知相同的功能,提出了相同的訴求,但是他是出於自身的利益,並沒有提及神。
一神教傳統繫統性地遺忘了《聖經》式的正義觀念在《聖經》出現之前的歴史,並堅持認為是《聖經》所實現的轉變首次將正義帶到了世界上。這並非事實,其實正義自古以來就存在於世界中;事實上,很難想象人們在沒有正義的情況下如何共同生活。但正如我們所見,在埃及,正義被置於人類的世界,而不是神靈的世界。雖然神靈渴求祭品,人類卻渴求法律。在其起源中,正義是一種凡塵的或世俗的東西。宗教和倫理有著不同的根源,並且在原始宗教中,它們是彼此分離的領域,盡管相互關聯。只有在一神教中,它們才融合成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這種融合代表了聖經《聖經》一神教最顯著的創新之一,但從埃及學的角度來看,這種發展絕不是理所當然的,這一點再多強調也不為過。埃伯哈德·奧托(Eberhard Otto)寫道,“直到後期階段倫理才在遲疑中與宗教聯繫起來”,而米裏安·利希泰姆(Miriam Lichtheim)則認為,“宗教和倫理一直是,也仍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
在埃及學中被視為不言而喻的事實,在其他學術領域仍然是激烈爭論的話題。那些認為倫理和宗教在淵源和本質上都毫無關聯的人,同樣主張倫理道德可以脫離宗教而存在。皮埃爾·貝勒 (Pierre Bayle)在 1700 年左右提出這一觀點時,引發了群情激憤。甚至伏爾泰也對這一論點提出質疑,調侃道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必須發明一個出來,因為沒有任何其他東西能夠使人尊重法律。但這個問題今天仍然備受爭議,關於法律、道德和正義乃是地上事務而非來自天上的產物這個觀點有時會在神學界引起深深的不安情緒。在過去的幾年裏,我曾有兩次機會在神學家面前闡述我對正義的世俗起源的看法。第一次,它們在一種耐心和理解的氣氛中被討論。然而第二次,2000 年在薩爾茨堡(Salzburg),一位教會人士甚至聲稱,我的立場在邏輯上會導致“墮胎,斯洛特戴克(Sloterdijk)的人類動物園和新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正說明了即使在今天,教會仍然用如此的刻薄(和盲目)態度捍衛一神教與正義不可分割這一教條。
遠非為無神論開閘放水,我的論點——正義的觀念具有世俗的起源——反而保護了《聖經》一神教免受尼採對其提出的指控。尼採將救贖性正義的原則貶斥為“奴隸道德”。他也認為它們是《聖經》一神教的發明,因此將其視為被壓迫者和弱勢群體的宗教,源於他們對取得勝利的希臘羅馬文化的怨恨,而後者代表了高尚、財富、力量和美的更為優越的價值觀。甚至像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這樣的權威人物也在這方面強烈地支持他。如果能夠證明《聖經》救贖性正義原則也存在於古代近東文化的智慧傳統中,並且它們構成了協調個體、社群和國家生活的廣泛基礎,那麽就能夠為《聖經》一神教擺脫這一指控,並進一步證明這些原則與怨恨和奴隸道德完全無關。恰恰相反,我們在這裏所討論的是真正的主人道德,即統治者的道德,他們意識到自己對臣民的責任,他們的主宰感隨著認識到他人需要他們的保護和恩惠而增長。力量和美貌並不能造就一個主人;相反,一個人是通過在依賴鏈的頂端承擔責任而成為主人。這就是為什麽埃及的統治者在他們的墓誌銘中擁護這種道德,即便這表示他們承認了在《雄辯的農夫》故事中下層階級代表所要求的自下而上的正義。
一神教並沒有首創法律和正義;這些都早已存在。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神教的記憶是准確的:一神教可能並沒有像人們有時所說的那樣發明了正義,但它確實首次使正義成為上帝直接關註的問題。在此以前世界上從未見過一個制定法律的神。神是一個監督法律和正義的法官,獎勵正直的人並懲罰不義之徒,這在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是絕對核心的觀念。在埃及,正義是一個帶有神性的概念,但法律和法規是一種人類制度。它們因此是國王的特權,他的角色是頒佈和執行法律,以及在寬大處理的情況下懸置它們。在這樣做時,他並不是在與神爭權,而是在人世間代表著正義的神聖原則。國王在立法方面仍然享有完全的自主。當《聖經》中的上帝以立法者的身份出現時,他奪走的,正是這種立法自主權。他在自己的領域與國王競爭,篡奪了他的位置,將他從行使主權和具有立法王權的寶座上趕了下來。這種形式的統治在《聖經》一神教的世界中不復存在。
因此,一神教聲稱自己主張正義並推行法律的說法並非毫無歴史依據。沒有哪種“異教”宗教把法律作為其首要關切。但是一神教忽視了在舊大陸(Old World)中,國家對法律和正義負有責任,而且恰好也是在救贖性正義的意義上,這種救贖性正義正好也涵蓋了法律和寬恕,這兩者也正符合《聖經》中“神性正義”概念的特點。一神教的成就並不在於引入法律和正義,而在於將法律的源頭從塵世和人類的經驗中,轉移到了天堂和神的意誌。通過“神學化”正義,也就是將正義置於上帝手中,一神教將其提升到宗教真理的地位。正義成為真正宗教的典範。由此,無法無天、道德敗壞和行為不端便成為“異教”的屬性。
這就是為什麽,在《聖經》的描繪中,異教不僅崇拜偶像,同時也無法無天、行為不端。偶像崇拜和道德敗壞往往是密切相關的。從埃及學的角度來看,這要麽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要麽是蓄意的中傷誹謗。像巴比倫人和古埃及人這樣的“異教徒和偶像崇拜者”,也有高度先進的道德觀念,只是對於他們來說,這些觀念並不是根植於宗教,而是根植於其他相對世俗的文化生活領域。除了國家作為正義制度化的形式以外,這裏還需要提及“智慧”這個相關的話語體繫,這些道德觀念正是在其中得以發展、編纂和傳承。《聖經》傳承了古代近東的智慧傳統,有時甚至將整段文字翻譯後編入經文,例如取自埃及的《阿蒙尼莫佩的教導》(teaching of Amenemope)。埃及語中對這一傳統的表達是 sb3jj.t,字面意義是“訓誡,教導”。這些文本要教授的實際上並不是智慧,而是良好的行為舉止,既包括餐桌禮儀,也包括協調人際關繫的嚴肅箴言。相關的埃及詞語是瑪亞特(Ma’at)。瑪亞特是一位女神,所以這並不是與宗教完全無關的領域。正義的領域只是相對而不是絕對世俗的。之所以說它是相對世俗的,是因為有些關於宗教儀式的潔凈的規定並不屬於道德規範之列。在這裏,沒有像不可以在母山羊的奶中烹飪它自己的幼崽那樣的規矩。至於儀式法律的層面,諸如托馬斯·阿奎那的 caeremonialia【儀式法規】或拉比傳統中的 chukkim【典章】[2]這類儀式法律都是缺席的。當然,埃及嚮來也不缺少純潔法規和禁忌,但這些並不屬於一般意義的道德教導。
最初以色列也是如此。在《聖經》中,我們找到了與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智慧傳統中相似的生活准則。這些准則並不具備 mitsvot【神的戒律】——由上帝本人指派的神聖職責——的地位,而這些准則是基於世代積纍傳承的傳統知識所形成的人類生活指南,它們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聖經》將這種相對世俗的智慧與一個象徵性的人物形象——所羅門王——關聯在一起,正如將神聖的神授律法與摩西相關聯一樣。摩西代表著神授律法,其正義形式源自與上帝的盟約,因此也來自《聖經》宗教的核心,即人們必須遵守它,這樣才能保持與上帝的盟約。在英語、德語、法語和其他語言中,這些法律往往以單數形式總結為“法律”(the Law),對應於希伯來語的妥拉(torah)。這個詞的意思類似於“指導”,指摩西的所有五本經書,同時涵蓋了歴史和法律。歴史和法律的聯繫至關重要,因為它保障了法律的專屬性。法律和歴史同樣神聖;它們是上帝選民的法律,其正義正是以這些法律為基石,而不是一般的倫理道德。
所羅門智慧(hokhmah)的俗世性質與摩西律法的排他性質構成了鮮明的對立。各種各樣的格言諺語都進入了《箴言》書,其中包括一整套從埃及人那裏翻譯過來的格言。這些格言智慧集中的知識遍佈在整個東地中海地區。所羅門智慧的內在於世界和相對俗世的特質與摩西律法的排他和神聖的特質形成鮮明對比。當然,在這裏,要對“俗世”這一概念做一些限定。雖然 Hokhmah 可能不像古埃及的瑪亞特那樣是一位女神,但在整個復雜的智慧體繫的頂端,矗立著這樣一句話:“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篇》第 111 章第 10 節;參見《箴言》第 1 章第 7 節;《箴言》第 9 章第 10 節;《西拉書》[3]第 1 章第 14 節),這句話將智慧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之上。在後來的拉比釋經學中,Torah 和 Hokhmah 非常接近,有時甚至被混為一體。但我們在這裏討論的是起源。有一點應該已經很清楚,像埃及一樣,智慧在以色列的起源是俗世的,並且也與祭祀儀式無關。
因此,聲稱“異教”宗教對道德一無所知的說法在其指嚮的意義上錯誤的。道德並不屬於狹義上的宗教,不屬於祭祀獻祭及其潔凈法規。它屬於一個俗世、通常是團體或宮廷智慧的領域。它規範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共處,而不是他們與神靈的互動。因此,我的觀點是,正義並非從宗教中孕育而生的,而是從外部被引入宗教的。這樣,不僅僅是宗教被倫理化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正義也被神學化或神聖化了。這一過程在從埃及的角度觀察時最為清晰。因為古埃及的文獻不僅僅展示了道德的相對俗世的起源,而且道德的神學化過程也初見端倪。
埃及人邁嚮正義神學化的一步表現在死者將要接受審判的觀念上,這個觀念在大約公元前三仟紀末到兩仟紀初之間開始被人們接受。有了這一觀念,正義被置於神聖的基礎上。即使君主有時在履行其神賦使命——即確保在人世間實現正義——時偶爾會失敗,沒有,個體在死後仍必須在神祇面前出庭,回答他生前的所作所為。然而,這些審判程序所依據的規範與社會生活的規範別無二致:不殺人、不偷盜、不撒謊、不淫亂、不辱罵國王、不藐視神明、不煽動叛亂、不侵佔神廟財產,以及更微妙的行為,諸如不在官府面前詆毀任何人、不施加痛苦、不使人挨餓、不使人哭泣、不虐待動物、不在每日之初增加預先規定的工作量、不咒罵爭吵、不竊聽、不擠眉弄眼、不動怒、不暴力、不傲慢,以及不對真理之言充耳不聞。
因此,在埃及,將正義神學化的真正一步並非在於國家的介入,而是在死者將要接受審判的觀念中。由此,倫理規範被置於神學的立足點上。然而,在這裏,神明仍然以法官的身份出現,尚不是立法者。這一差異至關重要。因為埃及神明審判死者所依據的法律並非神授法律,而是人類的智慧。神明按照與人相同的標准進行審判。因此,與他人和諧共處的人也與神明和諧共處。《聖經》在這裏做出了明確的區分,闡述了一個深刻的觀點,即為了正義,同樣有可能受苦受難。只有在神明既為立法者又為法官的宗教背景下,人才會開始思考人的判決和神的判決有可能大相徑庭。這是《聖經》一神教的真正創新之處。
一神教將原本存在的法律和道德傳統神學化——將它們置於上帝手中——並將它們建構在其經典的三層結構的核心位置。《妥拉》,作為上帝的指示,它享有絕對的、超越時間的權威。在《先知書》(Nevi’ im)中,這些永恆的、來自上帝的教導與特定的時代聯繫起來,以一種歴史性的方式被解讀。在《聖錄》(Ketubim)中,優美的文學作品與世俗的智慧被收集起來,作為一種崇敬和虔誠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形式。只有在這個層面上,才能在古代東方文化中找到相似之處。即使是《漢謨拉比法典》(Codex Hammurabi),在其接受史中,其權威也未曾達到能與《聖錄》相媲美的水平。《妥拉》和《先知書》是獨一無二的。宣告和頒佈特定法律的王室法令大多是口頭傳達的;無論如何,它永遠無法擺脫時間和環境的束縛。新國王一登基,他就會頒佈不同的法律。正義是永恆的,但法律隨著世代更叠而變化,這些變更體現在君主和司法官員身上,卻不會在神聖經文之中。
通過將法律神學化並將其提升到神授法律的地位,一神教讓人們擺脫了這樣一個幻覺:如果沒有國王主持正義,他們就會互相殘殺。於是,此前從未受質疑的正義與國家(以及王權和救贖)的聯結便走到了盡頭。這種解放和自主的的精神應該堅決地保存下去,以免我們陷入錯誤的信仰,即認為:如果沒有一位時刻監視我們並深入我們內心的審判之神,就無法在世間實現人類尊嚴和人權。人類肯定永遠不會實現一種共同的宗教。但如果宗教和法律有不同的根源,那麽,我們最終將能夠確立一套共同的法律原則的希望仍然存在。在決定這些原則的討論中,倡導正義的宗教將發揮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前提是,它與其他——致力於同一目標的——“世俗”的聲音協同合作,而不是要去淹沒這些聲音。
第三章:記憶的沖突:偶像崇拜與毀像主義之間
麻風病人的傳說與埃及的阿瑪納創傷
在我關於摩西的拙著中,有一個論點遭到了特別猛烈的攻擊,簡言之,就是反閃族主義最早起源自埃及的反一神論。而一神論本身,最初是反宇宙神論。它針對的是對世界的神格化,這暗含著對統治的神格化。這一論點基於一種假設,即在整個一神教的歴史中存在著一條隱秘的記憶痕跡,可以一路追溯到埃赫那頓時期,遠遠早於《聖經》先知一神教的出現。但是,如果不假定阿瑪納宗教對《聖經》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我們該如何理解埃赫那頓在這段歴史中的角色呢?許多批評者指出,埃赫那頓與先知之間在時間上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並且阿瑪納的記憶在後來的埃及傳統中也消失殆盡,因此否認了阿瑪納與《聖經》之間的任何聯繫。但是,與弗洛伊德不同,我並不主張埃赫那頓與摩西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繫——即《聖經》一神教的起源。我甚至不主張在埃及或迦南的某個地方,阿瑪納宗教的殘余和回憶仍然存在並間接影響了先知一神教的發展。我的觀點是,埃赫那頓和摩西是在後世才被聯繫起來的。在我看來,一段被錯置的,阿瑪納時期的傳奇記憶確實在埃及流傳了幾個世紀——盡管這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並且在希臘化時期,當埃及人與猶太一神教接觸時,他們將這段記憶與摩西和猶太人聯繫在一起。埃及人對他們所遇到的猶太形式的一神教表現出過度的敵意,因為當他們相遇時,埃及人早已形成了一種反一神論的預設立場。我認為,他們從阿瑪納時期保留的唯一記憶,就是一種針對任何形式的毀像運動的焦慮和仇恨交織在一起的情結。這一情結反映在了曼涅托(Manetho)所講述的關於麻風病人的傳說中。因此,埃及的反閃族主義源自反一神論,可以用從阿瑪納時期潛伏下來的心理歴史後果來解釋。
為了證明這一論點,我需要重新審視一下“麻風病人傳說”,在《埃及人摩西》第二章中我已經詳細討論過這個傳說。約瑟夫斯(Josephus Flavius)在他的小冊子《駁阿庇安》(Contra Apionem)中摘錄了這個傳說。在這個文本中,約瑟夫斯斥責了一些希臘化歴史學家,其中大多是埃及裔,他們以一種攻訐的方式重新講述了猶太人的《出埃及記》的故事,歪曲了經文原文的敘述。阿庇安(Apion)本人是這本反猶太宣傳文集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所以約瑟夫斯的作品特別針對他。約瑟夫斯編纂的資料讓我們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原來反猶傾嚮的淵源集中在埃及。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亞歴山大時期的埃及,有大量被用來反猶的核心陳詞濫調被創造出來,這些陳詞濫調一直流傳至今,且名聲不佳。這個案例很重要,因為它表明對猶太人的仇恨遠比基督教要古老得多,基督教後來在這整個陰險的曲目中又添加了一些自己獨創的刻闆印象。
這種前基督教時期,尤其是源自埃及的反猶主義現象,學術界已經給予了充分的關註。最近幾年,柏林猶太學者彼得·謝弗(Peter Schäfer)和以色列古代歴史學家茲維·亞維茨(Zvi Yavetz)分別撰寫了關於這一主題的專著。學界普遍認同,反猶情緒曾在亞歴山大港的多元文化氛圍中盛行,而當時,一個強大的猶太移民社群與希臘人和埃及人共同生活在那裏。這些群體之間並非總是和諧融洽的,這有時會產生強烈的敵意,特別是埃及人這邊,他們已經對被視作土著居民感到不滿。爭議只在於如何解釋這場沖突的起源。一些學者認為這種對《聖經》一神教的反應始於埃及,後來擴大到廣泛的異教,由於《聖經》一神教的真理觀的排斥性,它將所有其他宗教都視為偶像崇拜。例如,阿莫斯·芬肯斯坦(Amos Funkenstein)將這些歪曲《出埃及記》的記述視為一種“反歴史”(counterhistory),是對《聖經》歴史學的有意扭曲,旨在通過顛倒猶太教奠基性的敘事來毀掉猶太人的自我形象。彼得·謝弗則反對這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t)的解釋,堅持這一過程的歴史偶然性。他認為這並非是任何“事物的本質”導致的必然結果,而只能通過結合特定的歴史形勢和事件來解釋,因此他認為可行的解釋只能是歴史性的,而不需要引入像“猶太教的本質”(essence of Judaism)或“埃及人的特質”這樣的偽命題。無論如何,他都想——當然,出於最純粹和最明了的動機——避免讓猶太人來為他們所受到的仇恨負責任。猶太人自身的看法則不同;他們知道“在西奈山上,仇恨降臨到了世界各民族身上”,並且出於對《妥拉》的愛戴,他們主動肩負起這種仇恨。這使他們確信他們的苦難並非徒勞,而且對於他們而言,其中蘊含著一些東西,它們超越了歴史的盲目偶然性。這種本質主義並不代表反猶太主義的陳詞濫調,而是一種猶太教內部用來給歴史賦予意義的主題。
即便我自己的解釋聽起來同樣“本質主義”,但我不再是從猶太教的“本質”中尋找沖突的核心,而是從埃及的“本質”中,更確切地說,是在起源於阿瑪納宗教創傷的一繫列創傷性經歴中尋找。在此,我想再次為我的解釋辯護,這個解釋主要是基於來自曼涅托的證據。曼涅托的版本與該傳說的所有其他版本之間存在一個意味深長的偏差,而我的論點就建立在這個偏差上。其他版本都提到了猶太人,曼涅托在他的敘述中卻沒有。唯一的聯繫是一個註解,它很顯然是後來才被插入敘述中的。
曼涅托講述了一個名叫奧薩西夫(Osarsiph)的埃及祭司的故事,他在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ophis III ,埃赫那頓之父,他的名字被從國王名單上抹去)時期成為了一群麻風病人的領袖。國王將這些麻風病人關押在集中營並強迫他們做苦工。一個預言警告國王說,這些麻風病人將玷汙土地,從而阻止他——阿蒙霍特普國王——見到神明。奧薩西夫與國王談判,獲得了搬遷到阿瓦裏斯(Avaris)的許可,它位於東三角洲,曾經是喜克索斯(Hyksos)人的都城。在那裏,他將他的人組織成為一個麻風病人殖民地,並為他們制定了法律。第一條是不得崇拜神靈,第二條是不放過任何他們奉為神聖的動物,也不得戒食其他在埃及被禁止的食物。第三條禁止與外界人接觸。最後,我們讀到,奧薩西夫取名為“摩西”(Moyses)。正是通過這個註釋,曼涅托本人或他的讀者約瑟夫斯以此建立與《出埃及記》的聯繫。被彈壓的異端國王和猶太的首席先知因此被合並成一個人物。此外,化名為摩西的奧薩西夫加強了城市防禦,徵服了埃及,並在 13 年間以極盡的殘酷手段統治整個國家。麻風病人摧毀了城鎮和寺廟,將聖所變成了廚房,並在烤架上烤制神聖的動物。13 年大致對應於埃爾-阿瑪納的定居期。相關事件發生在阿瑪納時期。這個傳說顯然保留了對阿瑪納時期一神教事件的模糊和脫節的記憶,它毫不含糊地描繪了其毀像運動的性質。
曼涅托從反面闡明了摩西區隔,即從異教徒的角度。在他的敘述中,不得崇拜其他神靈的戒律變成了完全禁止崇拜任何神靈。禁止造像則變成了搗毀神像和屠宰神聖動物的戒律。律法中涉及的自裁式的排他規定成為了不得與外邦人交往的禁令。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這裏第一次遇到了關於疾病的話語。從傳統宗教的立場來看,它建立在純潔和汙穢區別之上,新宗教被視為最嚴重的不潔形式,如同麻風病一樣。教父們吸取了這樣的措辭,並將其反過來應用於異教徒和偶像崇拜者。優西比烏(Eusebius)稱之為“埃及病”,狄奧多勒(Theodoret)稱之為“希臘病”。在他們看來,偶像崇拜是一種瘟疫,尤其是一種成癮現象,要通過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戒除程序來根除。在疾病的語境中,特別是在成癮的隱喻中,我們發現了一種對一神論宗教創傷性方面的敏銳認知,以及其對真理與謬誤的區分。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埃及人的反閃族主義確實是基於一種壓抑,因此是基於一種集體的心理失調。在面對猶太一神教時,埃及人經歴了被壓抑記憶的回歸,對此他們訴諸於激烈的否定機制來應對。
曼涅托的敘述嚮我們展示了“創傷”、“壓抑”和“潛伏”等概念如何可以既指涉心理現象,也指涉文化現象。對埃赫那頓的壓抑表現為徹底抹除阿瑪納時期的一切痕跡,包括將他的名字從國王名單中除掉,使後人無從辨識、斷代和定位當時的創傷性記憶。因此,這些記憶變得越來越模糊和傳奇,陷入一種潛伏的狀態。經過一兩代人後,人們不再知道這場神權革命背後的那個名字。盡管如此,埃赫那頓的名字和個性並沒有被完全壓抑;在奧薩西夫的面具下,記憶痕跡在大眾記憶中被保存下來,形成一個“密室”,並最終使人們將埃赫那頓與摩西聯繫起來。
約瑟夫斯將麻風病人傳說解讀為對《出埃及記》故事的汙蔑性扭曲,這是一個經典的誤讀案例。尤為值得註意的是,所有那些——像約瑟夫斯本人一樣——無法破譯這個傳說對埃及歴史的影射的讀者,都延續著這種誤讀。因為曼涅托毫不含糊地告訴每一位知情的讀者,他所描述的,是與他在別處講述的驅逐喜克索斯人完全不同的事件,而約瑟夫斯正是將後者與以色列子民的出埃及聯繫在了一起。曼涅托將麻風病人傳說的時間定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時期,距離喜克索斯事件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因為他將智者阿蒙諾菲斯(Amenophis[1]),帕皮斯(Paapis,即海普(Hapu))之子,做為故事的主要人物之一。曼涅托可以假定他的讀者中有人了解這位歴史人物,因為在他寫作的時代,這個人物仍然受到崇拜。但是約瑟夫斯不再能理解這個歴史掌故,這就是為什麽他將這兩份敘述混為一談的原因。約瑟夫斯將它們看作是對同一事件的描述:一個是喜克索斯人的故事,它被精心傳抄並可靠地保存了下來;另一個則是以口頭流傳的傳說形式保留下來的麻風病人的故事。
非埃及學出身的讀者,例如阿莫斯·芬肯斯坦、彼得·謝費爾和弗朗茨·馬切耶夫斯基(Franz Maciejewski),也都步了他的後塵。他們忽視了對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提及,因此忽略了阿瑪納時期的往事,將麻風病人傳說解讀為希臘化文化對出現在亞歴山大港的猶太教的反應。然而,對於有埃及學背景的讀者來說,對阿瑪納時期的暗示則再明顯不過:以阿蒙霍特普三世為時間基點、持續了 13 年的恐怖局勢,尤其是沖突本身毋庸置疑的宗教性質。沖突的核心不在於政治,而在於宗教;不在於剝削和壓迫,而在於摧毀埃及的多神教,其最核心聖所——至聖所——便是在對神聖動物的崇拜之中。這些細節既不符合喜克索斯時期,也不符合希臘化時期,而僅適用於曼涅托為這些事件推定的年代。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緊接在阿瑪納時期之後,一場大規模的瘟疫肆虐了整個近東地區長達二十年之久,那麽在傳說的每個版本中都提到的疾病——無論是瘟疫還是麻風病——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那麽,一個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為什麽曼涅托提到的是奧薩西夫而不是埃赫那頓——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子——以及為什麽他將這場由國王詔令發起的新宗教的建立——即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描繪成了一場麻風病人的起義。我的解釋是,這其中對歴史事實的歪曲正是壓抑導致的結果,即有關埃赫那頓的記憶被抹殺後的結果。在阿瑪納時期結束後,埃及回歸到被埃赫那頓禁止和迫害的傳統宗教,他的名字被從國王名單上除去,他統治的痕跡被盡可能地徹底抹除。從此以後,這些記憶再也無法被准確地定位。人們不再知道是哪位領袖發動了這場改革;也忘記了他們自己的君王竟然令人遺憾地牽涉其中,並借助疾病的話語來描述那個不可名狀的異端,將其描繪為埃及(順便說一下,也包括以色列)所知的最嚴重的不潔形式:麻風病。
唯一剩下的問題是,一個被官方歴史拒之門外、被從國王名單上抹去、也沒有任何幸存的遺跡或紀念碑等實物支持的記憶,如何能夠——盡管以一種嚴重扭曲的形式——被保存一仟多年,甚至流傳到曼涅托的時代?以下三點可以支持這一假設。首先,對阿瑪納宗教的迫害絕對沒有成功地摧毀它所有的紀念碑。阿瑪納的邊界石碑保存完好,私人墓地也沒有遭到破壞,而且誰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建築施工等過程中還有什麽其他的發現;畢竟,我們目前對這一時期的了解來自於數量可觀的文獻資料。對於埃及人來說,在阿瑪納邊界碑上描繪的人物一定顯得神秘、令人生厭,甚至可能身體畸形,看起來是形狀怪異的“異類”,這些都可能為類似麻風病人傳說這樣的故事提供了素材。第二,許多對於阿瑪納記憶的抹除工作的痕跡仍然留在較早的紀念碑上。我在這裏所說的“壓抑”,並不是指這段時期的記憶在一夜之間消失,然後又在仟年之後從集體無意識的深處湧現,而是指這些記憶被邊緣化和妖魔化了。第三點,這個傳說想必在早期就與有關喜克索斯人的記憶聯繫在一起,而且這些記憶被篡改的程度不亞於兩者相互交織的程度。喜克索斯人是來自巴勒斯坦南部的入侵者,於公元前 17 和 16 世紀建立了一個帝國,並建都在東三角洲的阿瓦裏斯,他們統治下埃及並嚮上埃及徵收貢金。考古和碑銘的證據並沒有顯示他們實施過恐怖統治或造成過巨大的苦難。直到他們被驅逐再又經過兩代人之後,哈特謝普蘇特(Hatschepsut)女王才在她的一份銘文中將他們描繪成如下形象:
我已重振衰朽之物,
並重建破碎之物,
(甚至)從亞洲人在北地的阿瓦裏斯初現之時起,
(隨著)混跡於其中的遊牧部落,推翻了所建之秩序;
他們的統治不尊奉太陽神,
他並非奉神諭而治,直到我這威嚴的自己,
我被堅定地擁立在太陽神的王座之上。
預言稱在未來的一個時代,我將
成為一個天生的徵服者(“她崛起,她徵服”)。
在拉美西斯(Ramses)王朝時期——因此必然發生在阿瑪納時期之後——出現了一個故事,將喜克索斯國王阿波菲斯(Apophis)描繪成一位一神教徒,“除了塞特(Seth)之外不崇拜任何神或女神”。想必直到這個時候——也就是阿瑪納時期後再經過兩三代人——在近期經歴的影響下,關於喜克索斯人的記憶才開始帶有宗教沖突的性質。由此,便形成了一種關於宗教狂熱時代引發深重苦難的傳統認知。這些記憶並沒有被遺忘,而是繼續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被反復講述,並融入了新的經歴,例如十九王朝末二十王朝初的“敘利亞陰謀”,亞述和波斯的徵服,以及外族人的統治,最終被固化在猶太人身上。
然而,在我看來,這裏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一段記憶如何能夠跨越仟年保存下來,而是創傷如何能夠產生如此持久且深遠的影響。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記憶的穩定性,而在於創傷化的持久性。曼涅托敘述的一神教改革十三年的經歴,深深地烙印在了埃及人的文化態度中,以至於他們對猶太人產生了恐懼症般的反應。
那麽,為何這段經歴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創傷,這一點仍需解釋。畢竟,這裏並沒有涉及到外來侵略者。埃赫那頓引入埃及的一神教是一種太陽神崇拜,而埃及人——盡管並沒有否定其他神靈的存在——一直將太陽神視為至高無上的神靈。然而,這恰恰正是埃赫那頓的偉大革新。問題並不在於引入的新神,而是對舊神的禁止和迫害必定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在埃及人的思維方式裏,世界的存續有賴於儀式被按時並正確地執行,可突然之間,這些儀式被永久取消,慶典被廢除,聖所被褻瀆,神像被搗毀,崇拜被禁止,祭司被迫害,由神靈和規範構成的整個傳統宇宙觀都被斥責為謊言和欺騙,是魔鬼的作為和偶像崇拜,在這裏,我們自身的後殖民時代的經驗讓我們得以理解這些突然的變革對傳統埃及人意味著什麽。埃及人或許是歴史上第一個遭遇這種經歴的民族,它發生在公元前 14 世紀。除了創傷之外,我無法想象這還會是什麽。讓我重申,這裏決定性的因素不是神的唯一性的觀念,而是虛假神明的觀念,即存在虛假宗教的觀念,一個並非為了補充和增強其他真理的真理觀念,而是以其自身為標尺,將其他一切都貶斥為謬誤的真理觀念。作為首個區分真假宗教的人,埃赫那頓領先於他的時代,並且在他同時代人眼中,他必定顯得像個異端、褻瀆者和瘋子。
一旦我們揭開了麻風病人傳說——通過它與阿馬納時期的聯繫——的真實歴史背景,它便呈現出另一番光景。它不再是約瑟夫斯所描繪的那種對猶太人惡毒的誹謗。在這裏涉及的是反一神論,而不是反猶太主義。一神教信徒被描繪成無神論者和偶像破壞者,因為這種新宗教形式的標誌性特徵不是崇拜某個新神,而是——我再說一遍——對舊神的迫害。雖然這個傳說可能達到了最大程度的批判性,但它並不是真對猶太教,猶太教只是禁止自己的信徒崇拜其他神,將自己排除在其他民族之外,並沒有迫害其他神靈或排斥其他民族。相反,這是由阿瑪納時期的大規模毀象運動引發的一種反應。
弗朗茨·馬切耶夫斯基特別批評了這個論點,他不願將埃赫那頓納入在摩西區隔的記憶歴史之中:“摩西區隔應該被局限在它在字面和精神上所屬的地方”,即猶太教。我認為摩西區隔的記憶歴史線應該被延伸到埃赫那頓,並將反猶太主義追溯到比猶太人更古老的反一神論思潮,他懷疑在我的這一主張背後,是“後納粹集中營時代盛行的一種負面且愚昧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既有的偏見使其“熱衷於剝奪猶太人創立一神教的責任(並將其轉嫁給其他人——即埃及人),就好像這種奉獻被誤解成為了一種指責似的。” 但這恰好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論點,只不過當時他的興趣焦點顯然不在此處。當然,我並不想否認猶太人創立一神教的功勞。我只是想指出,如果以對其他神靈的否定作為定義一神教的標准,那麽埃赫那頓必定是第一個創立一神教的人,而且,在新宗教被建立的時候,一神教對其他神靈的憎恨以及反一神論對“阿瑪納的惡徒”(正如拉美西斯時期銘文中對埃赫那頓的稱呼)的仇恨都已經顯露無疑。馬切耶夫斯基後來認同了我將曼涅托的文本解釋為阿瑪納記憶錯置的觀點,並提出了一種比我自己還更為大膽的方式將埃赫那頓納入一神教的記憶歴史中。他認為:“芬肯斯坦所指責的——希臘化時期的學者在扭曲《出埃及記》時所採用的——反歴史操作,首先就表現在《出埃及記》自身的敘述中。”馬切耶夫斯基認為,《出埃及記》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反歴史敘述,是對埃及的傳說(它將喜克索斯人和阿瑪納經歴融合在一起)的一種回應。“這意味著,早在曼涅托之前,喜克索斯人和阿瑪納的記憶就已經在《出埃及記》的核心歴史記憶中被聯繫在一起:作為猶太人記憶的一部分。因此,毫無疑問地,是猶太人自己,在他們的起源神話的埃及情節中,將其自身視為喜克索斯人的繼承者和埃赫那頓的子民。”《出埃及記》的敘事確實呈現出反歴史的所有跡象,或退一步,絕對帶有“顛倒敘事”的跡象,至少在與喜克索斯人有關的敘述中表現為如此。它將國王變成了奴隸;將驅逐變成了移民禁令;將從王座到無名之輩的淪落改寫成為從被壓迫到走嚮自由並成為上帝選民的升華。阿瑪納時期的信件證明巴勒斯坦積極參與了當時發生在埃及的事件,考慮到這一點,為何不將埃赫那頓的一神教改革的記憶也納入到這個記憶歴史中呢?我不想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我在這裏主要關心的是反一神論和反閃族主義之間的區別。
只有最初的傳說才應該被解釋為受喜克索斯時期的歴史影響而形成的關於阿瑪納的錯位記憶,曼涅托的版本或許也可以這樣被解讀,盡管也有可能正是他將其與猶太人關聯起來的。後世的人在吸收了不同版本後,將它僅僅與猶太人的《出埃及記》聯繫起來,約瑟夫斯發現了這些記述背後的詆毀意圖,在這一點上他是完全正確的。所以,存在於埃及的反猶太主義是不容忽視的。我們能夠用埃及人的“阿瑪納情結”加以解釋,即他們對任何形式的偶像破壞都存有恐懼,到了古埃及晚期,這種態度與圍繞神聖動物的崇拜聯繫尤為緊密。猶太人對埃及神聖動物和無數神像的批判態度觸動了埃及人的敏感神經。就像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印度的聖牛一樣,在波斯和希臘佔領時期,埃及的神聖的動物成為民族宗教認同的核心象徵。麻風病人的傳說描繪了一個噩夢般的場景,在外族人統治的條件下,它顯然既普遍也充斥著敵意:即埃及人的世界可能有一天終因屠殺神聖動物、搗毀神像和褻瀆祭祀而以暴力終結。如今有大量證據表明,存在一種埃及特有的末日啟示性敘述,描述了這樣的場景。從後來的事件來看,埃及人知道他們在談論什麽,因為事實證明,給他們的文化帶來毀滅性打擊的,既不是波斯人,也不是希臘人和羅馬人,而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他們的衰落標誌著的是一神教真理的勝利,而非政治暴力。
一神教的真理並非帶來了仇恨本身,而是產生了一種新形式的仇恨,即一神教信徒對於舊神的一種毀像主義(iconoclastic)與毀神主義(theoclastic)式的仇恨,他們宣稱這些舊神都是偶像,以及那些被摩西區隔所排斥並貶稱為異教徒的人所滋生的反一神論仇恨。澄清這一點並不意味著渴望回歸到尚未被摩西區隔所分割的世界。這只是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沖突,並加深我們對後來的西方歴史中它重新出現的多種形式的認識。在這方面,區分反一神論和反猶太主義可能會大有裨益。
我所講的“反一神論”,指的是一種針對摩西區隔的態度,即針對真理和謬誤宗教的區隔。值得註意的是,這種態度自古以來就一直與對神性統一的強烈堅持相輔相成。與一神論相反的立場並不是宣稱“神是為數眾多的”,而是:“神是唯一的,且神即一切”。因此,將它稱為多神論會產生誤導。重要的不是神靈的多元性,而是,當它在世界之內顯現自身時,這種顯現的形式的豐富性和完整性不受任何教條界限的限制。本質上講,這裏的問題是世界本身的神格。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一神論在神和世界之間劃定了一條嚴格的界線。古代反一神論主義(anti-monotheism)所反對的,正是這條界線,並稱其為毀像主義(iconoclasm),或者更確切地說,毀神論(theoclasm)。這就是為什麽我建議在這裏使用“宇宙神論”而不是“多神論”的原因。
毀像主義與偶像崇拜
從埃及人的角度來看,對造像的禁令具有雙重含義。其中一方面具有政治性質,它反對國家在人間代表神的主張。根據埃及人的觀點,神是遙遠而隱匿的。他們從世界退隱出去,無影無蹤。然而,他們在人間建立了國家,來替代他們的真實存在,並通過國王、雕像和神聖動物的形式代表他們。只要國家存在,神就會繼續棲居在他們的雕像中,並維持在內在世界的共生關繫。因此,國家同時也是一種教會。它的主要任務是確保即使在神靈遙不可及的情況下,世界與神之間的聯繫仍然不會被切斷。媒介和代表取代了神的物質性存在。國家和宗教、寺廟、儀式、雕像以及圖像都可以令神明顯靈,並通過符號的力量與之建立間接的聯繫。埃及人曾經借由神話來想象和描述出人類與神明之間的親近關繫,它是一種原始、直接和互惠共生的聯繫,在這種關繫所在之處,出現了一個由文化形成的親近空間,它建立在符號媒介和代理的可能性之上。國家是這種讓人能夠親近神明的機構。法老則作為造物主的代表在人間統治。
在埃及,國王可以通過保障人世間的正義來代表造物主和太陽神拉。在他對人民的執法統治中,國王炮制了至高神對其余眾神的統治,並從這種相似的關聯中獲得權威。國王的統治並不與神競爭;相反,它復刻了相同的統治並以之為前提。然而,神權需要通過國王和國家機構在人間維護其權威,因此要依賴於圖像在人類世界的視野中代表它。這就是代表性政治神學的原則:統治者代表著神的形象。因此,在埃及,“神的形象”是一個常見的皇室頭銜也就不足為奇了。在《聖經》一神教眼中,法老的異教崇拜的虛假恰好就顯露在用替代物代表神靈的方面,即國王、聖像和神聖動物的層面。這就是神像必須被禁止的原因。《聖經》中對造像的禁止帶有這樣一種政治含義,而迄今為止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在禁止造像的禁令背後,真正的用意是對“虛假政治”最激烈的否定。在以色列周邊的近東國家中,尤其是在埃及,神靈也以統治者的身份出現。他們作為帝國神靈統治著整個國家,例如亞述的阿修爾(Assur)、巴比倫的馬爾杜克(Marduk)、埃及的阿蒙(Amun)或阿蒙-拉(Amun-Re),或作為城市的神掌管著整個城市,例如尼普爾(Nippur)的恩利爾神(Enlil)、烏魯克(Uruk)的伊什塔爾女神(Ishtar)、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的太陽神拉、底比斯的阿蒙神和雅典的雅典娜女神。然而,這些神並非直接和親自統治,而是間接地統治。他們主要是統治其他神靈,而不是統治人民。在人世間,他們的這個統治職能則由國王代表。在政治維度上,禁止造像所要革除的,正是這種代表形式。禁止造像首先意味著神不能被描繪刻畫。與神的契約確保了他允諾的真實臨在,而神像與這種臨在並不相容,即神的在場感以及他積極與世界互動的政治形式。圖像是一種媒介,通過它,神靈被神奇地召喚。然而,活著的神不能被變戲法般地召喚;他會在自己選擇的時間以自己選擇的方式現身。同樣,神也不需要一個國王來代表他行使法官和立法者的職責。這就是禁止造像的政治含義。
除了其他方面外,一神教對造像的禁令還意味著對宇宙神論(Cosmotheism)的否定。描摹被視為一種崇拜行為。人們應該避免描摹這個世界的事物,以免陷入崇拜它們的陷阱。這就是人類應該統治世界的原因:倒不是為了剝削世界,而是為了防止它被變成崇拜的對象。
除了政治意義之外,對造像的禁令還有一個超越政治範疇的更為普遍的含義。它直接針對神像本身的。禁止的名目包括:
……雕刻偶像,仿佛什麽男像女像,
或地上走獸的像,或空中飛鳥的像,
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魚的像。
又恐怕妳嚮天舉目觀看,見耶和華妳的神為天下萬民所擺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萬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
耶和華將妳們從埃及領出來,脫離鐵爐,要特作自己產業的子民,像今日一樣。
(《申命記》第 4 章第 16 至 20 節)
對造像的禁令還具有一層更為深遠的含義,它禁止了一切圖像的表現形式,針對的是宇宙神論中與世界的共生關繫;它反對將圖像作為一種禁錮內在精神世界的方式。人類被置於創造物之上,而不是與它們融為一體。人類不應因意識到自身的脆弱和依賴性而崇拜世界,反倒應該自由獨立地統治它。甚至“統治大地”的誡命本身也將圖像的概念與一繫列生命形式並列在一起: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世記》第 1 章第 26 節)
在上帝後來與挪亞達成的契約中也使用了類似的話語: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妳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
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妳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裏一切的魚,都交付妳們的手。
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妳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妳們,如同菜蔬一樣。
在其自由、獨立和責任之中,人是神的描摹。神的領域是人類無法控制的,所以,如同“統治大地”一樣,造像禁令旨在將世界從這個領域中抽離出來。人有責任自主地掌管這個世界。通過這樣做,人類承認了世界不具有神格,或者更准確地說,承認了只有超越塵世的神才具有神格。統治與崇拜是相互對立的。這同樣適用於圖像。物質應該被操縱而不是被崇拜。圖像不應該被崇拜,因為那將意味著崇拜這個世界。
對造像的禁令因此具有雙重含義:它摧毀了國家借以將自身合法化(或自稱合法化)為教會的代表機制,使其無法在人間代表神;它破除了世界的魔力,否則它會對人類下咒,使其疏遠神。搗毀神像等於破除神靈:神像和被崇拜的神靈一起被粉碎。這裏我們所描述的世界尚未形成不涉及利害而純粹以愉悅為目的的藝術和審美的概念。神像是為了崇拜而建造的,是為了在凡人和神靈之間建立聯繫。一神教排斥多神教並將其視為異教,多神教崇拜的是一個具有神格的世界,而非一神教所信奉的唯一真神。然而,誠如我之前所言,異教的神性世界並非站在“世界”——指宇宙、人類和社會的一切總和——之外並與之對立,而是一個從內部充盈世界的原則,賦予其結構、秩序和意義。因此,神性世界以一種宇宙的、政治的和神話的神學來表達自身,並構成一套關於宇宙、城邦和宗教秩序的話語,以及關於神話命運的話語,在這些話語之中,神靈被言傳。我們再次看到,在摩西對真理宗教和謬誤宗教所作的區隔背後,最終是神和世界之間的區隔。
一神教對於崇拜偶像的宗教的批判,始於《耶利米書》第 10 章,《以賽亞書下卷》第 44 章,以及《詩篇》第 115 章,到了希臘化時期則延續在《智慧篇》四整章、斐羅(Philo)的長篇論述《論十誡》(De Decalogo)和《論特殊法律》(De Specialibus Legibus)、《密釋納》中的《外邦崇拜》(Avodah Zarah),以及眾多基督教著作,其中典型代表是特土良(Tertullian)的《論偶像崇拜》(De Idololatria)和狄奧多勒(Theodoret)的《希臘(即異教)苦難的療法》(Remedy of Greek (= pagan) Sufferings)。猶太人和基督教徒一致認為,崇拜偶像的宗教是一種瘋狂,它降臨在異教徒身上,無法控制,並阻礙他們獲得對神的靈性認知。相比之下,埃及的傳說則將搗毀聖像的人描繪成了患有麻瘋病的人。雙方都將對方視為“無神論者”。但是,對於一神論陣營而言,無神論指的是崇拜虛假的神靈,而對於宇宙神論者而言,無神論指的是拒絕崇拜任何神靈本身。在“異教徒”看來,不存在所謂虛假的神靈。所有神靈都有被崇拜的權利,最令人擔憂的並不是崇拜了某個虛假的神靈,而是在供奉中漏掉了某個神——也許是一個未知的神。猶太人被命令清除所有的聖像,以免與他們的神失去聯繫,而“異教徒”必須增加他們的聖像,並將其視為最珍貴的財產加以保護,才能與他們的神靈保持聯繫。
赫爾墨斯(Hermetic)學派的一部論述——《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預見到了基督教的崛起帶來的危機,闡述了偶像崇拜中的利害攸關。該文有幾章專門論述了神像。這些神像可能是人造的工藝品,但它們絕非“死物”,因為人們認為它們具有一種魔力,通過這種魔力,它們能夠與神建立聯繫,並在儀式期間讓神明顯靈。聖像成為一種媒介,通過它,人可以與神靈貼近。它們存在於一個崇拜儀式的上下文中,其目的是在人世間再現神跡,並將神明從天國引至人間。通過這個儀式及其眾多的神像,整個埃及成為了“世界的神殿”,神明在此駐留——前提是,並且只能是,這個無休無止的活動不被終止。然而,文本繼續說道:
終有一天,人們將會發現,埃及人由衷的虔誠和殷勤的崇拜都將是付諸東流;我們對神靈的崇拜都將註定是徒勞無功的。因為神靈將從人間返回到天國;埃及將被遺棄,曾經發源宗教的大地將會荒蕪,神明棄之而去。這片土地和宗教將會被外國人佔據;人們不僅不再侍奉神靈,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將會頒佈所謂的法律,來禁止宗教、虔誠的信仰和對神的崇拜。……埃及啊,埃及,關於妳的宗教,將只剩下一個空洞的故事……只有石頭會述說妳的虔誠。到那一天,人們將厭倦生活,他們將不再認為宇宙(mundus)值得贊嘆和崇拜。因此,宗教,作為所有恩賜中最美好的恩賜——因為沒有什麽,過去未曾有,將來也不會有,能夠被視為更美好的恩賜——將岌岌可危。人們會認為它是一種負擔,並開始厭惡它。他們將不再熱愛我們周圍的這個世界,這個神所創造的無與倫比的作品,這個他所建造的輝煌結構,這個由各種形態的事物匯聚而成的善,這個無私地關懷人類福祉的機器(machina,神的意誌通過它運作),這所有豐富多彩的事物結合在一起——它們能喚起觀者的崇敬、贊美和熱愛。比起光明,人們將更喜歡黑暗,死亡將被認為比生命更有利可圖;沒有人會擡頭仰望天空;虔誠的人會被認為是瘋子,不虔誠的人會被認為是智者。瘋子會被認為是勇敢的,邪惡的人會被認為是善良的……
因此,神靈將離開人類——這是一次痛苦的離別——只有邪惡的天使會留下,他們將混跡於人類中間,並強迫這些可憐的人作奸犯科,包括戰爭、搶劫、欺詐以及一切違背靈魂本性的惡行。那時,大地將不再堅固,海洋將不再承載船只;天空將不再支撐星辰,星辰也將脫離它們的軌道;所有神明的聲音都必將沈默無言;地裏的果實將會腐爛;土壤將變得貧瘠,空氣也會因為在陰郁中停滯太久而變質。世界就會以這樣的方式老去。宗教將不復存在(inreligio);一切都將變得混亂不堪(inordinatio);一切祥和都將消失(inrationabilitas)。
“人們不僅不再侍奉神靈,而且……來禁止宗教、虔誠的信仰和對神的崇拜”——這裏我們看到了奧薩西夫(別名摩西)的第一戒律。 “虔誠的人將被認為是瘋子”——這與《聖經》對偶像崇拜者的諷刺相呼應。然而,根據那些崇拜偶像的人的估計,其後果將是神靈離開人間,被遺棄的土地將變得無法居住。因此,偶像崇拜等同於宇宙崇拜或宇宙神論。聖像和儀式使人間接近於天堂,並將人類世界融入到宇宙秩序中。誰破壞了神像,誰就將切斷天與地、宇宙與社會之間的紐帶,將神靈從世界中趕走,摧毀一切文明秩序。戰爭、盜竊、欺詐和暴力也將隨之而來。
“崇拜偶像”的“異教徒”對一神教徒所懼怕的,恰恰卻也正是後者歸咎於他們的:敗壞道德、煽動暴力、欺詐和通奸。對於一神教徒來說,落入神像的陷阱意味著落入世界的陷阱。當崇拜神像時,異教徒會迷戀於那些被創造出來的、終將消逝的事物。由於被創造物的誘惑所吸引,他們忽視了隱形的創造者,那個遠離塵世、不會藏匿於任何人工制品中的神。這種將造物主與創造物分割開來的想法,等同於顛覆了古代世界所有習以為常的思維和信仰形式,並對它們進行了價值重估。當時的人們卻根本不會將創造物與造物主分開,相反,他們認為創造本身確保了它們之間的聯繫。造物者顯現在他所創造的事物中。在埃及,這種緊密聯繫的概念甚至可以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即:世界是神的身體,神從內部賦予其生命力。這樣的觀點在希臘化時期的宗教融合(Hellenistic syncretism)中被廣泛接受,尤其是在斯多葛學派(Stoic)、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c)和赫爾墨斯學派的宇宙神論中。基督教神學將其妖魔化為偶像崇拜,而這種偶像崇拜(idololatria, avodah zarah)最終只不過是古老的宇宙神論。任何崇拜偶像的人都會破壞與超越世界的神的聯繫,因為他們將虔誠傾註於一個俗世之物上,從而將崇拜付諸於被創造出來並註定會消亡的東西上。他迷失在世俗世界及其價值觀中,受制於享樂主義、叢林法則和“適者生存”等准則。而一神教信徒認為,所有更高級的秩序和規範都源自超越世界的神的啟示。相反,“異教徒”的宇宙神論將排他式一神教妖魔化為無神論,因為這種宗教要求拒絕和迫害所有其他神。宇宙神論並不主張亞威是一個“假”神,不應該被崇拜;相反,它迅速將猶太人的這個神收錄其神聖文本和魔法公式大全中。令它感到震驚的是,猶太人竟然拒絕嚮所有其他神致敬。它擔心這種拒絕將會毀滅世界,神靈是內在世界的力量,驅動著世界,為其帶來生機,一旦偶像破壞者趕走這些神靈,世界將衰敗雕零。對於宇宙神論來說,宇宙是某種規範的原型,這種規範共同奠定了人類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麽在它看來,偶像破壞者的無宇宙觀(acosmism)破壞了社會和諧。而對於一神教來說,維繫人類共存的秩序,並不是來自這個世界,而是在世界之外有一個源頭。一神教認為神像是可憎的,因為它們阻礙了通往這個源頭的途徑,並使人陷入世俗的凡界。
在《埃及人摩西》一書中,我主要想證明一神教從未完全成功地壓制宇宙神論。在西方宗教和思想史中,宇宙神論這個選項一再找到願意接受的聽眾。古埃及在其中扮演了一個特別重要的角色——這足以讓一位埃及學家對重見天日的古埃及文本產生濃厚興趣,縱然它們早已不再為人所知。“埃及”這個名字主要在希臘和拉丁文獻中得以保留,尤其是《赫爾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和赫拉波羅(Horapollo)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在 17 和 18 世紀,一種觀念逐漸流行起來,即摩西並非通過神的啟示接受了一神教思想,而是從他身為埃及王子所接受的埃及密契主義中獲悉的。這樣一來,一神教和宇宙神論似乎得到了調和。古埃及的宇宙神論被視為一種自然宗教,其中孕育並保存了神性合一——伊西斯(Isis)作為自然之母——的觀念。摩西將這一奧秘泄露給了希伯來人,進而泄露給了全人類。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宇宙神論”的概念被提出,它既指古代的異教宗教,也指斯賓諾莎的當代哲學。
18 世紀末期,人們意識到印度是一個充滿靈性追求的國度。語言學家認識到梵語、希臘語、拉丁語等語言之間的親緣關繫,並基於這種親緣關繫,將印度視為“印歐語繫”民族的發源地。埃及的宇宙神論,曾經作為一神教的替代選擇而被歴史棄絕,但是,由於這個發現,印度繼承了埃及的這一遺產。直到這個時候,閃米特語和印歐語世界才開始相互對立,形成了兩個在語言、種族和精神信仰方面相互對立的陣營。直到與印度有關的時候,宇宙神論或反一神教才具有反猶太教的特徵。也只有在這個時候,與印度建立了聯繫,宇宙神論或反一神論才開始具有反閃族主義的特徵。現在看來,排他性的一神教,以其拒絕偶像崇拜為標誌,是一種典型的閃族宗教,一種沙漠遊牧民的宗教。古埃及人意識最深處的恐懼症也被再次喚醒。許多反閃族主義的元素並非源自基督教,而是源自異教或新異教,這也是弗洛伊德將反閃族主義者診斷為“受洗不徹底”[2]的原因。
在我看來,弗洛伊德的這句評論切中要害。宇宙神論思潮從未被徹底徵服和根除,而是以各種變形和偽裝不斷出現,如赫爾墨斯主義、帕拉塞爾蘇斯主義(Paracelsianism)、煉金術、斯賓諾莎主義、共濟會(freemasonry)、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ism)、神秘學(theosophy)等等。二十世紀,人智學(anthroposophy)、海克爾(Haeckel)的“一元主義聯盟”(Monist League)、慕尼黑宇宙主義者(Munich cosmicists)、納粹主義新異教(National Socialist neo-paganism)以及眾多新世紀(New Age)宗教運動都表現出明顯的宇宙神論傾嚮。當然,這些宗教運動彼此相去甚遠,甚至針鋒相,絕不應該簡單地混為一談。然而,它們確實都共有一種反一神教的元素。研究古埃及和希臘化時期的文獻,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場沖突的根源,並通過歴史分析的方法化解某些反猶偏執和恐懼。
上古神學與摩西區隔的廢除
在近代早期,一場記憶的沖突再次爆發了,但這次並非發生在一神教信徒和“異教徒”之間,而是發生在一神教信仰內部。爭議的核心在於一神教信仰與其自身過去的關聯。是否應該將摩西律法出現之前的這段歴史(ante legem)視為異教而果斷拋棄,並將西奈山上的一神教的信仰宣言單純視為一次信仰突變?還是應該將這段過去也納入到一神教的真理史中,然後僅將摩西視為古代世界眾多真理載體和啟示媒介中的一位?其余的包括索羅亞斯德(Zoroaster,其波斯文原名被譯為“查拉圖斯特拉”),和赫爾墨斯·特裏斯墨吉斯特斯(Hermes Trismegistus),他們在年代上甚至遠早於摩西。後一種選擇意味著廢除摩西的區隔。在《埃及人摩西》一書中,我將廢除摩西區隔的學術活動與 18 世紀的自然神論聯繫在一起。對此,有人可能會反駁說,15 世紀和 16 世紀的佛羅倫薩新柏拉圖主義,其中的上古神學(prisca theologia)或長青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的理念已經包含了這種廢除。從很多方面來看,18 世紀回歸到了 15 世紀和 16 世紀,所以我們不僅可以從 18 世紀的角度將中間的 17 世紀視為摩西區隔最終被廢除前的序曲,同樣也可以從 16 世紀的角度將其看作重新強化這種區隔的時期。我在閱讀邁克爾·施特勞斯伯格(Michael Stausberg)的《魅力非凡的查拉圖斯特拉》(Faszination Zarathushtra)一書時,心中湧現了這些反駁觀點,這本著作在某種程度上平行於我在《埃及人摩西》中所作的研究。在這本書中,施陶斯伯格運用記憶歴史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從 15 世紀到 18 世紀的歐洲宗教史中對查拉圖斯特拉(即索羅亞斯德)的接受情況,發現了一條“記憶痕跡”,它非常近似於我從埃赫那頓開始,經希臘文獻一直延伸到 18 世紀的記憶痕跡。在這裏,新柏拉圖主義的文本也發揮著關鍵作用。《迦爾德的神諭》(Chaldaean Oracles)之於索羅亞斯德就相當於《赫爾墨斯文集》之於赫爾墨斯·特裏斯墨吉斯特斯一樣重要。
西方對索羅亞斯德的記憶歴史始於格彌斯托士·蔔列東(Gemistos Plethon,1355/60–1454),他在 15 世紀從拜佔庭逃到佛羅倫薩,以躲避不斷逼近的土耳其人。他可以被視為“上古神學”或“長青哲學”的最早代表。蔔列東通過將新柏拉圖主義文本(如《迦爾德神諭》)追溯到索羅亞斯德,並根據古代文獻(尤其是普魯塔克,Plutarch)將索羅亞斯德的年代定在特洛伊戰爭前 5000 年,通過這樣做,他將自己版本的柏拉圖主義提升到原始哲學的高度。他幾乎將自己視為新宗教的開創者,這個宗教將通過恢復所有人共同擁有的原始真理來消除異教徒和基督徒之間的差異。據我所知,蔔列東的嘗試是有史以來最激進的廢除摩西關於真理宗教和謬誤宗教之間區隔的嘗試。因此,他的對手指責他是一個新異教徒,是多神論者(polytheos)。在他的思辨膽識中,蔔列東註定會成為一個孤立的案例。盡管後來所有的觀點都間接地建立在他的基礎之上,但它們從未冒險超越基督教的界限,無論這些界限的定義有多麽寬泛。然而,值得註意的是,近代早期對摩西區隔的批判始於一個激進的破裂,並且這種與《聖經》傳統的破裂通過訴諸一個據稱更古老、更原始的傳統來為自己的立場尋找依據。蔔列東所倡導的新宗教標榜自己是對最古早的復興。在後來的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時期,這一激進的出發點被很大程度上淡化。因此,這裏的發展路線從激進的異端走嚮正統,這與 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情況截然相反,在當時,有一位英國神學家和希伯來學者約翰·斯賓塞(John Spencer,1630-1693),盡管他自己始終認為其最初立場是基本正統的,後來卻被自然神論者和共濟會(Masonic)圈子中產生的愈發激進的異端立場所取代。
馬爾西利奧·費奇諾(Marsilio Ficino,1433-1499)的“上古神學”的概念不再被視為超越基督教的新宗教,而是被視為一種原始宗教和原始哲學,它將柏拉圖主義——可以追溯至索羅亞斯德和赫爾墨斯·特裏斯墨吉斯特斯——整合到基督教中。與蔔列東一樣,費奇諾同樣關心廢除摩西區隔,但他試圖以一種更廣義的基督教視角來做到這一點,將基督教理解為由所有古代宗教奠基和背書的原始宗教,而不是以一種後基督教時期新異教的視角。這一概念背後是基於《聖經》譜繫的真理傳播理論,根據該理論,宗教習俗源於挪亞,然後由挪亞的子女和孫輩傳播到世界各地。赫爾墨斯·特裏斯墨吉斯特斯和後來的索羅亞斯德被視為一繫列智者和神學家中的最初兩位,這些智者保存並發展了亞當或挪亞的原始知識,同時又遊離於《聖經》的傳統之外。所有宗教、規範和文化傳統(sapientia,智慧)都有一個共同的起源,那就是神,並且在原始時期由智者們編纂成典。
費奇諾將上古神學的模型與他的一項計劃聯繫起來,在這個計劃中,他打算將哲學改造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以醫學美術、人文關懷和文獻學等方式統攝了智慧、虔誠和實踐活動的集合體。以最高祭司赫爾墨斯·特裏斯墨吉斯特斯和索羅亞斯德為原型,文藝復興時期發展出關於“賢者”(magus)的理想,“賢者”集所有這些角色和技能於一身。這種將神學家和醫生、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合二為一的理想,也意味著一種對摩西區隔的否定,這種區隔的特點恰恰是將精神事務排除在世俗職業和能力範圍之外。 在這個背景下,喬凡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伯爵(Count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的案例尤其值得關註,因為這位作者在他短暫的生命即將結束時做了一個 180 度的轉變。起初,他極富熱情地接受了“上古神學”的模式,隨後卻在《駁斥佔星術》(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 divinatricem)中疏遠了它,將其斥責為“古代迷信”(prisca superstitio)。他因此預見了一些導致在 18 世紀摩西區隔被增強的論點。由此,皮科不僅與他自己之前的立場背道而馳,也以同等程度超前於他自己所屬的時代。
奧古斯蒂諾·斯特歐科 (Agostino Steuco,1497/98–1548) 在其“長青哲學”概念中鞏固了費奇諾的上古神學模型。他也希望廢除真理宗教與謬誤宗教之間的區隔,代之以“所有民族智慧相互一致,以及這種智慧與基督教教義一致”。斯特歐科同樣假設存在一個由偉大智者們傳承下來的“完美的原始神聖啟示”,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被保存並傳播給各民族。然而,盡管費奇諾從演化的角度解釋了原始宗教從共同起源分支散葉的擴散過程,但對於斯特歐科而言,這個過程是退化的標誌。傳統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衰落,基督教,曾經是無可爭議的世界宗教,如今環顧四周,皆是各種墮落的變種在蓬勃發展,只有通過回歸共同真理才能撥亂反正。關於傳播理論的這種“退化”觀念將在 17 世紀成為主導文化範式。正如蔔列東在東西方教會沖突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沖突的直接影響下勾勒出他的統一願景一樣,斯特歐科也是在天主教和誓反教之間無法挽回的分裂的背景下發展出了自己的願景。在這兩種情況下,以及在費奇諾、皮科、羅伊希林(Reuchlin)和其他人身上,對索羅亞斯德和赫爾墨斯、柏拉圖主義和卡巴拉主義(Kabbala)的回歸——這些據稱是古老的真理源泉——都是為了創建一個和融主義式(Irenicism)的寬容模式。他們試圖在起源的統一性中尋找解決當代宗教紛爭的方案,通過廢除摩西的區隔並回歸到摩西之前的歴史和傳統來緩和教派沖突。
弗朗切斯科·帕特裏齊(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 的新宇宙哲學(Nova de universis philosophia)計劃受到類似的統一願景的啟發。他也設想超越摩西區隔,但這一次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即真理融合理論(convergence theory of truth),一方面,該理論認為,五種不同的哲學流派(包括四種“古代”哲學和帕特裏齊自己的哲學)之間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又稱它們與天主教教義也完全一致。對於帕特裏齊而言,退化理論描述的其實是原始語言的衰落和消亡的歴史。這種原始語言——即巴別塔建造後失落的語言——遵循 “直接意指”(immediate signification) 的原則(借用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3])的概念),即其符號直接且自然地參與所指的本質,而現代語言則遵循 “間接意指” (mediate signification)的原則運作,即它們通過一套約定俗成的編碼來制定符號和所指之間的關繫。直接意指的原則在異域語言的魔法咒語——“野蠻名稱”(onomata barbara)——中才能得以保存,只有這些咒語仍保留著召喚所指並使其現身的力量。在這種“尋找完美語言”的背景下,埃及由於將象形文字視為“自然符號”而扮演了核心角色。由於亞裏士多德被認為支持基於間接意指的符號學和語言學理論,而帕特裏齊等人的柏拉圖式符號學理論則以直接意指為基礎,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麽他們在其作品中攻擊亞裏士多德。
摩西區隔的反撲與異教研究的興起
帕特裏齊的作品標誌著文藝復興時期寬容的知識分子氛圍的結束:1592 年,它被列入禁書目錄。反宗教改革的環境變得更加嚴酷,上古神學和廢除摩西區隔的烏托邦理想再也無立足之地。關於赫爾墨斯·特裏斯墨吉斯特斯和索羅亞斯德的著述從意大利遷移到政策更寬鬆的北方地區,從天主教環境轉嚮到以誓反教為主的環境,並從哲學(或將神學、哲學和醫學融為一體的烏托邦)轉嚮歴史研究,確切地說是“古代文獻”研究。這個階段一方面,以文獻學-歴史批判為標誌,另一方面幾乎是對偶像崇拜的近乎恐懼的拒絕。經過仔細的批判性審查,《迦勒底神諭》被揭露為與《赫爾墨斯文集》(Corpus Hermeticum)一樣,不過是晚期古典時期的作品。其他來源就相應地變得更為重要起來:銘文、古代歴史學家和教父的記述、遊記等等。與索羅亞斯德相關的傳統首次以其異己性見稱,並不再被視為西方傳統的原始或胚胎形式。人們付諸更多的努力來劃定出一條界限,為了將所有的外來事物都拒之門外,但矛盾的是,與此同時,卻意外地出現了新興的、更加深入和繫統化的對經外世界的興趣。盡管在 17 世紀,“異教徒”再次被疏遠和排斥,但對他們的研究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種新興的“異教學”經常用於揭示異教文本和儀式的非原創性和衍生性,例如艾薩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確定了《赫爾墨斯文集》相對較近期的起源;但它也代表了對摩西區隔的更為嚴格的重新應用和由此帶來的宗教不容忍的再次爆發的反應。
然而,第二個焦點——即新的敵人“拜星教”(Zabiism 或 Sabianism)——使我們無法在現代意義上討論宗教史學。特別是索羅亞斯德,他成為了這個異教的代表人物,因此遭到最嚴厲的詛咒。拜星教是偶像崇拜的同義詞。“拜星教徒”(Sabians)的概念,是偉大的猶太哲學家摩西·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的一種發明,常被與薩拜人(Sabaeans,居住在薩巴王國的人)相混淆。猶太教的儀式律法不能夠僅靠理性來尋找依據,因此邁蒙尼德曾嘗試為其尋找歴史性的合理化依據,他認為猶太教的儀式律法源自對異教儀式的“規範顛倒”(normative inversion)——即,在異教被嚴格禁止的,猶太律法規定其為必須要履行的義務;反之,在異教被看作是神聖義務的,猶太律法則明令禁止。在尋找這樣的儀式時,邁蒙尼德在十世紀作家伊本·瓦希什亞(Ibn Wahshiyya)的著作《納巴泰農農業》(Nabataean Agriculture)中偶然發現了拜星教。拜星教在偶像崇拜方面的首要特徵是崇拜天體和佔星術。對於邁蒙尼德來說,“異教”不僅僅是所有因其謬誤而被拒絕的宗教的總稱,而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宗教,對他來說,它與某個社群、民族或國家的民族身份認同息息相關:拜星教,拜星社群(‘ummat Sabi’a)。抹除記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反記憶覆蓋它。因此,作為一種反宗教,一神教只能通過在拜星教不計其數的儀式上疊加新的儀式來建立自身,並根據顛倒規範的原則將這些儀式顛倒過來。1625 年,斯蒂芬·內茨(Stephen Nettles)總結了邁蒙尼德的顛倒規範原則如下:
在《迷津指要》中,摩西·本·邁蒙(Moses ben Maimon[4])寫到,設立祭祀的主要目的是根除偶像崇拜。因為外邦人崇拜動物,例如迦勒底人和埃及人崇拜公牛和綿羊,並將它們與白羊座和金牛座等天象聯繫起來,因此,(他說)上帝命令將這些動物宰殺作成祭品。
邁蒙尼德認為猶太教的儀式律法沒有理性依據,需要以歴史的方式加以解釋。他認為,儀式律法的歴史解釋在於其功能,即讓猶太人遠離他們已經完全習慣了的拜星教偶像崇拜式的祭祀行為。隨著被新的法規文本層覆蓋,這些異教儀式逐漸被廢棄。邁蒙尼德的“拜星主義”概念,曾經是一個世界性宗教,如今卻已被遺忘,它與“上古神學”的概念形成了鮮明的反照。上古神學強調結合異教的智慧,試圖在共同真理的光輝下消除摩西區隔;而拜星教的概念則強調對異教習俗的堅決否定,試圖在排他性真理的光輝下強化摩西區隔,這種真理只能通過巧妙地適應歴史環境而逐漸被接受。
雖然“拜星主義”的概念毫無疑問地帶有負面含義,但它同時(甚至對邁蒙尼德來說)也成為一種難以抗拒的魅力的來源。新的異教學就是在這種魅力的驅使下發展起來的:異教被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而不是被當作基督教的先驅而研究。17 世紀是異教學的黃金時代,也是宗教學術研究的搖籃。現代讀者必須忽略對偶像崇拜的嚴厲指責和反復表達的憎惡態度,盡管這些言論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從根本上損害了這些研究的科學性,但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一種必要的偽裝,即便在誓反教環境中也是如此,相反,讀者應該欣賞研究者們對“異域”所表現出的明顯好奇心,在最初的接受階段,這個術語的含義被限制在上古神學的框架內,而如今,對它的理解遠比當初更加全面,也更具有歴史批判性。
現在,對異教的關註轉嚮了其起源、發展和結構形成。與 15 世紀和 16 世紀不同,摩西區隔——真假宗教、基督教和異教、一神教和多神教(或偶像崇拜)之間的界限——被堅定地守護著,但這樣做只是為了能夠以淵博的學識和敏銳的批判來研究被排斥的“異己”。這就是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敘利亞的神祇》, De diis syris,1610)、赫爾哈德·約翰內斯·弗斯(Gerhard Johannes Voss,《論異教神學》, De theologia gentili,1641)、塞繆爾·博查特(Samuel Bochart,《聖地地理學》,Geographica sacra,1646)、西奧菲勒·蓋爾(Theophile Gale,《外幫人的宮院》, The Court of the Gentiles,1669–1671)等人的著作對科學史的意義所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傳播理論將所有知識都追溯到一個共同的起源,並且,同時也在這個起源中發現了回歸到曾經的統一狀態的希望,但隨著摩西區隔的收緊,這個看法被徹底改變了。現在,“轉移”(translatio,mutatio,imitatio)的概念取代了“傳統”的概念,並且這種轉移是雙嚮的,要麽說是異教徒借用了《聖經》的知識,要麽說是《聖經》借用了異教的知識。轉移的概念意味著邊界的觀念,因此也隱含了跨越邊界進行比較的可能性。在這方面,皮埃爾·丹尼爾·惠特(Pierre Daniel Huet,1679 年,《福音證成錄》,Demonstratio evangelica)是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他以火藥味十足的語調劃清了真理宗教和謬誤宗教之間的界限。惠特強調了《摩西五經》的真實性和悠久歴史,(想必是為了反駁斯賓諾莎),他將這五本書看作是神聖真理的原始編纂,而將異教視為他們的邪惡拷貝。盡管這部作品在當時既有很高的學術性又聲名卓著,但由於它帶有很強的片面、盲目偏袒和護教性的意圖,顯然科學的歴史法將其作為宗教史發展道路上的裏程碑而接納。然而,約翰·斯賓塞(John spencer)在他的《論希伯來人的儀式律法及其原因》(De legibus Hebraeorum ritualibus et earum rationibus,1685 年)一書中駁斥了惠特的論點,從而顛覆了他的理論,並展示了 17 世紀可能存在的其他選項。惠特將異教的文化制度描繪成《摩西五經》的剽竊版本,而斯賓塞則試圖證明摩西律法來源於(埃及的)異教傳來顛覆這一說法。盡管,以我們今天對埃及和《聖經·舊約》的了解來看,斯賓塞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是錯的,但在一個問題上他當然是正確的,那就是埃及宗教比《聖經》宗教年代更久遠。然而,更為關鍵的是,斯賓塞將“轉移”(translatio,mutatio)的概念從任何抄襲或(拙劣)模仿的嫌疑中解放了出來。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在他的《波斯古史》(Historia veterum persarum ,1700 年)中也以這種價值中立的方式使用了這一概念。在這裏,《聖經》再次是給予者,異教則是接收方。但是,在海德看來,索羅亞斯德是先知耶利米亞(Jeremiah)的弟子,從他的講話中學到了很多,這反而有利於耶利米亞的教導。
隨著“轉移”或“轉譯”的概念出現,摩西區隔至少被相對化了。邊界仍然存在,但它現在足夠鬆散,可以允許物品的交換,無論這些物品是違禁品還是獲得批准的。在反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以正統之名而對摩西區隔的收緊政策被謹慎地、但持續而有效地放緩。人們不再使用具有鮮明的批判色彩的“偶像崇拜”概念,代之以更為中立、或至少批判口吻更微弱和更具描述性的“多神論”概念。 17 世紀和 18 世紀異教學的關鍵概念是“神秘”。異教宗教被解釋為神秘宗教,它們早已知曉真理,但被要求將其隱藏在神秘的面紗之下,只有少數被點化的才能接觸到。然後,摩西將其揭示給他的族人,並將入門者和俗人之間的區隔轉化為猶太人和異教徒之間的區隔。
第四章: 弗洛伊德與智性的進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他的作品《摩西和一神教》時,精神分析學家、歴史學家和神學家幾乎沒有給予關註,但在過去十多年裏,也就是該書問世半個多世紀之後,它經歴了某種程度的復興。毫無疑問,這種復興與近年來人們對摩西和一神教起源問題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興趣密切相關,這種興趣已經超越神學領域,滲透到歴史、哲學、文學和廣泛的知識分子圈,甚至滲透到埃及學這個孤立的領域,大約在十到十二年前,這個話題也開始吸引了我。經過半個世紀的蟄伏,弗洛伊德挑釁性的論點終於開始在受過教育的公眾中產生影響。幾乎可以說,這本書的主題已經成為它自身的命運:壓抑、潛伏和被壓抑者的回歸。
這本極具挑釁性和爭議性的著作的主要貢獻在於,它將一神教作為一個心理歴史問題提了出來。弗洛伊德認為,隨著這種宗教的興起,也出現了一種全新的靈性、一種根本上全新的靈魂趨嚮。他將一神教描述為——或者應該說,剖析成——一種父權宗教,因此帶有與父親的關繫(在俄狄浦斯情結的意義上)通常會導致的所有心理歴史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對父權意誌的挑戰和順從、被選中的欣快感、愧疚感、以及自卑的幻想和無所不能的幻想。如果說——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俄狄浦斯情結已經代表了人類靈魂的普遍稟性,那麽一神教這種父權宗教則標誌著俄狄浦斯傾嚮的決定性的強化,並且這種強化是特別以猶太人的方式發生的。在一神教中,原始部落那個被壓抑的祖先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回歸,成為一位強加規則的“超級父親”,他要求他的子女對他表現出無條件的愛、忠誠和服從。真正引發人們思考的,並不是這個命題本身,而是弗洛伊德賦予一神教問題的那種心理歴史的曲摺性,這一挑釁直到最近幾年才引起應有的關註。
弗洛伊德本人用一個簡潔的短語總結了一神教的心理歴史後果——“智性的進步”。他指的是一神教的(即猶太人的)父權宗教——以及這一概念所涉及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所有含義——要求其兒子們(在較小程度上也要求其女兒們)在道德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和升華的豐功偉績。在拙著《埃及人摩西》裏關於弗洛伊德的章節中,我誤解了摩西區隔與弗洛伊德的“智性進步”概念之間的關繫。我當時提出了一個我現在不再認為站得住腳的觀點,特別是在閱讀了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弗洛伊德和摩西的遺產》(Freud and the Legacy of Moses)之後。我的這個觀點是,弗洛伊德將摩西描繪成一個埃及人的時候,他是要試圖廢除摩西關於真理宗教和謬誤宗教的區隔。我之所以會有這種印象,是因為我是在讀了斯賓塞、萊因霍爾德和席勒的作品之後便立即閱讀了弗洛伊德的《摩西》一書,當時還處於他們的影響之中。當時,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像是延續了啟蒙時代的一種特殊話語。然而,當我最近重新閱讀它的時候——可能是第三或第四遍——這本書給我的印象卻截然不同。我現在反倒認為,弗洛伊德試圖將摩西區隔(以禁止偶像崇拜的形式)呈現為一種具有開創性、極其寶貴和深刻的猶太人的成就,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放棄,而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學恰恰可以因為進一步推進了這種特定類型的猶太式進步而自豪。
猶太選項與希臘選項
法國哲學家雅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這位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反思的人,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希臘人嗎?我們是猶太人嗎?但誰,我們[1]?”海因裏希·海涅(Heinrich Heine)則以另一種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所有人,要麽是猶太人,要麽是希臘人,要麽是帶有禁欲和毀像的本能,沈迷於知識分子化的民族,要麽是熱愛陽光和務實,為自身順其自然的成長而感到驕傲的民族。”這表明,這個問題並不新鮮。自從 19 世紀歐洲人意識到他們具有相互矛盾的雙重起源,並將其轉換成“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Hellenism and Hebraism”)的非寫實性的誇張對立以來,它就一直睏擾著歐洲人的心靈。
這個問題最初起源於語言學領域,梵語和印歐語繫的發現導致人們構建了歐洲文化的“雅利安”(Aryan)起源。這種“雅利安”和“閃族”(Semitic)之間的對比,最初僅存在於語言學層面,但快就成為種族心理學和文化類型學的老生常談,催生了一繫列無休止的傳統二元對立和文化陳詞濫調,這些觀念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的思維。結果,歐洲人變得越來越難以理解“猶太性”和“希臘性”之間是一種富有成效的合作關繫,而不是勢不兩立的敵對關繫。對歐洲起源的這個問題,海涅的回答的獨到之處在於其中對非此即彼的普遍化。它不再僅僅是雅利安人與閃族人之間的對立,而是涉及“所有人”的更為廣泛的對立。我們每個人都發現自身處於兩種傾嚮的相互撕扯之中:其中一種是對靈性與智性化的追求,它使我們遠離世界;另一種是感性,它令我們奔嚮世界。前者傳承自猶太人,後者則是希臘人賦予我們的。因此,我們的軀體裏住著兩個靈魂,一個是猶太人的,一個是希臘人的,它們相互爭奪主導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海涅將(猶太人的)靈性與“本能”和“沈迷”的概念聯繫在一起,將更具褒義的“氣質”概念保留給了其對立面——即(希臘人的)“安於世間”的特質。
弗洛伊德對這此持有類似的觀點。他也認為猶太人對人類歴史的獨特貢獻在於追求他所說的“智性進步”。這種在人類心理歴史層面的進步對應於他在個體心靈生活層面所說的“升華”,對他而言,這代表了心靈發展和成熟的最高成就。與海涅一樣,弗洛伊德在此語境下也提到了“本能”,盡管他隨後便指出這個概念並不適用。他說:“多數人無法放棄這樣一個信念,即人類存在一種追求完美的本能,是這種本能把他們引領到了目前高度的智力成就和道德升華,”他接著說:“然而,我不相信有這樣的本能存在。”我們最出眾的文化成就遠非源於本能,而是要歸功於對本能的壓抑。弗洛伊德寫道:“在我看來,對人類目前的發展,並不需要與動物的發展不同的解釋。在我看來,少數人類個體表現出的那種對進一步完善的不懈追求,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釋為本能壓抑導致的結果,而這種壓抑正是人類文明中一切最寶貴的東西的基礎。”猶太教是文明進步的引擎,這種進步遠非植根於人類的本能屬性,反而與之深深敵對。猶太人在這裏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他們——此處弗洛伊德贊同海涅的觀點——通過拒絕偶像崇拜做到了這一點。在整個人類進步的故事中,第二戒命標誌著一個劃時代的門檻。
對於第二戒命的這種觀點也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康德認為禁止造像是崇高的典範(所有“升華過程”所趨嚮的目標):“也許在猶太律法書中,沒有比這條戒命更崇高的段落了:‘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麽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單只這一條誡命就可以解釋猶太人在其文明時期——當他們將自己與其他民族進行比較時——對其宗教的熱情,這與伊斯蘭教所激發的自豪感如出一轍。”弗洛伊德對“智性的進步”的評論就像是對這句話的延伸評論。像康德一樣,弗洛伊德也在探究兩個現象的終極源頭,一個是宗教對猶太人施加的強制性力量——即康德所說的“熱情”,另一個是他們作為上帝選民所感到的自豪。在弗洛伊德看來,一神教宗教的特徵在於“它拒絕魔法和神秘主義,激發智性的進步,並鼓勵升華”。在一神教之下,“人們因擁有真理而陶醉,因知曉被神選中而不勝自喜,看重智性,強調道德。”
在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摩西和一神教》中,弗洛伊德用八個章節總結其研究結果,他用“智性的進步”來作為其中第三章節的標題。他不僅將這一章節單獨發表成了一篇文章,還批准了他的女兒安娜在 1938 年巴黎舉行的國際精神分析大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Congress)上宣讀它。可見他對此文的重視程度。他認為這是他對猶太教的忠誠宣言,是他作為文化哲學家的遺產,以及他的《摩西》一書的精髓。因此,可以用以下陳述來概括弗洛伊德對猶太教和猶太人對人類歴史貢獻的理解:如果“智性的進步”是人類必然的命運,那麽猶太人在這一方面就是引路人。
一神教的創傷:分析闡釋學與記憶歴史
弗洛伊德選擇作為出發點的問題涉及到猶太教的起源。他想知道“猶太人是如何成為他們現在的樣子,以及為什麽他們招致了這種持久的仇恨。”我之前提到的“俄狄浦斯情結強化”只適用於猶太教,正如弗洛伊德在談到一神教宗教時,考慮的是猶太教而不是基督教。對於智性的進步來說,猶太父權宗教中父權-俄狄浦斯情結的強化是心理層面的先決條件。
關於“猶太人是如何成為現在的樣子”這個問題,弗洛伊德的解釋簡直令人訝異。他聲稱,“猶太人”是由一個叫“摩西的人”獨自一人創造的。這個人以兩種方式創造了猶太民族。一個是解放他們,為他們立法,並賦予他們宗教教義,他將原本是一盤散沙的奴隸塑造成了一個民族,即一個具有政治組織的社群。但他還以第二個更深層次的方式創造了猶太民族,那就是塑造他們的靈魂。正是這個更具決定性的創造首次使猶太人成為“他們現在的模樣”,但摩西本人生前並未看到,而是在他死後實現的。這是一個跨越數仟年的種族心理遺傳過程,屬於秘密歴史的範疇。官方記憶的年表、《聖經》文本和其他歴史文獻對此一無所知。只有精神分析的“考古”工具才能深入到集體精神生活的地下領域,揭示一個不僅從意識記憶中消失,而且——根據所有精神分析理論規則——必定被壓抑為深刻創傷性經歴的起源。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沒有任何其他理論能夠解釋這樣一種動力,通過它一個觀念竟然能夠如此徹底地俘獲整個民族的靈魂,並讓其“沈迷其中”: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每一個從遺忘中回歸的部分都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力量,對大眾施加著無比強大的影響,它宣告一種無法抗拒的真理,任何邏輯上的反對意見在它面前都顯得無力:一種類似“因其荒謬,故而信之”(credo quia absurdum)的信念。這種顯著的特徵只能用精神病患者的妄想模式來理解。我們早已了解到,在妄想觀念中隱藏著部分被遺忘的真相,當它回歸時,不可避免地會被扭曲和誤解,並且與妄想相伴隨的強迫性信念源於這一真相的核心,然後蔓延到掩蓋它的幻覺上。我們也必須承認,宗教教條中存在著類似於這種可以稱為歴史性真理的成分,雖然它們無疑帶有精神病症狀的特徵,但作為群體現象,它們卻擺脫了孤立的境地。”
對於弗洛伊德而言,宗教傳統編織了一層由“幻覺”、“歪曲和誤解”構成的面紗,而他的准考古學式的心理分析方法則將其揭開,露出隱藏其下的歴史真相核心。弗洛伊德確信他揭示了這個起源而非重建它,就像十九世紀的考古學家重新發現了法老埃赫那頓(他對其評價很高),或者在弗洛伊德自己的時代,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發現圖坦卡蒙法老一樣。
弗洛伊德最具代表性的拓撲隱喻之一便是“深度”。這與他的心靈拓撲學密切相關,他將心靈劃分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個層次。本我潛藏於潛意識的深處,它超出了意識的範圍,只能通過痕跡和症狀顯露出來。精神分析便是探索這些深度的藝術。弗洛伊德喜歡將自己的工作比作考古學,他對古董的個人收藏也佐證了他對考古學的濃厚興趣。早在 1896 年關於歇斯底裏症的研究中,他就已經開始詳細闡述這種方法論上的類比:
想象一下,一位探險家來到一個鮮為人知的地區,一片廣闊的廢墟引起了他的興趣,那裏有殘垣斷壁、斷裂的柱子和字跡模糊的銘文石碑。他可以只滿足於觀察暴露在外的東西,嚮居住在附近的——或許是半野蠻的——居民詢問有關這些考古遺跡的歴史和意義的傳統說法,並記錄他們的講述,然後繼續旅程。但他也可以採取不同的行動。他可能帶了鋤頭、鐵鍬和鏟子,並讓當地居民使用這些工具。他可以與他們一起清理廢墟,清除垃圾,從可見的遺骸開始,發掘掩埋的寶藏。如果他的工作取得成功,這些發現將不言自明:破敗的墻壁是宮殿或寶庫的城墻的一部分;柱子的碎片可以還原成一座寺廟;那些數量眾多的銘文,幸運的話可能是雙語的,揭示了一種字母表和一種語言,一旦它們被破解和翻譯出來後,就會提供關於遙遠過去的事件的意想不到的信息,那些紀念碑正是為了紀念這些過去而建造的。Saxa loquuntur! (石頭在說話!)
Saxa loquuntur,石頭在說話;但對於深入探究的考古學家來說,石頭的講述與半野蠻土著口口相傳的故事,或僅靠表面發現所能揭示的內容截然不同。從地下挖掘出的真相與暴露在視野中的信息或表象之間存在著本質差異。弗洛伊德式闡釋學原則正是源於這種差異。這是一種懷疑的闡釋學(瑞考爾,Ricoeur),它只會從表面明示的信息中看到被扭曲和誤傳的被掩埋的真相的痕跡。弗洛伊德正是以這種方式解讀《聖經》文本的。他聲稱,透過這些文本,他瞥見了歴史的輪廓,這段歴史曾在受其影響的人們的靈魂中引起了巨大的動蕩,並使他們成為今天的模樣。
記憶歴史方法則朝著相反的方嚮發展。它探究的是象徵性的真相而非歴史真相。它並不會在(通過符號)揭示出某個被埋藏、遺忘或壓抑的真相後便拋棄符號,而是深入探究符號本身想要表達的內容。與其追問事情“究竟如何發生”,它更關心“為何會被如此記憶,以及如何被記憶”。
弗洛伊德將一神教視為一種“父權制宗教”——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父神論”——他的分析建立在兩個無法被任何意識記憶(因此也無法通過文化傳播)直接觸及的基礎之上,只能通過精神分析闡釋學的“考古挖掘”才能重見天日。第一個基礎是一種心理歴史的“建構”,即他在《圖騰與禁忌》(1912 年)中已經詳細闡述的原始部落的神話。第二個基礎來自一項宏大的歴史重建,弗洛伊德以近乎法醫般的細致進行這項工作,最終提出了兩個令人震驚的大膽主張:摩西並非希伯來人,而是埃及人;而且他並沒有像《聖經》所記載的那樣在摩押去世,而是被自己的人民殺害。這兩個基礎都是站不住腳的。弗洛伊德自己在書中和私人信件中都抱怨說,他豎起一座巨人的雕像,可是他的腳卻是用泥土搭建的。但是,這個巨人——他對一神論父權宗教及其心理歴史學後果的分析——始終都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挑戰。
弗洛伊德關於摩西是埃及人並且被猶太人謀殺的論斷與《聖經》的記載直接矛盾。因此,它們構成了歴史真相和象徵真相之間、以及歴史上的摩西和符號化的摩西之間的截然相反的對立。考慮到關於歴史上的摩西沒有一絲證據留傳下來,這一點顯得更為自相矛盾。除了《聖經》中的摩西之外,我們僅有一些歴史可靠性更加可疑的希臘化和猶太傳說,而這些傳說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幾乎沒有提及。他構建的矛盾並不是來自《聖經》和《聖經》之外的文獻的矛盾,而是來自《聖經》本身的矛盾。《聖經》中的摩西擁有兩面性,如同經過重寫的羊皮紙卷,或者是一幅精心修飾過的肖像畫。在弗洛伊德看來,《聖經》文本竭力掩蓋摩西的埃及血統和被謀殺這兩個基本事實,但還是留下蛛絲馬跡,暴露了其隱藏的真相。其中一個線索是摩西的名字,它顯然源自埃及語,而《聖經》文本試圖用一個非常老套的希伯來語詞源解釋。另一個線索是他嬰兒時期的傳說,這個傳說顛倒了熟為人知的“英雄誕生”(奧托·蘭克,Otto Rank) 的神話模式,以至於讓人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其實是在“猶太化”一個埃及人。第三個線索是摩西的“口拙”,這表明他無法流利地說希伯來語,必須依靠亞倫(Aaron)的翻譯才能與猶太人交流。《聖經》中也存在一些指嚮摩西可能被謀殺的線索。弗洛伊德認為,頻繁對摩西進行的致命暴行和公然的死亡威脅都是這樣的線索,此外還有先知們慘遭毒手的命運的主題,尤其是在《何西阿書》中。歌德和弗洛伊德引用的舊約學者恩斯特·塞林(Ernst Sellin)都從這段經文中推斷出摩西一定被謀殺了。例如,《出埃及記》第 17 章第 4 節中寫道:“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嚮這百姓怎樣行呢?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而在《民數記》第 14 章第 10 節中,我們讀到:“但全會眾說,拿石頭打死他們二人[摩西和亞倫]。”以色列的許多其他先知,一直到施洗者約翰和耶穌,也都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在《聖經》中,“先知被殘暴殺害的命運”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關鍵的一段經文是《以賽亞書》第 53 章,描述了上帝的仆人所承受的苦難。根據這些線索,弗洛伊德推斷,猶太人最終殺害了摩西,因為他們發現從長遠來看,他們無法滿足摩西高度抽象、精神化的宗教所強加給他們的嚴格要求。智性的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優越感,總是會引發反動性的暴力。摩西是第一個受害者,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殺害他的猶太人是第一批“反猶主義者”。“反猶主義”——在弗洛伊德在寫這本書時是特別緊迫的議題——是對智性的反抗,而這個世界對智性的容忍總是勉勉強強。反猶主義是反一神教,因此也是反智性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一旦證明摩西是埃及人,並且他所宣揚的一神教與猶太人自己的傳統毫無淵源,那麽,猶太民族的建立,就更顯得只是摩西一個人的功勞。亞伯拉罕則僅僅是一個為了歴史連續性而虛構出來的形象。作為一個民族,猶太人的存在是由外部的驅動力所致。
對於弗洛伊德來說,摩西是埃赫那頓的支持者,他將一神教傳給了居住在三角洲的猶太人,並在法老去世後與他們一同移居巴勒斯坦。然而,摩西的一神教高度抽象,它對他們提出的智性和靈性的要求太高,猶太人無法達到這樣的要求,最終殺害了摩西,然後掩蓋了他們所做的事。他們的集體行為是一次創傷性經歴,因為他們在此事件中演繹了被壓抑的記憶——即原始父親被殺的事件,這個記憶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演化的開端。摩西之死,意味著“被遺忘的記憶痕跡被近期的真實重演而喚醒。摩西之死就是這樣的重演。”摩西的一神教意味著“父親的回歸”,而摩西之死則重復了原始父親被兒子們殺害的事件。弗洛伊德論證的核心悖論在於,只有通過被殺害,然後相關的記憶被壓抑,摩西才能成為那個銘刻史冊的記憶形象——“猶太民族的創造者”。摩西死後,他所倡導的一神教經歴了幾個世紀的潛伏期,最終再次影響大眾。如果認為這兩個事件之間可能存在關聯——一方面是被壓抑的關於謀殺的記憶,另一方面則是被壓抑的這段記憶的回歸——那麽就得回答它們之間的時間差異的問題。埃赫那頓生活在公元前 14 世紀,可《聖經》一神教直到公元前 8 世紀的先知運動才開始真正發展,並在後流亡時期才最終達到弗洛伊德所理解的純粹和激進的“一神教”狀態。為了解釋這種時間上的延遲,弗洛伊德提出了“潛伏期”的概念。他的壓抑理論認為,存在一種保存(記憶)性的遺忘。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排他性一神教的觀念被這種“保存性遺忘”所掩蓋,使猶太人能夠從公元前 14 世紀一直到公元前 5 世紀都保留了這一記憶。
對於弗洛伊德而言,摩西之死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被壓抑了;只有這種被壓抑的內容“回歸”時所產生的獨有的不可抗拒的強大動力,才能幫助猶太人實現一神教的最終突破。正如原始父親的謀殺終結了原始部落制度,成為文化和圖騰宗教的奠基之舉(或奠基之罪),摩西之死也終結了多神教,成為一神教的奠基之舉(或奠基之罪)。每一個真正引人入勝和精神上令人著迷的傳統都建立在一種壓抑行為之上,不留情面地講,都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深入到集體精神生活的這個深度層面,揭示出這個起源,一個不僅從意識記憶中失落的起源(即書面傳播),而且——根據精神分析理論的所有規則——也已經被壓抑為一種深刻的創傷性經歴的起源。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表層和深度之間的分裂究竟在哪裏發生?它是否位於個體的精神結構中——在這個情況下即猶太人的靈魂——然後認為他們在潛意識層面保留了對於共謀——參與摩西的謀殺——的記憶,但卻在意識層面上壓抑了這種記憶?還是它實際上存在於書面和口頭傳統的文化記憶中,在其表層含義之下,只有通過蛛絲馬跡來獲得更深層次的意義?為了捍衛弗洛伊德免受耶魯沙米(Yerushalmi)將其稱為心理拉馬克主義(psycho-Lamarckism)的責難,雅克·德裏達和理查德·伯恩斯坦都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轉移理論解讀為像“檔案”(德裏達)和“傳統”(伯恩斯坦)這樣的文化機制。但是,弗洛伊德在他關於摩西的研究的第一部分總結中,清晰而明確地表明了他的立場,他反對文化檔案的解釋,並支持心理拉馬克主義。這一段落值得完整引用:
當我們研究對早期創傷的反應時,我們經常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反應並沒有嚴格限於主體自己真正經歴過的事情,而是以一種更適合種繫(phylogenetic)事件模型的方式偏離這些經歴,總的來說,我們只有通過這種影響才能解釋它們。在俄狄浦斯情結和閹割情結的影響下,患神經症的兒童對父母的行為充滿了這種反應,這類反應在個體案例中似平是不合理的,只有與早期世代的經驗聯繫起來,才能在種繫學上被理解。將我在這裏引用的那此資料,整理並呈現給公眾將是非常值得的。這些證據對我來說足夠充分,足以讓我冒險邁出更遠的一步,斷定人類原始遺產不僅包括稟性,還包括主體觀念——早期世代經驗的記憶痕跡。這樣,原始遺產的範圍和意義將得到顯著擴展。
經過進一步的思考,我必須承認,我表現得好像以下假設是毋庸置疑的,即祖先經驗的記憶痕跡可以直接遺傳給下一代,並不一定要經過直接溝通和受到示範教育的影響。當我談論某個民族傳統傳承或民族性格形成時,我腦海中想到的往往是這種直接繼承的傳統,而不是通過交流傳遞的傳統。或者至少我沒有區分這兩者,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忽視這種區分的輕率。毫無疑問,當今生物科學的態度令我的立場更難站得住腳,它們拒絕承認後代會繼承後天習得的特性。然而,我必須謙虛地承認,盡管如此,在解釋生物進化過程時,我仍然無法擺脫這一因素。誠然,這兩種情況並不完全相同:一種涉及難以捉摸的後天習得特性,另一種涉及外部事件的記憶痕跡——仿佛是某種具體可感的實物。但或許從根本上說,在這二者之中,我們無法在忽略一個的情況下去想像另一個。
如果我們承認這些記憶痕跡存在於民族的原始遺產中,那麽我們就彌合了個人和群體心理之間的鴻溝:我們可以像對待神經症患者一樣來理解民族行為。
這段話明確表達了弗洛伊德站在生物學而非文化史學的一邊。與之相反,記憶歴史(Mnemohistory)則將研究範圍局限於文化傳播的檔案(archive)。它不需要借助種族遺傳(phylogenetic)的原始記憶。我對弗洛伊德的批評在於,他關於文化記憶(或文化檔案)的概念過於薄弱,因為他將其局限在“自願記憶”(volunté mémoire)層面,即在有意識情況下傳播的信息。
僅僅建立在交流之上的傳統無法產生宗教現象所具有的那種強迫性特徵。人們會像對待任何來自外部的信息一樣,對其聆聽、評判,或者否定,它永遠無法獲得跳過邏輯思考限制的特權。它必須經歴被壓抑的命運,在潛意識中徘徊,然後才能在其回歸時展現出如此強大的影響力,讓大眾臣服於它的魔力,就像我們在宗教傳統中驚嘆不已卻難以理解的那樣。
文化傳播的檔案是多層次疊加在一起的,保存著許多已經無法在其原始含義和功能上被理解的內容。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摩西本人:他的名字源於埃及語,卻有著希伯來語的詞源解釋——“從水中被救起的人”。另一個例子是在麻風病人傳說中被延後的來自阿瑪納時代和喜克索斯時代的記憶。文化記憶不僅僅是一種“自願記憶”,還是一種“非自願記憶”(mémoire involontaire);許多深層的信息潛藏其中,經過漫長的潛伏期後,可能會再次爆發並攫取人們的想象力。
我認為,一神教的創傷(如果存在的話)並不是建立在雙重的弒父之上——首先是原始父親,然後是摩西——而是建立在雙重的弒神之上——首先是“異教”神靈,然後是一神教自身的神。換句話說,一神教內在的毀神論(theoclastic)暴力傾嚮,最終會把矛頭指嚮它自身的神。不僅是否定神學(negative theology),甚至連“上帝之死”都可能會成為智性進步的道路上的必經之處。
禁止造像是一種智性進步
弗洛伊德將禁止造像的規定看作是智性發展的決定性突破或進步:
在摩西宗教的戒律中,有一條看似簡單,實則意義深遠。這就是禁止制作神像——即強制人們只能崇拜一位看不見的神。我懷疑,摩西在這方面比阿頓宗教更加嚴格。也許他只是想要保持一致,讓他的神既沒有名字也沒有面容。也許這也是針對魔法濫用的新措施。然而,如果這條禁令被接受,它一定會有深遠的影響。因為這意味著感官知覺讓位給一個可以稱為抽象概念的東西——這是智性戰勝了感性,或者更准確地說,是一種對本能上的放棄,它必然會帶來一繫列心理後果。
對於弗洛伊德來說,摩西的這一禁令意味著邁嚮一個新世界。“開啟了一個智性的新領域。”拒絕偶像,僅此一項就打開了新的精神領域的大門。弗洛伊德認為,第二誡命強調了上帝是絕對無影無形的,同時也是絕對無法描繪的。考慮到這條戒命禁止的是所有偶像,而不僅僅是上帝的形象,如今人們可能更傾嚮於強調雅威的獨一性,並要求人們專一地崇拜他。按照這個思路,每一個圖像都隱含著被當作神靈崇拜的潛在可能性,而既然真神無法被描繪,它必然是一個“異神”。然而,弗洛伊德對造像禁令的解讀古已有之。古典時期已經有人作出這樣的解讀。根據公元前 4 世紀下半葉的赫卡泰奧斯(Hecataeus of Abdera)就寫道,摩西禁止神像,是因為他“認為神不具有人的形象,只有環繞大地的天堂才是具有神格的,他主宰著宇宙。”摩西所創立的真正宗教在於崇拜一位“包羅萬象”(peri-echon)、獨一無二的天神,而且不為其制造任何聖像。在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 1 世紀)的記載中,一位名為摩西的埃及祭司決定離開自己的國家,並與許多對埃及宗教同樣不滿的人一起遷居到猶地亞,他教導人們,神就是“我們稱之為天堂、宇宙或萬物本性”的存在。這種神聖的存在無法以任何形象復刻:“是的,人們應該停止一切雕像刻制,並且…應該不以形象來崇拜神。”要接近神,所需要的僅僅是“過自律和正直的生活”。對斯特拉波來說,智性的進步首先意味著宗教的倫理化。摩西的神不贊成血腥的祭祀和狂歡的舞蹈;他要求的是正直。當然,斯特拉波在這裏只考慮了十誡。他認為希伯來人後來偏離了摩西的純正教義,發展出了迷信習俗,諸如飲食禁忌、割禮和其他儀式。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種無聖像崇拜式的信仰與倫理道德之間的聯繫對弗洛伊德而言也十分重要。在追溯猶太教起源的學者中,約翰·托蘭德(John Toland)是弗洛伊德的先驅者之一,他在其著作《猶太起源》(Origines Judaicae,1709)中,以斯特拉波的記載為基礎,重建了猶太人的起源。塔西陀(Tacitus,公元 1 世紀)同樣將猶太人對神的概念描述為一神論和無偶像崇拜:“埃及人崇拜許多動物和怪物形象;猶太人只構想了一個神,且僅用意念(mente sola)來想像;他們認為用易腐朽的材料制作人形的神像是對神的褻瀆;對他們而言,那位至高無上的永恆存在無法被描繪,同時也是無限的。”
對弗洛伊德而言,相信自己是神的選民是猶太身份的核心。這種信仰及其帶來的自豪感,源自對偶像崇拜的禁令,及其所要求的對本能沖動的放棄。弗洛伊德認為,禁止造像意味著他定義的一神教三大要素:“唯一神的概念、對魔法儀式效用的否定,以及強調以神的名義對道德的要求。”禁止造像與倫理的聯繫,或者說偶像崇拜與無法無天、淫亂和暴力的聯繫,在《聖經》傳統中根深蒂固。先知們否定了(或至少相對化了)獻祭崇拜,並首先呼籲人們追求正義。律法——在這裏是指倫理規範——被宣稱為神的旨意,只有遵守律法地生活,才能夠取悅於神。弗洛伊德的智性進步的概念將禁止造像與放棄本能欲望聯繫起來。禁止造像意味著捨棄感官,轉嚮精神。弗洛伊德認為,一神教是一種升華的壯舉。它意味著對世界說“不”,這與我在禁止造像和一神教自身中所看到的相同,對我持批評態度的舊約學者自稱對此一無所知。我重申我的立場,因為我並不打算批判一神教,恰恰相反,我完全贊賞這一智性上的突破(盡管它總是受到威脅,並且經常又倒退回去)或者說“進步”。遵守律法的人,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得像個陌生人。因此,詩篇第 119 章第 19 節寫道:“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求妳不要嚮我隱瞞妳的命令。”堅守律法意味著即使在應許之地,也要在世上像個陌生人一樣生活。律法勾勒出一個反事實的秩序,迫使其信徒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卻不會完全被同化。一神教助長了存在主義式的異鄉感。這種對世界的疏離感,就是“智性進步”的含義。
必須承認,弗洛伊德將禁止造像解釋為智性進步上的突破,以及猶太人身份和驕傲的核心元素,這在內在合理性上相當令人信服。然而,另一方面,有人可能會反對說,猶太人這種從感官領域嚮精神領域的轉變,並非獨一無二的案例,而應該被視為人類歴史上普遍突破——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所謂的“軸心時代”(axial age)——的一部分(盡管其形式獨特)。
這裏首先要提到的名字當然是柏拉圖。柏拉圖的哲學是最具堅決的一次嘗試,它試圖擺脫感官世界,進入一個只有精神之眼才能領悟的真理世界。在這方面,它為無數基於更高精神世界理念的哲學和宗教運動鋪平了道路,尤其是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赫爾墨斯主義(Hermeticism),以及最重要的,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整個西方思想深受柏拉圖精神哲學的影響,甚至弗洛伊德自己的文本也受到了柏拉圖主題的影響。然而,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並沒有提及柏拉圖。就像海涅一樣,弗洛伊德通過將猶太人與希臘人對立起來,來構建他關於智性進步的概念:“在猶太民族約兩仟年的生活中,智力勞動佔據的首要地位自然產生了影響。這有助於抑制在尚武精神盛行的地方出現的野蠻和暴力傾嚮。” 弗洛伊德充分意識到,“發展體魄”並不能完全體現希臘的“普遍理想”,因此他繼續說道:“希臘人民所取得的智力和體力培養方面的和諧,對猶太人來說是無法實現的。”最後,他總結道:“在這種二元對立中,他們的選擇至少是更值得稱道的選擇。”
如果有人問希臘人在哪個領域對西方產生了最持久的影響,以及,在希臘傳統中,究竟哪裏可以被看作西方文化的源頭,那麽人們就不得不指出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形而上學。體育和健身文化是相對晚近的革新,雖然它們可能已然成為我們當代西方身份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在古老的歐洲傳統中並無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至少從尼採的時代開始,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柏拉圖的二元世界觀可能將一種並非源於希臘本土的二元論引入了希臘思想。誠然,柏拉圖具有深遠的影響,但他並不能被視為希臘文化的代表性人物。直截了當地說,他更接近海涅的對比中的猶太人那一邊。畢達哥拉斯學派學者諾米尼烏斯(Numenius of Apamaeia)稱柏拉圖為“說雅典話的摩西”,並非毫無道理。因此,弗洛伊德選擇忽略柏拉圖,並在人類智性進步史上賦予猶太人特殊地位,這樣做或許是有道理的。
然而,在這方面更引人註目的是他對基督教的評價。對他而言,這個宗教標誌著智性的顯著衰退,因為它回歸到了偶像崇拜和魔法儀式之中,尤其是圖騰宴的祭祀儀式,在這個儀式中,信徒通過食用聖餐與神實現聯結。這種從局外人的視角得到的過度簡化的觀點,可以部分歸因於弗洛伊德個人的宗教經歴,他所接觸到的應該僅僅是維也納當地流行的天主教信仰,另外,也可能是他受到 W. 史蒂文森·史密斯(W. Stevenson Smith)、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和詹姆斯·弗雷澤(James Frazer)等人的作品的影響。一位猶太觀察者對奧地利民間天主教的外部形式產生——即使不是徹頭徹尾的厭惡——不悅,這完全可以理解,正如西方反猶主義恰恰是抨擊猶太教的某些外在形式一樣。宗教之間相互的厭惡往往只源於對彼此表面儀式的觀察,而不是基於從彼此內部對其神學的深入理解,因為作為外部的觀察者,他們往往無法接觸到這些內部的信息。事實上,從其內部的視角來看,基督教不同於其他宗教的主要根本原則正是與弗洛伊德的“智性進步”不謀而合。人們不禁會說,在提出“智性進步”這個說法時,弗洛伊德借鑒的是基督教的陳詞濫調而非柏拉圖的。然而,我懷疑他使用基督教的主題詞是有用意的,而且還帶有一定的諷刺意味。在基督教的反猶論述中,“智性進步”的觀念是一個標准要素,一再被用來合理化它對猶太律法的排斥。保羅對律法的批判正是以“靈”和“肉”的概念展開的。“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聖靈是叫人活”[2]。這個主題貫穿於整個基督教傳統。哈拉卡(Halacha,猶太法律)被貶斥為“因行稱義”,因此被視為外在的和物質的。律法與信仰相對立,指嚮一個既不能僅憑感官也不能單靠理性達到的神的國度。“因其荒謬,故而信之”(credo quia absurdum)——弗洛伊德在這一語境中兩次引用了這一典型的基督教信條,卻沒有看到它與他對基督教的評價之間的矛盾。按照基督教的觀點,猶太人仍然深陷於肉體之中:“屬肉體的以色列”(Israel carnalis)。只有走出律法的世界,才能進入靈性的國度。
在基督教神學中對靈性的這種堅持不懈,一直追溯到耶穌和聖保羅的教導,以對弗洛伊德對這一傳統的借鑒程度而言,他絕不可能沒有註意到這一點。因此,在我看來,更有可能的解釋是,他想從基督徒那裏奪走這一基督教的核心神學理念(theologumen),並將其歸功於猶太人,這是對基督教的竊取習性的一種諷刺性顛覆,因為基督教一貫宣揚的自我成就,例如愛鄰如己、愛仇敵、對內在自我的強調等等,其實都是竊取自猶太教核心的概念。這就是為什麽他將保羅原本用來合法化基督教拒絕律法的公式,應用到造像禁令和猶太人對神像的拒絕上。弗洛伊德認為,基督教“吸收了許多其他來源的成分,放棄了純粹一神教的某些特徵,並在許多細節上適應了其他地中海民族的儀式。” 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埃及:“就好像埃及再次對埃赫那頓的繼承者實施復仇一樣”。 弗洛伊德在另一段文字中表達得更為明確:
從某些方面來看,基督教相較於更古老的猶太教而言,代表了文化上的倒退,這種現象在歴史上經常出現,當大量文化水平較低的新群體加入或被接納進入一個文化傳統時,往往會降低整體的文化水平。基督教宗教在思想方面沒有保持猶太宗教所達到的高水平。它不再嚴格奉行一神論信仰,而是從周圍的民族吸取了許多象徵性的儀式,重新引入“大地母親女神”,並且在一種極易識破的偽裝之下為多神教的眾多神祇找到了容身之處,雖然只是將他們置於次要位置。最重要的是,它不像阿頓宗教和其後的摩西宗教那樣嚴格排除迷信、魔法和神秘主義元素,這些元素在接下來的兩仟年裏嚴重阻礙了人類的智性發展。
弗洛伊德拒絕承認基督教對宗教靈性的激進化是智性進步的證據。他在談到基督教的興起時寫道:“後來,智性本身被一種令人費解的情感現象——信仰——壓倒了。這就是著名的“因其荒謬,故而信之(credo quia absurdum)。”因此,弗洛伊德不僅沒有將這一發展視為智性發展上的更進一步,反而將其視為對智性的摒棄。他認為,隨著理性被視為為非靈性或不夠靈性而被拒絕,基督教跨越了通往神秘主義——他將其與魔法混為一談,並認它為與智性無關——的界限。在他眼中,(猶太人的)智性(intellectuality)與(基督教的)靈性(spirituality)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他所說的“智性的進步”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通過理性化過程使“世界祛魅”的命題非常相似。在這方面,基督教標誌著朝著將世界再度魅化的反方嚮邁出的一步。出於同樣的原因,弗洛伊德也無法將柏拉圖、諾斯底主義或赫爾墨斯主義的神秘主義視為智性進步。然而,根據這些運動對自身的理解,它們追求的恰恰正是這個目標。整個崇拜儀式的領域被內化並轉變為一種被稱為智性祭祀(intellectual sacrifice,thysia logikē)的精神活動。“Logos” 意為“理性”,“thysia logikē”同樣可以被理解為“理性的宗教”。哲學上的神秘主義將自己視為高度理性的智慧活動。在晚期古代,整個地中海世界都陷入了這種對智性化的渴望中,當時湧現出的許多運動將在未來幾個世紀對西方思想史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不論是從基督教自身的內部視角來看,還是從其眾多哲學和神秘主義派別的角度來看,或者是從其敵對派繫(包括猶太人的卡巴拉)的視角來看,智性(intellectuality)與靈性(spirituality)的區分都根本無法維持。
所有這一切都可能被用來反駁弗洛伊德的構建——猶太人是智性進步的先驅,因此西方文化起源自猶太人。然而,盡管如此,正如另一部同樣假定西方文化源於猶太教的著作的標題所言:“起源於猶太教的理性宗教”(Religion of Reason, Out of the Sources of Judaism,赫爾曼·科恩(Hermann Cohen)著),弗洛伊德從“猶太教中推導出理性宗教”的論證也有一定的道理。
盡管最初可能並非出於這個目的,但禁止制造聖像包含了一種極具理性的沖動,這種沖動在後來的解釋中,尤其是宗教諷刺的形式中,得到了充分展現。這種對宗教批判的形式植根於猶太人的造像禁令,弗洛伊德的《摩西》一書也顯然傳承了這種批判,尤其是在他的病理學成像中。隨著對造像的禁令,神聖世界中的真假之分,以及隨之而來的理性和瘋狂之分,首次進入了宗教領域。“摩西禁令”構建了一個阿基米德點,以這個點為支點,偶像崇拜的宗教可以被揭示為一種幻覺,而弗洛伊德最終也可以以此揭示宗教本身的虛幻質。智性進步在於我們逐漸從偶像崇拜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些束縛限制了我們的思想。通過重新審視禁止造像的禁令,弗洛伊德揭示了這種追求思想解放的鬥爭從深層來講是一項猶太人的偉業,同時也是他自稱繼承並通過他的精神分析嚮前邁進一步的傳統。如果人類的使命在於智性進步,那麽猶太人將走在最前列。
第五章:一神教的心理歷史影響
我想從文化記憶和記憶歷史理論的角度,將一神教(或反宗教)的一些心理歷史影響,總結成以下四點。
“經文轉向”:從儀式到經典
從原始宗教到次生宗教的轉變,可以被理解為從儀式(ritual)到經文(text)的轉變。在原始宗教或早期宗教中,經文被嵌入到儀式之中,並服從於儀式,但在一神教中,經文(即正典書寫的形式)占據了核心位置,而儀式則被降到輔助性和補充性的角色。這種從儀式到經文的轉變標誌著一種分水嶺,它將宗教劃分為兩種類型:儀式型宗教(cult religions)和經典型宗教(book religions)。後者包括西方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以及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所有的次生宗教都是經典型宗教。它們都以一套神聖經文為基礎,例如《希伯來聖經》、基督教《聖經》、《古蘭經》、《耆那教聖典》、《巴利文大藏經》和《錫克聖經》。一神教的轉變與媒介的改變相互關聯。在次生宗教中,書寫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相伴相生,正如在原始宗教中,儀式和內在性(immanence)相伴相生一樣。兩百多年前,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就已經注意到宗教史和書寫史之間的這種聯繫:“在我看來,不同文化時期文字形式的變化,在整個人類知識的總體革命中,以及在人們對宗教問題的各種觀點和想法的轉變方面,始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門德爾松當時所考慮的是(追隨威廉·沃伯頓(William Warburton)和賈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腳步)從象形文字到字母文字的轉變,而我在這裡主要關注的是從口頭流傳到書面傳統的轉變,從“儀式”到“文本連續性”(textual continuity)的轉變。
與儀式連續性原則緊密相連的理念是:世界需要保持在其既定的運行軌道上。儀式文化或儀式型宗教通常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如果不按照規定方式舉行儀式,宇宙就會遭受破壞,甚至走向終結。儀式總是用來支撐宇宙的秩序,否則秩序將面臨崩潰。當這個理念開始失去影響力時,就出現了文本連續性。對於《聖經》來說,這一轉變是由創造神學(theology of creation)和意志神學(theology of the will)的興起帶來的。世界的持續存在不是因為任何儀式的執行,而是因為超越性的神的保護意志和作為。儀式連續性原則以及維持世界運轉的需要與祭司這一社會類型息息相關,正如經注家、學者和傳教士這些社會類型與文本解釋原則相對應一樣。嚴格的潔淨律法將祭司與群眾隔開。他通過洗滌、禁食、禁慾和其他形式的“神秘苦修”(借用馬克斯·韋伯的術語)與其他人區分開來,從而獲得儀式上的潔淨。因此,首先,他是否適合擔任祭司職位是一個生理上的問題;與經典型宗教相比,體魄在這裡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從儀式型宗教到經典型宗教的轉變伴隨著神聖性本身的結構性轉變。原始宗教或儀式型宗教的神聖性主要表現在它顯化於世俗世界的方式(希臘語:hieros,拉丁語:sacer)。在經過儀式淨身後,祭司接觸到的神聖性存在於世界之中。在一個特定的地點,神聖性被具象化並顯現,並通過高牆將這個地點與日常的凡俗世界分隔開來。與神聖性的接觸要求祭司保持一種聖潔的狀態,即希臘語“hosios”,和拉丁語“sanctus”所指的含義。這意味著一種與世俗領域隔絕的狀態。相比之下,次生宗教取消了這種區分,因為對它們而言,神聖性不再存在於世俗世界之中。唯一仍然被視為 hieros 或 sacer 的是神聖的經典,即 biblia sacra(神聖的書)。這就是為什麼在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中,圍繞宗教經典出現了明顯源自儀式的觀念和律法。因此,例如,猶太人被禁止將聖經放在地上,而穆斯林則既不允許銷毀用阿拉伯文字和語言寫成的任何東西,也不允許將其帶到不恰當的地方閱讀,即使所涉及的材料只是一份報紙。基督教,尤其是誓反教,則拋棄了這些儀式的最後殘餘。經注家或傳教士之所以勝任其職,是因為他們對神聖文本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們懂得如何閱讀和背誦它們,將它們熟記於心,能夠通過參照其他經文來闡釋某個特定章節,最重要的是,他們懂得如何將它們與當下的現實生活聯繫起來。在這裡,與自然的直接互動已經不再重要。他職責履行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他的布道被會眾理解和吸收的程度,即神聖經文的教誨轉化為日常行為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的程度。
神聖性從世界中的逃逸——一方面遁入超然存在,另一方面進入經典——這一現象產生的心理歷史後果導致了注意力的根本轉移。曾經關注的對象是世俗世界中的顯象和在這些顯象中顯現的神聖性,現在完全轉移到了經典之上。其他一切都被視為偶像崇拜。這個世界上的事物,尤其是圖像,被視為會誘使思維遠離經典的陷阱。信徒有責任防止自己跌入這些陷阱。對圖像和視覺領域的妖魔化,還伴隨著一場語言改革,旨在將宗教去感性化並解構儀式的戲劇性。摩西·門德爾松也清楚地看到了這些後果。他哀嘆道:“我們是文人,是文學家,我們的整個存在都依賴於文字。”他之所以讚賞猶太律法,正是因為它通過規定了如此多的儀式,才在經典型宗教的條件下挽救了宗教的審美維度。
儀式連續性原則的基礎是,媒介可以在世俗世界中令神聖性以視覺形式呈現。這些媒介包括聖地、樹木、泉水、岩石、洞穴和樹林,但首先還是圖像、雕像、符號以及建築裝置,例如寺廟、金字塔和佛塔。當進入神聖性顯現的空間時,祭司必須調整自己的行為。我們在《出埃及記》第 3 章第 5 節中讀到,“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神聖性以物理和可視的方式存在的地方,會遵循不同的律法,違反這些律法可能會招致致命的後果。對於嵌入儀式之中的神聖文本也同樣如此,它們會在儀式過程中被誦讀。它們也使神聖性得以顯現。在正確的地點和正確的時間,由正確的人以正確的方式朗誦時,這些經文會釋放出宇宙力量,幫助維持世界的運轉。在古埃及晚期,這些文本被統稱為“拉神之力”(power of Re),意義類似於“太陽能量”。埃及祭司在誦讀這些經文之前必須咀嚼蘇打並清潔口腔,這些經文必須被嚴格保密,並像聖地、神像和符號一樣受到保護,以免遭到褻瀆。
在猶太教中,書寫與崇拜儀式的關係發生了逆轉。在這裡,書寫不再是編排或記錄宗教儀式的工具。書寫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重要存在。宗教儀式被簡化為經文的重演,形式包括共同誦讀、紀念、宣誓和解釋。這代表了一次徹底的轉變。書寫不再被用於穩定儀式,而是取代了其位置。
在比較猶太教與希臘化宗教(即異教)時,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弗拉維奧斯(Josephus Flavius)已經領悟了“儀式”連續性和“文本”連續性之間的關鍵差異,他寫道:
“難道還會有比這更聖潔的政體嗎?難道還有什麼比這樣的制度更能讓上帝得到他應得的榮耀?在這種制度下,宗教是整個社區教育的目的和終點,祭司受託承擔其特殊職責,整個國家的治理彷彿就是某種神聖儀式。其他民族以神秘主義和皈依儀式之名推崇的實踐,只能勉強遵守幾天,而我們卻能欣然接受並矢志不渝地堅持一生。”
當異教徒們必須等待下一個儀式才能參與其中時,猶太人卻可以永久擁有他們的文化文本,他們通過祭司的點化,接受了關於這些經文的教導。他們的“奧秘”——在祭司的解經指導下閱讀這些經文——是永久而持續不斷的。
這是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巧合之一,耶路撒冷聖殿恰好在猶太宗教的內部發展使其變得多餘的時刻被摧毀。公元 70 年提圖斯(Titus)摧毀聖殿時,經文早已取代了聖殿的位置,而儀式本身的意義也從內部被架空。耶穌運動只是眾多猶太教(以及希臘宗教)運動中的一部分,試圖通過升華、倫理化和內化來破除祭祀宗教——即血祭或儀式性屠殺——的基本理念。即便提圖斯沒有摧毀聖殿,它最終也可能被關閉——否則,猶太教,以及由此產生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將永遠不會興起。聖殿已經失去了它的用處,因為它所容納的祭祀儀式早已在經文的墳墓中長眠。
有許多證據表明,猶太一神教、啟示原則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傳統祭祀宗教實踐日益增長的厭惡,都源於經文的精神,或者至少與書寫媒介有著根本性的聯繫。兩百多年前,摩西·門德爾松就看到了這種媒介革命與宗教轉變之間的聯繫。邁入超越性宗教的一步,同時也是踏出塵世的一步——在這個語境下,我們幾乎可以說是一場“出埃及記”——走入經文之中。經典化的經文最終取代了藝術、公共生活和整個世俗世界。這個世俗世界本身被宣稱為偶像崇拜的對象,並被否定。對造物主的崇拜不能與他的創造物糾纏在一起。神的徹底超越性與他的啟示的徹底文本性相呼應。
至此,我們觸及了書寫與超越性(transcendence)之間的一種聯繫,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用簡潔明快的語言總結道:“如果沒有文化技術……,我們將永遠不會知道除了存在之外還有其他東西。天空將只會是天空,大地只會是大地,所謂的人類只會是男人和女人。然而,神聖的啟示帶來了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人文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聖經》和《古蘭經》並非起源於祭祀儀式中的(cultic)程式,而是源於律法和故事。從本質上說,它們的規範性更多是道德和法律上的,而不是通神法力(theurgic)。它們為一種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礎,而不是為祭祀儀式提供了基礎。經文與宗教儀式對立,標誌著它的終結。18 世紀所謂的“實證宗教”(positive religion),將其與“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相對立,並將其視為一種人為的東西,如果沒有書寫和解經的文化技術,它將是難以想像的。先知的一神教缺乏自然證據;正如聖保羅所說,它不是基於視覺而是憑藉信心的。信仰由經文、契約和律法來支持。祭祀則依賴於儀式的舉行、表演和視覺。經文導致對宗教的去儀式化和去戲劇化。
走進“地下室”
次生宗教經驗不能簡單地被歸納為對異教“虛妄意識”的否定。它比那更複雜得多,它在一個綜合與融合的過程當中吸收了原始宗教體驗的形式和元素。沒有任何一種新興宗教或次生宗教完全成功地抹去了衍生他們的原始宗教的痕跡;相反,它們經常會接收這些痕跡,並將其調整為適合自身的目的。確實,狄奧·桑德梅爾認為,它們成功接收這些痕跡的程度決定了它們同化其他宗教和吸收新信徒的能力:“宗教史並不是這樣進行的:即由次生宗教的先驅者和創始人開創的新體驗取代原始宗教體驗。相反,是在第三階段,在一個否定和象徵性重新整合的複雜過程中,原始宗教體驗的重要元素被整合和融入一個新的綜合體中。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一種有機的融合機制在發揮著作用,它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可非議的。這種綜合越成功,新宗教成為一種可行的普世宗教的機會就越大。”
然而,這些“核心元素”的“異教”來源必須被遺忘和掩蓋。因此,可以說,次生宗教或反宗教通過汲取原始宗教體驗和宗教實踐的元素來豐富自己,發展出一種新的無意識形式,同時又必須重新詮釋它們的語義,重新調整它們的形態,以適合新的語境。這些元素構成了次生宗教建築中的一個“地下室”(crypt),一個不再被刻意培養的宗教語義的光芒照亮的地下領域,然而,新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古老的)衝動隨時可能從其深處升起,將人們再次置於它們的迷咒之下。
這讓人想起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弗洛伊德將一神教的興起描述為“被壓抑的經歷的回歸”。對他而言,宗教歷史也呈現為一種記憶的層積。最底層或最深的“地下室”由他所謂的“原始遺產”所代表,即“原始部落”留下的父權制俄狄浦斯烙印。在文化發展的後期階段,殺戮被終止,父親被提升為神靈。祭祀和圖騰餐取代了原始暴力。(原始)宗教出現並埋葬了史前的恐怖事件,這些恐怖記憶沉澱在人類心靈的無意識基礎上,形成“原始遺產”,伴隨著儀式和禁忌。在埃及人摩西的一神教要旨中,父權宗教及其對升華的嚴格要求、純潔和正直的規範,以一種新偽裝從無意識中重新浮現。“摩西之死”,實際上是重演了一個未被銘記的歷史事件[3],它作為一次創傷性的經驗深深刻在猶太靈魂中,並在經過幾個世紀的潛伏期後,最終以“被壓抑經歷的回歸”的力量,爆發於先知們的一神教要旨中。
誠然,弗洛伊德對“圖騰宗教”和“一神教”的區分與原始宗教和次生宗教的區分大相徑庭,如今也很少有人會全盤接受他關於“原始部落”和摩西之死的神話。如果不是因為這個理論為挖掘文化記憶的深層結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深刻見解,我們大可以毫不猶豫地將其置於科學神話創作的博物館裡。這種記憶形式不能簡化為接收傳統和領會新知識的意識性活動,它更多是以突然迸發、斷斷續續、時隱時現、潛伏再爆發的方式運作。最重要的是,它永遠不會在當下完全實現,而是不斷地將舊元素與新元素融合構成新的綜合體。與次生宗教融合的原始宗教體驗的形式,也可以被描述為“原始遺產”,但是卻不再是按照弗洛伊德的定義,而是全然不同的一種含義。它可能並未銘刻在人類心靈之中,但它仍然構成了宗教傳統的深層維度,一個“地下室”,就像語言一樣,它承載的知識和記憶,遠遠多於生活在這一傳統中的人們能在意識層面接觸到的。
這種看法由來已久,即認為《聖經》一神教是一種兩面性或自相矛盾的宗教,其經文所表達的外部或上層,與隱秘的內在或下層之間存在分裂。我在第三章已經討論過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提出的宗教理論,我將在此背景下再次回到這一話題。在 12 世紀,當邁蒙尼德以“顛倒規範”的原則為引,試圖為摩西的儀式律法尋找解釋時,他認為一神論宗教包含了一個深層維度,異教信仰正是被推入這個維度之中,然後被排斥被遺忘。對邁蒙尼德而言,毋庸置疑的是,踐行律法的人不再意識到其中與原始異教對立的最初含義。
宗教學研究首次揭示了這些深層維度,邁蒙尼德重新發現異教信仰或拜星教,並因此被公認為是這一學科的奠基人。他將儀式律法的功能解釋為一種遺忘的藝術,是一種戒斷拜星教偶像崇拜的治療方法。根據這一理論,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整個《聖經》宗教作為一個複雜的祭祀習俗、儀式和實踐規則的體系,呈現出雙重性。它被視為一個歷史性的和有期限的容器,這個容器承載著永恆的真理,並被隱藏在它自身內部,只有經過漫長的淨化過程,打破偶像崇拜的束縛,人們回歸到對神的純淨認知後,真理才會盛行。因此,邁蒙尼德將律法稱為“divrej kfilayim”(“重複的話”或按斯賓塞的翻譯,“verba duplicata”)。它們具有一層明顯的含義和一層隱藏的含義。相比之下,拜星教的儀式除了表面上公開可用的含義之外,別無其他含義。當一個宗教保留了它所拒絕的傳統,而又在其上疊加了與之相對立的新傳統(來覆蓋它)時,這導致的結構會令它呈現出一種雙面性。這與桑德梅爾對原始宗教和次生宗教體驗的區分以及反宗教概念相類似。次生宗教或反宗教是表裡不一的:它們表面上拒絕異教信仰,卻在其內部加密保存了異教信仰的元素。
內在自我的構建
正如狄奧·桑德梅爾特別強調的那樣,次生宗教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它們意識到自己的新穎性。毋庸置疑,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些一神論宗教並不認為自己是次生宗教或反宗教。在它們看來,唯一的原始宗教就是一神教,而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的奠基工作僅僅標誌著回歸到被謬誤淹沒的一神論真理。因此,《出埃及記》神話對從原始宗教到次生宗教的轉變過程的描繪的精準性就更加引人注目。通過這一過渡——這場被猶太人和基督教傳統視為從“律法之前”(ante legem)到“律法之下”(sub lege)的跨時代的轉變——宗教實現了一次質的飛躍。它將自己置於嚴格的規範基礎之上(律法);將自身與“他者”嚴格區分——“埃及”和“迦南”是這一過程的核心象徵——它以“盟約”(b’rît)的形式出現,模仿政治聯盟,根據這個盟約,以色列不僅同意成為神的子民,神也同樣承諾成為一個民族的神。在這裡談論追根溯源沒有任何意義。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造。我將整個出埃及和西奈事件(Exodus-and-Sinai)理解為是對從原始宗教到次生宗教、從較低狀態的意識到更高狀態的意識的記述,是對忠誠和承諾的敘述。
由於意識到自身的新穎性,次生宗教同時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強調性的宗教概念認識自身,原始宗教則沒有這種情況。原始宗教不把自己與其他事物區分開來,因此不需要將自己與“文化”分離,也不需要在文化內部進行“分區隔離”。次生宗教或反宗教培養了更高的意識水平,因為它們賴以生存的“真”與“假”之間的區隔必須不斷地在信徒的靈魂中重新劃定。次生宗教認識到自己作為宗教,不僅是與魔法、迷信、偶像崇拜和其他形式的“謬誤”宗教相對立,而且還與科學、藝術、政治和其他社會子系統相對立。因此,從原始宗教到次生宗教體驗的轉變也是一個提升意識的過程。在原始宗教體驗的視界中,那些未能覺察到自身的自主價值和規範的領域,現在都以其特定的輪廓凸顯出來,並迫使人們做出一個有意識的決定。“現在人們可以但也必須為新事物做出決定。僅僅遵循形式是不夠的,還需要內心的接受。信仰和門徒是當務之急,真理必須與謊言分開……現在有了‘真正的’和‘虛假的’宗教。”
正因如此,從原始宗教體驗到次生宗教體驗的轉變標誌著心靈和靈魂史上的突破。桑德梅爾在談到“內心的接受”時也暗示了這一點。真理和謊言的區分不僅僅劃分了外部空間,還切割了人類的心靈,心靈首次成為宗教動態演繹的舞台。回想一下《示瑪》禱告便足以說明這一點,它在上帝的獨一性與內心接受的強度之間,建立了一個不可能再更緊密的聯繫:
“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申命記》第 6 章 第 4 至 6 節)
反宗教與原罪的概念
伊曼紐爾·本·古里安(Emanuel bin Gorion,伯迪切夫斯基(Berdyczewski))在他編撰的《猶太傳說》(Die Sagen der Juden)序言中指出,這些傳說的核心特徵是“所有生靈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負罪感,並永遠不懈地努力贖罪。” 然而,當我推測“原罪”(sin)——或者也許應該說是:一個全新的“原罪”概念——是否隨著摩西的區隔而來到世界時,我並不是指古里安所討論的負罪感。古里安所討論的罪惡感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許多宗教,也許所有宗教,都存在著一個原始罪惡的概念,它導致了最初樂園般境況的失落,以及我們所熟知的世界——充滿著苦難、死亡、艱辛和勞役——的誕生。《聖經》提供了兩個這樣的原始罪惡神話: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和大洪水。大洪水的故事也可以在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和許多其他傳統中找到,而古埃及和其他非洲神話則講述了人類犯下的原罪導致了天與地、神明和凡人之間的分離。在這方面,《聖經》一神教與異教宗教沒有什麼不同。墮落和洪水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這種原罪的概念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也絕不是隨著一神教才第一次出現在世界上的。一神教引入的全新原罪概念與一個前所未有的忠誠誓言有關,這個誓言將超越並對立於世界的獨一神與他的子民(至少是那些相信他的人)緊密聯繫在一起。犯罪就是背叛這個誓言,違背信仰。
這種新形式的罪惡的原始場景並不在墮落和洪水中,而是在金牛犢之舞。通過這個行為,以色列人背叛了他們的神,並重新陷入了原始宗教。在走出埃及之後,“原始宗教”(現在被貼上“異教”的標籤)不再僅僅被視為謬誤,而且也被視為背叛和罪惡。真理與謊言之間的界限既具有認知意義,也具有道德意義。雖然虛假的神可能並不存在,但它們仍然代表著一種永存的誘惑源,潛伏著,用陷阱蠱惑人心。原罪伴隨著次生宗教體驗而產生,是對自己曾經缺乏忠誠、內心信念不夠堅定,以及屈服於虛假神的誘惑的覺悟。“原始宗教”體驗並不區分宗教和文化,它的特點是依靠樸素和幾乎是理所當然的證據。沒有人會考慮否認神聖力量的存在。它們以太陽和月亮、空氣和水、土地和火、死亡和生命、戰爭和和平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眼前。它們可以被忽視、不被尊崇、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冒犯,例如違反與它們相關的禁忌,但沒有人可以選擇主動與它們建立或終止關係。我們都生來就處於這種關係之中,因此它永遠無法成為內在抉擇(inner decision)的對象。然而,次生宗教體驗植根於一種無法看到也無法體驗到的啟示,只能“全心、全意、全力”地去相信。這種與感性世界的分離,正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智性上的進步”,它被認為是“次生宗教”體驗最根本的特點之一。
這種關於新的原罪的概念和意識的一個重要方面與一神教中神性和人性之間的關係的排他性有關。當獨一真神轉向世界時,除了信奉他、渴慕他的人類心靈之外,他找不到其他的伙伴,因為世界本身已經失去了所有的神性。換句話說,人類承擔了上帝對世界的全部回應,各種模式和隱喻描述了這種關係,例如新郎和新娘之間的愛的情關係、父親和兒子之間的特殊紐帶、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園丁和他的葡萄園,尤其是——但這不再是隱喻——統治者和他的盟友之間的關係。以前,人類從未對一個契約伙伴背負過如此沉重的責任。多神教的神靈通過相互的義務和盤根錯節的關係來實現他們與世界的對話。在一神教中,獨一真神第一次完全投入到人類及其愛和忠誠的能力。這種轉變在人類一邊的對應物是一種全新的無能感。一神教的神的獨特性和唯一性也意味著孤立和孤獨。埃及文本強調了這一點,他們不僅稱神為“獨一的那一位”,也稱他為“孤獨的那一位”,正如亞比修斯(Iamblichus)抄錄的這個警句:“獨自一人在他的獨一性之中逗留。”首先,那是創世之前或世界誕生之前的原始神,然後,是在被創造或誕生的世界之中的創造神和太陽神,因為他不僅可以被認為存在於世界之中,而且還可以被認為是站在世界之外。然而,這位神既然沒有與人訂立盟約,他只能通過在神聖世界的多種不同形態中顯現自己,才能在世界中被體驗到。因此,《聖經》中的神的——即使在與世界對話的形式中亦是如此——更加顯得是寂寞和孤獨的。因而,他依賴於人類的愛和忠誠。托馬斯·曼(Thomas Mann)在他的《約瑟夫》四部曲中,將上帝的孤立與他的嫉妒盡可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是的,上帝,主,在他的偉大之中也是孤獨的;約瑟夫的血液和他的記憶表達了這樣一個認識,即無妻無子的上帝的孤立與他和人類建立的紐帶背後的嫉妒有很大關係。”
一神教特有的原罪概念的另一個方面是偶像崇拜,即屈服於崇拜虛假神靈的誘惑。很顯然,摒棄虛假神靈的戒命在人類的靈魂中遭遇了最頑強的抵抗。這種抵制的主題在《聖經》中反覆出現。對於人類來說,遠離被宣稱為假神的神靈並非易事。因為這些神靈擁有自然證據的優勢和吸引力,而這正是啟示真理所缺乏的。這個世界的神靈頑強地捍衛著這個被一神教徹底祛魅了的世界的神性。《聖經》經文充滿了這種抵制。
我提出的這個觀點受到了批評者的嚴厲批判,即:摩西區隔的出現帶來了一種新的罪惡觀念,與之相伴的是一種新的負罪感。格哈德·凱澤更是認為我描繪一神教時使用的“陰鬱色調”(somber tones)冒犯到了他。然而,這些“陰鬱色調”是一神論宗教調色板上的基本色調。順便說一下,我並不是在聲稱“原罪和內疚感本身是摩西區隔導致的世界分裂造成的”,我只是認為,隨著這種區隔以及它所引發的意識史上的轉變,一種全新的罪惡意識和概念出現了。這一說法並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在我看來,一種精緻而深化的罪惡意識的發展代表了一個文明的高峰,《聖經》中的這一進步,相當於古希臘悲劇的誕生。原罪的發明是“智性進步”的一部分,因為“首先要理解了原罪,才會犯下原罪;是的,從根本上講,所有的精神主旨都不外乎對是與非的理解。”
結論
拙著《埃及人摩西》一書的德文版以這樣一句話結尾:“誰在埃及發現上帝,誰就能夠消弭這種區隔”,如果讀者由此誤以為我在埃及發現了上帝並夢想著消除摩西區隔,我並不會覺得被冒犯。坦白地說,我並沒有在埃及發現上帝;事實上,我對宗教史上那些熟為人知的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並不十分看重。我也無意廢除摩西區隔。我在這句話中想表達的是,所有將摩西塑造成埃及人並聲稱在“埃及發現了上帝”的人,從斯賓塞到席勒(一直到弗洛伊德,儘管我今天不再堅持這一譜系),都在試圖廢除摩西區隔。我的關注點在於關於摩西的爭論的記憶歷史邏輯:誰在講述故事,它是如何被講述的,其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意圖?
當我在《埃及人摩西》一書中重新審視這段故事時,自然也會捫心自問,為什麼我這樣一個非猶太人、基督徒、德國人、埃及學家會對這個主題如此著迷。毋庸置疑,我這一代的德國人對反閃族主義問題格外關注,而作為一個埃及學家,我長期以來一直沉醉於探究古埃及的記憶滲透到西方自我形象和文化記憶基礎的程度。摩西的神話——如果我可以這樣稱呼這個故事,一旦剝離其不可否認但又難以捉摸的歷史內核,成為純粹的記憶形象——也召喚著埃及學家登場,不僅僅是因為——如弗洛伊德認為的那樣——《聖經》塗改和歪曲了一個準確的埃及歷史記載,還因為這裡加密了一個特定的埃及形象。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一神教在《出埃及記》中通過與埃及的區別來定義自身。為了到達一神教的應許之地,必須拋棄埃及。我不排除這個版本的事件在歷史意義上可能是真實的;無論如何,它在象徵意義上是真實的,我必須承認,比起可能的歷史真實性——即一群希伯來遊牧民或客籍工人真的在一位名叫摩西的埃及人的領導下走出埃及——我覺得象徵性的真實更有趣。
至於一神教的心理歷史後果,重要的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它是如何被記住的,以及為什麼被認為值得講述。在這方面,我同意弗洛伊德的觀點,他認為摩西的名字是埃及人的,敘述強調摩西在埃及宮廷被作為王子撫養,並且“摩西在埃及享有極大的權威”,因此,當他回到他的人民那裡時,他不得不改變他的身份。一神教要求改宗,首先是個人層面,然後是集體層面。當上帝說“我已將我的兒子從埃及召出來”時,“埃及”不僅僅指一個地理空間,也指一個自成一體的精神世界。埃及象徵著人類與世界和上帝之間的一種普遍的聯繫,包括與之相關的“靈性”,人們必須從中撤離,或者如《聖經》所說,“被拯救出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即漸進演化的意義上,永遠不會進步到一神教。一神教要求遷移、劃界、改宗、革命,其對舊事物的激進的斷裂、放棄和否定,導致了對新事物同樣激進的嚮往。
因此,一神教的決定性時刻是改宗的情境。受困於異教偶像崇拜的希伯來人被摩西轉變為一神教信徒,保羅使猶太人和外邦人皈依基督教,穆罕默德使猶太人、基督徒和無信仰者皈依伊斯蘭教;在所有這些改宗的情境下,摩西關於真假之間的區隔被重新引入並強化。摩西的區隔必須被不斷地重新劃定。毫無疑問,正如卡爾-約瑟夫·庫歇爾所指出的,納粹德國屬於“歷史上令‘摩西區隔’變得至關重要的危機局勢之一”。面對這種暴政,無論是弗洛伊德還是托馬斯·曼都將一神教解釋為“智性的進步”,儘管他們是以人性中不可磨滅的基石為參照,而不是任何神的啟示。我完全同意庫歇爾的觀點,即“災難的經歷迫使人們接受摩西的區隔”。 對於海因里希·海涅來說,就像對弗洛伊德和托馬斯·曼一樣,災難同樣迫使他接受了這一點。
摩西神話劃定了一條界線,並作了明確的區隔: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間、在過往與世界的關係和未來與世界的關係之間、在其他神靈和獨一真神之間、宗教中的真理與謬誤之間,最終是在神和世界之間。這種區隔連同其心理歷史後果,烙印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信徒的靈魂上。在我看來,一個宗教是否除了唯一真神之外還崇拜天使和聖徒完全無關緊要,即便基督教中聖子聖靈的概念也無法使其成為多神教。更重要的是,這條界線外存在著其他神靈、假神、偶像、迷信、魔法、異端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宗教的“非真理”。無論這條界線劃在哪裡,我們所面對的都是新宗教及其心理歷史影響。毋庸置疑,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像猶太教一樣劃定這個界線。唯一的區別在於,猶太教是劃定界線來隔離自己,而其他一神論則為排除他人劃界。通過崇拜唯一真神,猶太人使自己與那些對他們無足輕重的民族隔離開來。他們通過嚴格遵守律法,來培養一種能夠象徵性地表達這種自願的孤立的生活方式。基督教認為自身的使命是結束這種自我強加的孤立並向所有人敞開大門。現在,所有拒絕接受這一邀請的人和事物都被遭到排擠。因此,一神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具有侵略性,有時甚至會變得咄咄逼人。伊斯蘭教同樣如此,它在政治層面重新定義了這條界線,不僅區隔了真與假,還區隔了宗教中的臣服和戰爭(伊斯蘭國和征戰國)。在每一種情況下,一神教都通過以其排除的異教徒作為參照來定義自身。
我相信我在埃及發現了一神教被壓抑和遺忘的一面,可以說是它黑暗的一面,它充其量只作為一種否定和否認的對象存在於西方文化記憶中。這個被壓抑的黑暗面不斷回來困擾著西方,從它每次回歸時帶有的爆發力可以推斷出,我們在這裡確實是在面對一個經典(即弗洛伊德式)意義上的“壓抑”案例:在上古神學中、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爾墨斯主義中、在自然宗教、斯賓諾莎主義、啟蒙運動和早期浪漫主義時期的的泛神論的思想中、以及在各種新宇宙主義思想中——包括從慕尼黑宇宙主義者(Munich cosmicists)到“希特勒之神”(Hitler’s god),威卡教(Wicca)和其他新世紀(New Age)宗教潮流。
因此,我正在努力進行一項回憶的工作,將被壓抑的東西揭示出來,以便之後對其加工或——借用弗洛伊德的說法——“升華”。我想要升華摩西的區隔,而不是廢除它。儘管卡爾-約瑟夫·庫歇爾持反對意見,但我仍然堅信,我們不能再依賴“絕對”的真理,只能依賴相對的、務實的真理,這些真理需要不斷重新協商。正如弗洛伊德教導我們的,摩西的區隔不僅代表著創傷、壓抑和神經症,也代表著“智性的進步”,無論它的代價多麼高昂,我們都不應該放棄它。如果我們想要保持信念的力量和深度,我們就需要堅守真假之間的區分,以澄清我們所認為與這些信念無法調和的觀念。但我們再也不能夠將這種區隔建立在一勞永逸的神啟之上。因此,如果我們要使摩西區隔成為人類進步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們就必須不斷地反思和重新定義它,將其置於“話語的液化”(discursive fluidification,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過程之中。
譯者註
第一章
- “sin’ah”,其發音接近“西奈”。
- 此處原文是“theoclasm”,這是一個含義非常寬泛的詞匯,它的本意是“擾亂和質疑既有的關於神的認知、信仰和實踐”,姑且可以譯為“神學反現實或反傳統主義”,但根據本書整體上下文,作者的意圖是指對偶像崇拜的否定。
第二章
- 這兩者通常被學者解讀為亞威的配偶。
- 原意是:那種其緣由並非顯而易見的戒律。
- 天主教稱《德訓篇》。
第三章
- “Amenophis”,這個名字的近代英文拼寫和希臘化時期的拼寫與阿蒙霍特普相同,但他是一個官員,深受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賞識與愛戴。
- 這是一個雙關語,也可表示“基督化不徹底”。
- Aleida Assmann,作者之妻。
- Moses ben Maimon,即邁蒙尼德。
第四章
- 此處原文刻意略過了連接主語和賓語之間的謂語,它應該是一個 be 動詞的主格複數形式:are。譯文保持了原文這種文法殘缺的方式。
- 語出《哥林多後書》第 3 章,第 6 節。
- 指原始弒父。
譯後記
“誓反教” vs. “新教”
參見我的文章《經過五年的研究,我目前對基督教的看法是什麼?》中的“定義與範疇”一節。
“亞威” vs. “耶和華”
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聖經》中的這個上帝其實有很多名號。《舊約》——更準確地講,《希伯來聖經》——是我們能夠考據的最早文本,雖然《希伯來聖經》中的上帝也以若干不同的名字出現,但是最主要的是兩個:“Yahweh”和“Elohim”,其中“Yahweh”出現的次數明顯更多,關於這兩者的使用引發的研究,我不在此深入討論,總之,“Yahweh”被後世當作上帝的正式名號。
《希伯來聖經》最早的版本是用公元前幾個世紀的古希伯來文書寫,當時的希伯來文只有輔音字母,而沒有辦法表達元音,反映那個時期的手稿使用希伯來文“יהוה”表達上帝的名字,古代的猶太人認為這個名字太過神聖,為了避諱,使用“Adonai”(אֲדֹנָי)來替代它,發音接近於“阿多奈”,含義則接近於“(我的)主”。古代的《希伯來聖經》被翻譯成希臘文——即《七十士譯文》——的時候,當時的翻譯者很多也採用了這個做法,用希臘詞彙“Κύριος”(Kyrios)來替換“יהוה”,它的含義就是“(我的)主”。除此之外,希臘文譯本在接下去的幾個世紀的傳抄和重新翻譯過程中其實也出現過非常不同的其他音譯,這裡略去不詳細討論,在 researchgate.com 上面有一篇題為《Transmission of The Tetragrammaton in Judeo-Greek and Christian Sources》的文章詳細討論了希臘譯文中出現過的所有翻譯方式,其中有的很荒唐。拉丁文譯文的情況也與希臘文譯文相似,多數以“Dominus”代替,意思是“主人”,但同時也出現過非常多其他音譯。
古希伯來文的名字“יהוה”在英文字母化之後是“YHWH”,它在學術界有個專有名詞,叫 Tetragram(四字神名)。希伯來文後來逐漸進化,發展出表示元音的擴展符號,所以它現在可以被寫成“יְהוָה”,但是從 12 世紀到 19 世紀,由於對古老《希伯來聖經》文本的發現和對上帝名字的原始發音的執著,很多歐洲人都嘗試用自己的語言重新翻譯這個名字,於是它的音譯變種層出不窮(維基百科的詞條頁面羅列了一部分),到了 16 和 17 世紀,宗教大改革期間,英國人終於也參與進來,他們使用最多的兩種音譯是“Jehovah”和“Iehovah”,而中文的譯本(比如《和合本》),則根據“Jehovah”的發音將上帝的名字譯作“耶和華”。
到了今天,學術界對於《聖經》的歷史和希伯來文自身的歷史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對於現代希伯來文“יְהוָה”的正式英文譯法是“Yahweh”,可是由於古希伯來文沒有元音,關於它最初如何發音的信息沒有被流傳下來,今天有學者認為它的發音應該是“亞威”,有的則認為是“亞乎威”,前者明顯更主流。
我有注意到李展開先生在他的《摩西與一神教》的中文譯本中,使用的是“耶和華”。我所留意到的是,弗洛伊德這本著作的英文譯本使用的是“Jahve”而不是“Jehovah”,因為弗洛伊德在他的德文原版中使用的就是“Jahve”,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在德語中,“J”字母的讀音是“y”,接近於“耶”,這不同於英語,在英文中“J”的發音接近於“揭”。另外,我還注意到,在以英文為主的學術界裡,基本上討論這個話題的文本如果延伸到了《舊約》/猶太教——即《希伯來聖經》——那麼就不會使用“Jehovah”,而是一律使用“Yahweh”,即便討論的範疇僅僅局限於基督教,對“Jehovah”的使用也非常少見,因為,說到底,“Jehovah”是一種誤傳和誤譯的中間產物,而且對它的使用也表示了對於這個名字自身的發展歷史的無知或漠不關心——而這兩種情況在學術領域都無法被接受。似乎“Jehovah”的使用者主要是基督徒群體,範圍也限於宗教話語內,最典型的例子是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由於以上種種我在英文學術圈中觀察到的現象,我決定沿用他們的慣例,將上帝的名字翻譯為“亞威”,而不是“耶和華”。
“智性的進步” vs. “靈性的進步”
這個概念源自弗洛伊德的著作《摩西與一神教》,其德語原文是“Der Fortschritt in der Geistigkeit”,它出現在德文版的第 197 頁,正如阿斯曼在這本書中說的,弗洛伊德還用它來做一個小節的標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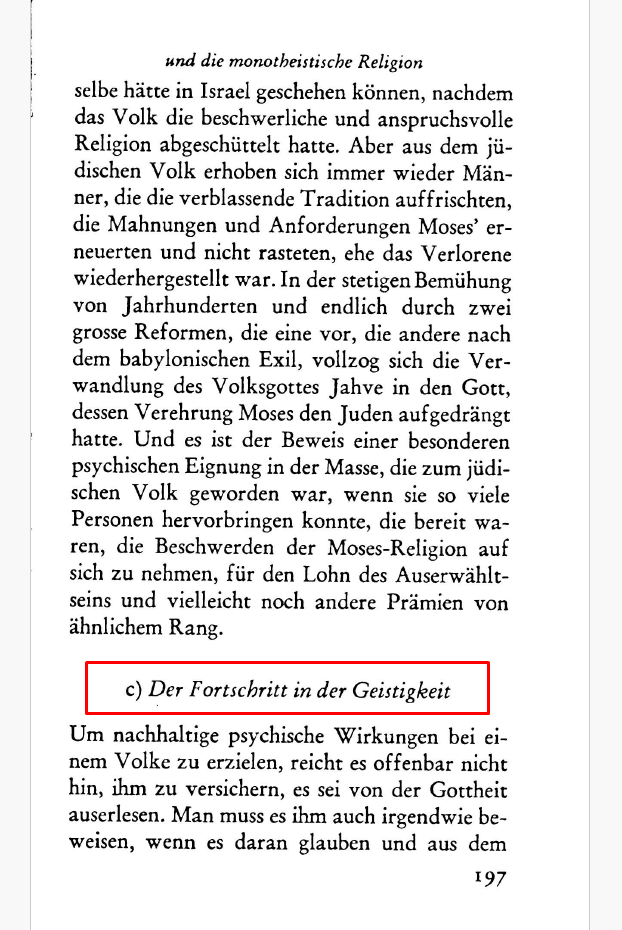
在阿斯曼提到的一本著作——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弗洛伊德和摩西的遺產》(Freud and the Legacy of Moses)——中,伯恩斯坦也詳細討論了這個概念,他首先指出,這個德語詞彙無法翻譯成英文,因為在英語中並沒有與之含義相等的詞彙,他還指出詹姆斯·斯特拉奇(James Strachey)在他的英文譯本中將其翻譯成“The Advance in Intellectuality”(智性的前進),而凱瑟琳·瓊斯(Katherine Jones)譯作“The Progress in Spirituality”(靈性的進程)。我所依據的英文版所使用的是“Progress in Intellectuality”(智性的進程)。李展開先生在他的中文譯本中譯作“靈性的進步”。
這個短語的其他部分沒有太多出入,接下來,伯恩斯坦深入解析了德文詞彙“Geistigkeit”,他說,英文“intellectuality”(知性,智慧)和“intellectual”(理性的)都無法傳達“Geist”這個詞根原本的力量(power)與活力(dynamic quality),而“spirituality”(靈性,精神性)又無法表達出“Geist”所蘊含的智慧和理性的層面,甚至往往被當作與理智相對的概念來使用。簡單地說,弗洛伊德用“Geist”表達了一種人類認知中結合理性智慧與靈性的能力,而在英文中沒有能同樣精準又貼切地表達這種能力的詞彙。
伯恩斯坦又繼續引用了弗洛伊德自己對於“Geist”這個詞的起源的詞源解釋,他認為“智慧”這個概念,同“心靈”,“靈魂”概念一樣,源自人吸入和呼出氣體的現象,或許他是想借用一種比喻修辭的效果來說明,“Geist”所表達的智慧是一種不借助感官但卻能帶來不可置疑且絕對有效的知識的一種認知能力。弗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始終在用這種認知能力與感官知覺和本能做對比,但是,當然,智慧與靈性,兩者都與感官知覺和本能截然不同,而這兩者本身又在另一個維度上也相互對立。
在這個問題上,英文的表達力不及德文,而中文的又不及英文,所以即便作了上面的分析和澄清,我們依然束手無策。不過,終究我的翻譯所依據的英文使用的是“Progress in Intellectuality”,而且還被用來與“Spirituality”相對立,比如在英文版第 102 頁中有這樣一句話:
In his eyes, (Jewish) intellectuality and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re two entirely different things.
綜上所述,我將這個短語翻譯成“智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