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里克·多兹(Eric Robertson Dodds)
译者:北公爵
版本: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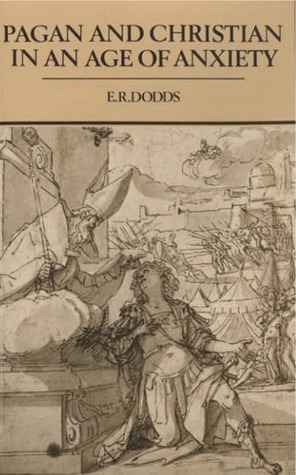
译者序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中对西方文化的两个习俗的起源做了一番历史考据。第一个习俗是,当有人打喷嚏时,他/她周围的人会说“God bless you”,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的教导令人们普遍相信,在一个人打喷嚏的瞬间,他/她的灵魂会出离身体,而人类世界充满了恶灵与魔鬼,他们潜伏在人周围,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占据人的身体。这个时候呼唤上帝之名就可以吓退这些魔鬼。另一个习俗是基督徒在餐前的祷告,这个做法的最初原因也相似,是为了阻止魔鬼附着在食物上面,通过人类进食进入到人的身体。
我目前尚未遇见过对这两个现象的神学起源有了解的基督徒,虽然,按说这是源自他们自己的信仰体系,他们理应有所了解。当然,我仅仅以我个人有限的经历来做此踹度,所以或许这个结论未必准确,但是,至少我的直观感受是,基督教的传承是有筛选性的,这并不仅仅是流于表面的文化现象或者仅仅一个教习——宗教的外在形式——那么简单,即便是一些基督教的内在核心,比如信条或教义的内容,也会被时间所淘汰。
基督教,像大多数宗教一样,将权威性建立在“神启”这个观念之上,上帝向教父们显灵,直接将信息传达给他们(这其中的细节却从来没有被描述,上帝是以一个外在的声音对他们讲话,还是用通灵或降头的方式到他们身上用他们自己的喉咙对他们讲话,还是甚至直接进入到他们的意识里完全跳过生理感官,或者还有其他超越我们想象力的可能,这些都不得而知),而他们再将这些信息以人类语言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神启”。而且,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超越的、至高的存在。于是,在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之上,基督徒可以自信地宣布他们信仰的教义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它直接源自最高的神。
基于上述这两个核心论点,我们可以对基督教的真理传承做一些合理的设想:
- 上帝传达给基督徒的真理应该是至少不会自相矛盾的;
- 上帝传达给基督徒的真理应该是至少会与客观事实相兼容的;
- 上帝传达给基督徒的真理应该是绝对清晰的,它不该受解读的影响;
- 上帝传达给基督徒的真理应该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它应该在任何时代背景,任何文化背景与任何社会背景下都适用;
- 上帝传达给基督徒的真理应该是不具有历史性的,即:它应该直接以今天的模样,出现在一个历史瞬间(甚至应该是在没有历史上下文的情况下),而且在接下去的时间长河里保持静态。
但是,我们看到的客观事实却不是如此。前面两点涉及长篇大论,我暂且略过。关于第三点,反面证据源自基督教内部的派系分裂和相互的攻击,这种分歧的一个源头就是对经文解读的不同,所以我没有见到基督徒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发展出很成熟的话术去化解。关于第四点,基督徒的回应是:因为2000年前的人类还没有足够的智慧,所以只能用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的方式说给人类,这个话术很容易推翻,它不是我现在想讨论的话题。第五点才是我这次想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考查历史的过程中,清晰地探查到了一个神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即:一个观念从粗糙和原始的雏形,逐渐随着时间被调整和修改(尤其是如何在周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被改变),演变成今天的复杂理论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那么这对基督徒而言,将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为了躲避这种尴尬,基督教教会向来厌恶历史研究(当然,我指的是对真实历史的研究),而教会体制内的护教学投入资源最多的活动,就是重写历史,在重写的过程中抹去神学观念这种“演化”的痕迹,是其诸多目标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从今天的基督教话术中,我们总是得到这样的印象:某个神学理念是在历史真空中一下子就蹦出来的,它在历史中出现时的状态就和今天的样貌一样,它在2000年的传承中是保持不变的。牧师向非信徒传道时不会像大学课程那样设计,在第一讲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介绍某个观念的正方和反方。
如果翻开真实的历史,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首先,基督教教义的传承并不具有连贯性,相反,它是离散的、非常跳跃的,是有断层的,很多理念出于政治或者认知原因被抛弃,而且一旦被抛弃,它们便要被深埋和掩盖;其次,当我们回到某个历史中的时间点,在这个点上截取它的全景时,则只会在这个截面上看到一幅支离破碎的图景,那些被后世追封为圣人的早期教父们,大多数都或多或少持有在今天是“异端”的想法,但是当他们被引用时,这些内在矛盾都会被巧妙地遮掩。
近代以来,有许多历史著作都揭示了基督教的这种内在的不一致性,和神学理念的历史性,这本著作便是其中之一,它所呈现的,是早期基督教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内,它的光怪陆离的面貌,以及它是如何在与异教哲学的互动中借鉴对方的,其中的很多神学理念和修行实践,甚至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现代基督教的话语体系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描述:在基督教初期,基督徒们借用了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和解释基督教的教义,言外之意是,这些被借用其他术语解释和阐明的理念本身是属于基督教自己的,但是,对于历史的研究推翻了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它纯粹是一种话术而已,更为客观的说法是,基督教从希腊哲学那里直接抄袭了基督教本来并没有的东西,而不是表达他们本来有的东西。而且,在基督教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借鉴”的极致状态——作为借鉴者,不仅可以鹊巢鸠占,声称自己拥有原创权,甚至还可以反戈一击,声称被借鉴者反而是在借鉴自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类古希腊哲学家只是基督之前的基督徒”。
我们还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描述:基督教是一股势不可挡的真理洪流,在它的冲刷下,各种各样的文化被塑造,尤其令基督徒们引以为傲的,是在西方被它造就的现代的文明政治,然而,对于历史的仔细考证也不支持这种说法,恰恰相反,基督教一直在被它自身以外的一股力量塑造着,每个时代它都会为了生存改变自己的面貌。所以,基督教的话语体系最大的敌人,是历史化的解构。
如果读者有翻译上的建议,我非常欢迎讨论,此博客有我的邮箱地址。
我可以预见到,某一天我的这个翻译文本会被其他华人抄袭,但是我还是要在此强调:谢绝转载。
目录
第一章:人与物质的世界
第二章:人与亚神的世界
第三章:人与神明的世界
第四章:异教与基督教的对话
原文注释
第一章: 人与物质的世界
人类唯一能确认的知识,就是生命的荒诞性和无意义。
怀尔斯信托基金会(Wiles Trust)资助了本书的撰写,该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文明史的研究,并鼓励将历史性的思维普及到各思想领域”。那么,本系列讲座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也许引用两位杰出的古代历史学家的评说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中,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考察并评判了人们用来解释罗马帝国衰落的不同理论,其中有的是政治学方面的,有的是经济学方面的,有的是生物学方面的,但在最后一章,他最终转向了心理学解释。他认为,人们的世界观的转变“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他还补充说,进一步研究这种转变是“古代史领域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我的第二个引述来自尼尔森(Martin Nilsson)教授的《希腊宗教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的最后一章。他写道:“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晚期古典时期宗教融合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仰和教义上,而这些信仰和教义赖以生长和汲取养分的精神土壤,则只是被顺带和粗略地提及;然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是最重要的部分。”他接着指出,我们已经有充足的材料可用于研究晚期古典时期的——按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定义的——宗教体验。
我希望这两段引文足以解释我将要在这些讲座中做的尝试。要全面性地解释精神面貌的转变及其与物质层面的衰退之间的关系,将是一项远远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任务;但是,在尼尔森教授所指出的特定领域内,我将尽力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会解释其发生的原因。这些讲座的主题是詹姆斯所定义的宗教体验。如果我触及异教哲学理论或基督教教条的发展,那也只是为了给个体的宗教体验提供背景。我完全不会涉及崇拜的外在形式。例如,我不会讨论所谓的“神秘宗教”及其对基督教仪式的所谓影响,因为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同我现在探讨的主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除了基督教教父们有争议的说辞外,有关神秘宗教的主要证据来自铭文,而铭文很少能提供深层的个人体验的信息。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阿普列尤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最后一卷中关于伊西斯密教(Isiac)的入教仪式的著名描述;但诺克(Nock)、费斯图日勒(Festugiere)和其他学者对此已经详细讨论过,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即使做了这些限制,罗斯托夫采夫和尼尔森提出的主题仍然太宏大了。即便我有能力完整地讲述一个从斐罗(Philo)和圣保罗开始,到奥古斯丁(Augustine)和波爱修斯(Boethius)结束的故事,也根本无法在四次讲座中完成。因此,我认为最好将注意力集中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即位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之间的关键时期,这是物质生活衰退最为严重、新宗教情感发酵最为激烈的时期。我称之为“焦虑的时代”,意思是指当时在物质和道德两方面的不安全感;这个短语是由我的朋友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创造的,他用它来描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想这也有双重指涉的意味。将历史分割成方便的长度并称之为“时期”或“时代”的做法当然有其缺点。严格来说,历史中没有时期,只有历史学家所谓的时期;真实的历史是一个顺畅流动的连续体,日复一日。即使后见之明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关键点上将其斩断,也总是存在时间滞后和重叠。当马可·奥勒留登基时,没有钟声响起警告世界:罗马的和平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蛮族的入侵、血腥的内战、接踵而至的瘟疫、急剧的通货膨胀和极度的个人不安全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必定继续以他们一直以来的方式思考和感受;对新形势的适应只能是渐进的。更令人惊讶的是,相反类型的时间滞后也会发生:即不安全感会在道德和思想层面先发生,而后才是物质生活层面。荣格在某处评论说,“早在1933年之前,空气中就已经有一丝灼烧的气味了”。同样,我们可以在《论崇高》(On the Sublime)的最后一章,在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某些段落中,以及,最明显的是在诺斯底主义中,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先兆,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巴西利德(Basilides)、瓦伦丁(Valentinus)和(如果我们把他算作诺斯底主义者的话)马吉安(Marcion)——在安敦尼(Antoninus)盛世中的繁荣时期构建了他们的体系。出于这些原因,在证据需要时,我会对我的年代界线进行一些弹性处理。
在我结束这些序言之前,还需要坦白一件事。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其自身宗教信仰的影响。因此,我应该公开我的立场,以便读者可以做出适当的权衡。事实上,这个话题对于我所持的立场并无利害。基督徒将基督教的胜利视为上帝干预的结果,并且认为这是他在创世之时就已经预设的方向,但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我无法认同这种观点。但同样地,我也无法认同普罗克洛所称的“野蛮的神学”抹杀了希腊文化的阳光。如果在这些讲座中,我谈论异教徒多于基督徒,那并不是因为我更喜欢他们;仅仅是因为我更了解他们。我置身这场特殊的争斗之外,尽管没有凌驾于其上:我对令双方产生分歧的的那些议题兴趣较少,而更关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态度和经历。
在这第一章中,我将讨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处境的总体态度;在第二和第三章中,我将讨论一些特定类型的体验。约瑟夫·比德兹(Joseph Bidez)将我们所讨论的时代描述为“人们不再观察外部世界,也不再试图理解、利用或改善它。他们被驱赶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天空和世界之美的理念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对无限的向往。”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弗洛伊德将其与“基督教教义对尘世生活的贬低”联系起来,真的是如他所说吗?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晚期古代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家那里继承的关于宇宙结构的观念。地球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球体,位于一系列同心运动球体的中心。最中心的球体是厚重而昏暗的地面大气层,一直延伸到月球;月球之外是太阳和五个行星分别所在的连续球层;再往外是第八层球体,由最纯净的物质元素——火热的以太构成,它每日围绕着地球旋转,并带动固定于其中的星辰。这整个庞大的结构被视为神圣秩序的体现;因此,它被认为是美丽的,值得崇拜的;而且因为它是自行运动的,所以被认为是有生命的,或者被一种活着的精神所充溢。因此,除了伊壁鸠鲁学派之外,这个宇宙观是所有哲学流派的共同基础,对于大多数受过希腊传统教育的人来说,在他们的时期及其之后,它仍然是共识。但是,虽然人们相信这个宇宙的各个部分通过“共感”(sympatheia)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无意识的生命共同体,但各部分的地位和价值却并不均等。亚里士多德遵循柏拉图的启示,在这幅宇宙图景中画了一条后来被普遍接受的界线:在它之上,月球以外,是不变的天界,在那里,斗转星移,“等级森严,一切遵循着不可变更的法则运转”;在它之下,月球以内的世界,是变数、无常和死亡的领域。在这个闪耀夺目的具有多层结构的栖居之地中,地球似乎是最卑微的那一层:它被认为是由宇宙的渣滓和沉淀物构成,那些冰冷、沉重、不纯的物质,它们的重量使它们沉到了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将天上与地下对立起来的传统越发被强化,并且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论证道德。在反复出现的灵魂穿越宇宙——它被想象为在梦中、在死后、或有时仅仅在清醒的沉思中发生——的主题中,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对于月球以下的世界里可以发生的一切可做和可受之事的日益增长的轻蔑态度。天文学家已经注意到,在空间上讲,与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微不足道:在整个宇宙的图景之中,它只不过是一个针尖大小般的点,一个“στιγμή”【希腊语:细微的点】或“punctum”【拉丁语:细微的点】。道德说教者们很早就将这一观察作为其说辞,来论述人类愿望的虚妄:它出现在西塞罗(Cicero)的作品中、塞内卡(Seneca)的作品中、伪亚里士多德的《论宇宙》(De mundo)中,以及琉善(Lucian)的一部戏仿太空旅行的作品《梅尼普斯的飞天之旅》(Icaromenippus)中。这也许不过是一种文学手法;所有这些作者可能都在抄袭一个现已失传的希腊的文学模型。但真正将这一思想化为己有的作家是马可·奥勒留,他将其从太空旅行的主题中分离出来,并以前所未有的强度从多方面使用它。正如地球是无限空间中的一个针尖,人类的生命也是无限时间中的一个刹那,是两个永恒之间的一线之隔——στιγμὴ τοῦ αἰῶνος【希腊语:时间中的一瞬】。他做什么都是“飘渺与虚无”的;而他的回报就像是“一只飞过的鸟,还未等抓住便消失了”。军队之间的战斗是“小狗为了一根骨头而互搏”;就连马可他本人的萨尔马提亚凯旋的浮华也只不过是一只捕获到了苍蝇的蜘蛛的自满。对马可来说,这不是空洞的修辞:这是他对人类处境的看法,而且是极其真诚的看法。
在马可·奥勒留的思想中,与之相关的是:人类的活动不仅不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完全真实的。另一个古老的主题表达了这种感觉——将世界比作舞台,人则比作演员或木偶。这种比喻如今已是老生常谈。它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法律篇》中的两段话,其中说到“男人和女人主要是木偶,只有很少一部分真实性”;至于神是将他们设计成纯粹的玩物,还是为了某些更严肃的目的,则仍然存疑。在柏拉图之后,早期的犬儒派和怀疑论者利用了这个意象:对于彼翁(Bion of Borysthenes)来说,“机遇”(τύχη)才是这出戏的创作者;对于阿那克萨图斯(Anaxarchus)和摩尼穆斯(Monimus)来说,我们所谓的现实不过是一个舞台布景,我们对它的体验不过是一场梦或幻觉。从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以来的斯多葛派则更倾向于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种比喻,用它来论证一种平庸是福的道德观念:即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构成一个世界,或者像塞内卡和爱比克泰德强调的那样:即使是很微不足道的角色也应该尽力而为。只有在马可·奥勒留那里,对虚幻感的暗示才再次出现,例如,他记下了一系列人类生活的景象,从“舞台剧和空洞的游行排场”到“提线木偶的抽搐”;中间还有花拳绣腿的搏斗、有向小狗扔骨头或向鱼扔面包屑、有蚂蚁枉然的勤恳和惊慌失措的老鼠徒劳的逃窜。在其他地方,他把整个感官生活称为“一场梦和一种谵妄”。
这同样的感受也贯穿了普罗提诺(Plotinus)晚年的一段长篇精彩论述,他借鉴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将人生的荣辱悲欢诠释为一场舞台剧。对他来说,就像对年迈的柏拉图一样,人的真挚只是神的一出戏剧,由“美丽可爱的活体木偶”在世界剧场中演出——这些木偶错把自己当成人,因此遭受苦难,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内在自我——唯一真正存在、真正实在的人——的外在影子。这些都与普罗提诺的基本观点相契合:即行动处处都是“沉思的影子,是其拙劣的替代品”。当城市被洗劫、男人被屠杀、女人被强奸时,这不过是一场永无尽头的戏剧中的短暂一幕:总有一天更好的城市会被建立,在罪恶中孕育的孩子可能会成长为比他们的父辈更善良的人。这似乎是他对他那个时代悲惨历史的最终结语。
从普罗提诺开始,这种顺应之中又带有厌弃的复杂态度被传给了后来的新柏拉图学派,无论是基督教中的还是异教中的。例如,对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来说,人间之事不过是孩子们建造沙堡的游戏,很快这些沙堡就会被冲走;正如达尼埃鲁神父(Father Daniélou)所说,他的整个作品都充斥着对感官世界虚幻性的深刻感受,他称之为“γοητεία”【希腊语:魅力,魔力】,一种魔幻般的幻觉,这正呼应了波菲利(Porphyry)的表述。
而奥古斯丁则宣称,“这一生不过是人类的一场幽默剧”。从他和波爱修斯开始,这个意象传入了后来的道德说教者和诗人的素材库中,恩斯特·柯提斯(Ernst Curtius)研究过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但即使在古代,这种态度也并非仅限于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剥去所有形而上学的外衣,异教诗人帕拉达斯(Palladas)的一首著名讽刺短诗生动地表达了这种态度:
世界如舞台,人生似玩偶;
粉墨登场,扮好你的角色;
抛下所有严肃的思考——
否则你只会肝肠寸断。
马可·奥勒留、普罗提诺和帕拉达斯都是在希腊传统的熏陶中长大成人的,他们的思考和情感都受到这一传统的限制。他们能够认同柏拉图的观点,即这个月球以下的世界“必然被邪恶所困扰”,并且能够感受到人类在其中的活动是一种无关紧要、无足轻重也不那么真实的存在,实际上是“荒谬的”(就像加缪所定义的那样)。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斯多葛学派或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也没有任何一个正统的柏拉图主义者会谴责整个宇宙。当我们遇到这种谴责时,我们就得怀疑它最终源于更为东方的某个地方,源自一种比柏拉图更激进的二元论。只有与在宇宙之外和超越宇宙的某个不可触及的完美之所或完美之人相对比时,我们才能说整个可见的宇宙是邪恶的,所以,激进的二元论意味着超越。斯多葛主义不承认这样的地方或人物,它是一个单层体系。
柏拉图主义当然承认;但对于正统的柏拉图主义来说,可感知的宇宙与理念世界之间是一种依赖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正如《蒂迈欧篇》所言,“它是可理解的世界的形象,一个可感知的神,在伟大、卓越、美丽和完美方面无人能及,独一无二”。当我们发现可感知的宇宙与神相互对立时,这种对立性可以用以下三个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全部来解释:(1)物质,或者“黑暗”,并非是由神所创造的,并且它抵抗神的意志;(2)命运,其代理人是行星恶魔,即七道门的守护者,他们将世界与神分隔开;或者,(3)最后的理论认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神,本身是邪恶的,在某些版本中他是世界的创造者。所有这些观念都以各种组合出现在基督教诺斯底主义中;其中一些被正统基督徒持有;但它们在异教徒中也广泛流行。而且,有证据证明,所有这些观念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不能将它们仅仅视为焦虑时代的副产品。
将物质视为独立自主的存在和邪恶的源头的观念,既有希腊的根源,也有东方的根源。希腊哲学史家们将其归功于毕达哥拉斯,而且在柏拉图的某些段落中也可以找到这种观点的依据;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努米尼乌斯(Numenius)是最坚定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早期诺斯底教派的巴西利德称其为野蛮人(即波斯人)的智慧。与其他两种观点不同,这种观念并没有完全贬低宇宙,因为在包含物质与黑暗的同时,宇宙至少包含了一点理念和光明,尽管微不足道。然而,其不可简化的二元论与主流希腊传统相悖:普罗提诺只能通过将物质和邪恶都降格为边缘产物,即从绝对精神流出的最低级的存在,才能接受物质等同于邪恶的说法。
其余的观念显然起源于东方。“七道门的守护者”似乎最早源自巴比伦的行星神崇拜,尽管在其漫长历史中的某个时间点,它们从高级神灵转变为邪恶的恶魔。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大多数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无论是诺斯底派还是异教徒——都承认它们的邪恶力量。在诺斯底派那里,他们是掌权者(archonte);在《以弗所书》中,他们统治着世界(cosmocratore);对于赫尔墨斯主义者而言,他们是七大统治者,“其统治被称为命运”;俄利根(Origen)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在其作品中都提到了基督徒和异教徒对他们的恐惧。然而,即使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里,最杰出的思想家们也否认了这种暴政。普罗提诺撰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尽管由于宇宙的共感,星辰可能预示未来,但它们不能决定未来——不久后他死于一种痛苦的疾病时,占星家们认为他定是冒犯了星宿恶魔而遭到了他们的报复。同样,俄利根也否认星辰具有因果力量,尽管他同时承认它们可以被当做征兆(上帝不是说过,“天穹上要有光体…..来作为迹象吗?”)。最终,是奥古斯丁通过双胞胎的例子,彻底否定了占星术的真实性。
第三种观点将可感世界视为某个邪恶神灵的国度甚至其产物,普鲁塔克(Plutarch)从中看到了(显然他是正确的)对波斯教二元论的回响,即善神(Ormazd)与邪神(Ahriman)之间的冲突。虽然在波斯教(和摩尼教)的信仰中,世界是这场冲突的舞台,但基督教、诺斯底教派和赫尔墨斯主义的教义,则倾向于将世界完全交给反派神灵。《约翰一书》的作者说:“而全世界都蜷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在昆兰地区发掘的一首诗篇说,世界是“恐惧和恐怖笼罩的国度,一个荒凉的苦难之地”;根据一位异教的赫尔墨斯主义者的说法,世界是“邪恶的总体”;对于诺斯底教派的赫拉克利翁(Heracleon)来说,它是一片只有野兽栖息的荒漠;在瓦伦丁派的《真理福音》(Gospel of Truth)中,它是一个噩梦般的领域,在那里“要么一个人不知要逃往何处,要么一个人不知要去追随何人并停滞不前”。对大多数诺斯底教派信徒来说,这样一个世界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神创造的:它必定是某个低等造物主的手笔——要么,如瓦伦丁所想,是一个无知的恶魔,不知道有更好的可能性;要么,如马吉安所想,是《旧约》中那个苛刻又愚蠢的神;或者,在其他体系中,是某个(或某些)反叛上帝的天使。正统的基督教不能走得那么远:它不愿意抛弃《创世纪》。然而,俄利根维护了诺斯底派观点的实质;他将创造归因于某些“无形智慧体”的行为,他们因厌倦了对上帝的沉思而“转向了低级乐趣”。
对于希腊传统来说,一个真实的、实体化的魔鬼是无法想象的;像塞尔修斯(Celsus)这样的人认为这个观念是亵渎神明的;当波菲利和杨布里科斯(Iamblichus)谈到“恶魔的首领”时,他们是在间接地引用源自伊朗的观念。魔鬼通过晚期犹太教进入西方,这种观念将撒但从上帝的代理人转变为上帝的对手;保罗从犹太教中接受了这个概念,并将其称为“这个世界的神”,是“灵性世界中掌权者的领袖”。对某些诺斯底派信徒来说,他是“被诅咒的神”;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是“一个天使,但以神的形象出现”;《迦勒底神谕》(Chaldaean Oracles)将他与冥王哈迪斯(Hades)视为同一个神。
当拿哈玛地(Nag-Hammadi)的诺斯底文本全部问世后,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了解这股席卷西方的悲观主义浪潮的起源和历史,这是“人类所属的两个秩序之间可怕的断裂,即现实的秩序和价值的秩序”。但我怀疑这是否能完全用历史推衍来解释。与其像布塞特(Bousset)那样假设一个原始的诺斯底主义体系,从中衍生出所有其他体系,我更倾向于像德法耶(de Faye)那样,谈论一种诺斯底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早在基督教的第一个世纪中就已经显现,尤其是在保罗的著作中,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反映在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神话结构中。这些结构从许多来源汲取意象,包括基督教和异教、东方和希腊,但正如伯基特(Burkitt)所看到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作者内在经历的一种实体化、一种梦幻般的投射。因此,瓦伦丁派的“深渊”(Bythos),那个不可知的、神秘的原始深渊,所有事物最初栖息的地方,它即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人类意识的深渊”(abyssus humanae conscientiae),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无意识”;而在巴西利德和瓦伦丁的体系中那道将人类经验世界与光明世界隔开的“屏障”(phragmos),则对应于将无意识的启示排除在正常意识之外的屏障。再者,正如特土良所指出的,瓦伦丁将物质世界本身视为阿卡莫斯(Achamoth,译者注:在诺斯底教派信仰中,她是一个低智神祇,是高智神祇的女儿,是巨匠造物主迪米乌尔(Demiurge)的母亲,迪米乌尔就是《旧约》中的上帝)的苦难的投射,阿卡莫斯是人类的本我(Ego)在神话中的对应物,因对终极真理的渴望而受折磨,却只能产生一种杂交的理性主义,并且这种理性主义必须先被“钉死”,然后本我才能得到救赎。最后,上帝分裂为两个形象,一方面是遥远但仁慈的父亲,另一方面是愚蠢而残酷的造物主,这似乎反映了个体父亲形象的分裂——分裂为各自相对应的情感组成部分,无意识心灵中的爱与恨的冲突因此得到了象征性的解决,啃噬内心的罪恶感也得到了缓解。
如果这些是人们在这个时期倾向于思考世界的方式,那么他们对人类状况的看法是什么?显然,在这样的世界里,普罗提诺所称的“内在人”(the inner man),圣保罗和诺斯底教派所称的“属灵的人”(pneumatic)或灵性的人(spiritual man),必定感到自己是个异乡客和流亡者;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确实如此。基督徒们期待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们自然从早期就把自己视为“异乡人和朝圣者”,他们的教导是“不要去爱这个世界,也不要爱世上的任何事物。”用《丢格那妥书》(Epistle to Diognetus)中的警句来说:“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度,却活得像异乡人;他们像公民一样履行所有的义务,却像异乡人一样承受所有的困苦;每一个异邦都是他们的国度,每一个国度对他们来说都是异邦。”这种疏离感在基督教诺斯底教派中更为强烈,他们构成了一个“异类(上帝的)选民”群体,教授一种“异类知识”,并希望有朝一日迁居到一个“全新”或“异类”的星球上。但这种情感绝不仅限于基督教群体,在柏拉图学派,它已成为一种常态。甚至连马可·奥勒留,一个多数时间都在治理国家的皇帝,也能时不时表达出没有归属的凄凉感:“人的生理生活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心理生活则是梦幻与谵妄;他的存在是一场战争,一段在异乡的停留;至于他们的身后名,则终将被遗忘。”他通过动用所有从斯多葛宗教那里获得的力量来抵制这种想法完全控制他的内心,他提醒自己,他的存在是伟大统一体的一部分。但这些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他也无法逃避,他只能问:“还要多久?”
这样的反思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何存在(ἐπὶ τί γεγόναμεν)?”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曾提出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答案;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柏拉图认为这正是哲学应该探究的主题。但事实上,幸福的人们通常不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幸福的生活本身似乎就是其存在的理由。只有在帝国时期,哲学家和其他人才开始将其视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费斯图日勒以杨布里科斯在其《论灵魂》中所做的学述汇编为起点,对这些答案进行了分类。他将它们分为两大类:乐观派和悲观派。对于那些坚守古老信仰,认为宇宙具有神性的信徒来说,《蒂迈欧篇》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人类,世界的完美将是不完整的。换言之,正如一位公元2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所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揭示神圣的存在”——人类的存在是神灵的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其他人从柏拉图的说法出发,即“所有生命无处不在关心无生命的事物”,认为人类是神的管理员,尘世生活是一种“服务”(leitourgia)形式。这既可以从乐观的角度解读,也可以从悲观的角度解读。塞尔修斯称之为“对生命的服务”;马可·奥勒留则更为苦涩地称之为“对行尸走肉的服务”;巴戴桑(Bardesanes)的印度圣贤们将其视为一种“强迫性的对自然的服务”,而他们不情愿地承担着这种义务。这种服务对灵魂来说可能是危险的,普罗提诺生动地将灵魂比作一个舵手,他在决心拯救自己的船时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然而,他认为,从总体上看,灵魂可以从其与邪恶打交道的经历中获益。对于普罗克洛(Proclus)来说,这种经历是我们所受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那里,我们发现了一种相似的观念,即将世界视为“灵魂的学校”。
但是,对于更激进的二元论者来说,这种解释似乎不够充分。如果地上的人类是外来流浪者,那么他们在这里的存在只能归因于一次堕落,正如《斐德罗篇》(Phaedrus)中失去翅膀的神话故事一样。按照杨布里科斯的说法,这是“非自然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出生显然是一种不幸,智者从不庆祝他们的生日。人类的堕落状态可以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对先前在天堂犯下的原罪的惩罚,要么是灵魂自身做出的错误选择的结果。将投胎到凡间视为惩罚的观念似乎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和俄耳甫斯教(Orphic,译者注:也就是古希腊人的多神论宗教):它出现在古老的毕达哥拉斯教义问答中;亚里士多德将其归因于“神秘主义的倡导者”,克兰托尔(Crantor)则更模糊地将其归因于“许多智者”。基督教或半基督教的诺斯底教派(瓦伦丁、马吉安、巴戴桑、摩尼(Mani,译者注:摩尼教创始人,中国人称该教为“明教”))从这些来源接受了这种观念,并将它与犹太人对堕落天使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俄利根似乎也接受了它;同样,作为一个异教的赫尔墨斯主义者,撰写《宇宙处子》(Kore Kosmou)的作者也接受了这一观念。根据后者的说法,灵魂的罪过,是一种由“傲慢的自我肯定”(tolma)所激发出来的不服从。这个教义的另一种形式则没有那么浓郁的神化色彩:堕落,是灵魂有意的选择,而这便构成了其罪过。这种观点出现在努米尼乌斯的著作中,出现在赫尔墨斯的《牧人者》(Poimandres)中,有时也见诸普罗提诺的著作中。灵魂的动机被描述为对自然或物质的热爱,或更微妙地说是自恋——她爱上了自己投映在物质世界上的倒影——或者又回到了野心或者“tolma”。“tolma”这个词本身的出现暗示了它来自毕达哥拉斯学派,因为我们知道“tolma”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来称呼二元对立原则(Dyad)的术语,它与一元论正好相反。当奥古斯丁告诉我们“audacia【不逊】使灵魂远离上帝”时,他的“audacia”就是对“tolma”的翻译。
普罗提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值得一提,因为我认为他的观点尚未被完全理解。他曾被指责在这个问题上前后想法不一致且思路混乱:这样说不太公平,因为,正如他自己指出的,这种不一致在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曾经在于,并且仍然在于调和《蒂迈欧篇》中的宇宙论与《斐多篇》(Phaedo)和《斐德罗篇》中的心理学。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普罗提诺首次尝试调和它们,但并不十分成功。可总的来说,他在早期的作品中倾向于接受从努米尼乌斯那里继承来的悲观假设,即个体的灵魂有意识地选择了坠落到凡间,渴望“独自统治世界的一部分”或“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三篇连续的文章中,他在这种关联的意义上借用了毕达哥拉斯的二元论话语(tolma-language)。当普罗提诺最终与诺斯底主义决裂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驳诺斯底主义者》(Against the Gnostics)一文中,认为灵魂出于傲慢和“tolma”创造了世界的正是他的反对者们。自那以后,他从自己的说教中剔除了二元论话语,也不再将个体灵魂落入凡间视为罪过。在第四章,第三节的第13段中,我们看到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成熟看法:灵魂落入凡间,“既不是有意的选择,也不是服从上帝的命令”,而是出于本能,遵循一种内在的“指示”(prothesmia),就像牛长角一样;这种必然性是生物学层面的。在这里,普罗提诺最终摆脱了努米尼乌斯的影响。这个最终的定论来自他晚期的一篇著作,《个人与有机体》(The Person and the Organism),他在其中告诉我们,灵魂对躯体的照亮,其罪过不会更甚于投射下身后那道阴影。无论他早期有何疑虑,普罗提诺最终成为了希腊理性主义的捍卫者。
我已经尽我所能,在简短的篇幅内描述了当时的人们所特有的对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地位的态度。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态度对人类行为产生了影响。显然,这样的态度不会鼓励人们去“利用或改善外部世界”,事实上,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基于一种新的神权政治理念,即皇帝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之前,在公元3世纪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作为。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超凡脱俗与对现世漠不关心等同起来。我们可能会觉得马可·奥勒留或普罗提诺更关心自我完善而不是现实生活;但我们不要忘记,马可·奥勒留为人类福祉所做的努力远胜过大多数人,而普罗提诺则从对“太一”(the One)的沉思中抽出时间,用他自己的房子设立孤儿院,并担任孤儿们的受托人,“听他们背诵功课”和“帮他们核对财产账目”。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基督教教会的慈善活动,仅举一个例子:在公元3世纪中叶,罗马城的教会社区支持了1500多名“寡妇和穷人”。他们并不仅限于帮助基督徒同伴,尤利安(Julian)恼怒地说,“这些持无神论的加利利人,不仅养活了他们自己的穷人,也养活了别人的穷人,而我们却对自己的穷人置之不理。”这一点我将在第四章中再作讨论。
我们可能预料到,并也确实发现了一种更积极的影响,就是敌对情绪向内的投射:对世界的怨恨变成了(或伴随着)对自我的怨恨——塞内卡称之为“自我厌恶”(displicentia sui)。这种情绪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泄出来:一种是纯粹的精神折磨,由过度敏感的良心——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超我——引起的;另一种是身体上的自我惩罚行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包括自残或自杀。自我谴责在各个时期的基督教作家中都很常见,这很自然,因为他们的信仰提出了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的道德要求。而在异教徒中,这种情况则相对罕见。毕达哥拉斯派的《金言》(Golden Verses)推荐自我反省:在入睡前,要回顾一天中所做或未做之事;批评自己的恶行,并为善举感到高兴。这条建议得到了爱比克泰德的赞同和引用,塞内卡也对其身体力行。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内,最引人注目的道德自责的案例却出现在看似最不需要的地方,那就在是马可·奥勒留身上。对他来说,对世界的怨恨是最大的不敬,所以他把这种怨恨转向了自己。在25岁时写给弗朗托(Fronto)的一封信中,他就已经对自己未能实现哲学生活而感到愤怒:“我为我的过错忏悔”,他说道,“我生我自己的气,我感到悲伤和不满,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同样的感觉在他当上皇帝后仍然困扰着他:他的行为未能达到自己的理想要求,错过了美好的人生;他的存在使自己变得伤痕累累,污秽不堪;他渴望成为不同的自己,在死前“终于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忍受自己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时期,其他一些人(以及处于不同情绪状态的马可·奥勒留本人)为了能够忍受自己,便在自我和身体之间做出明确的二分法,并将他们的怨恨转移到后者身上。这种二分法当然来自古典时代的希腊——这可能是她对人类文化最深远,同时也或许是最值得质疑的贡献。然而,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它却被用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异教徒和基督徒(尽管不是所有异教徒或所有基督徒)竞相辱骂人类的身体;它被称为“泥土和脓血”,是“一个肮脏的屎尿袋子”;人被浸入其中,就像在肮脏的水中沐浴一样。普罗提诺似乎为拥有身体而感到羞耻;圣安东尼(St Anthony)每次不得不进食或满足其他身体需求时都会脸红。因为肉体的生命就是灵魂的死亡,所以救赎在于扼制它;正如一位沙漠教父所说:“我正在杀死它,因为它正在杀死我”。身心的统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也被分裂成两半;其中一半通过折磨另一半来满足自己。
这种苦行主义与古希腊语中的“ἄσκησις”相去甚远,这个词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仅仅意味着“训练”。我们能够在早期希腊教义中发现这样或那样的苦行实践的先例,但整个苦行运动的起源仍然不明朗。我们看到关于一些苦行社群的描述,这些社群似乎在基督诞生前不久,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不同地方独立发展起来:巴勒斯坦的艾赛尼派(Essenes)、马里奥特湖(Lake Mareotis)周围的治疗者派(Therapeutae)、卡埃莱蒙(Chaeremon)所描述的埃及的沉思者以及罗马城的新毕达哥拉斯派(Neopythagoreans)。遗憾的是,除了昆兰(Qumran)文献之外,这些团体没有直接向我们传达他们的声音;我们只有二手的描述,而在其中很难区分历史事实和对理想的文学表达。这些团体对基督教苦行主义有多大影响?我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霍尔(Holl)和赖岑施泰因(Reitzenstein)指出,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圣安东尼传》(Life of St Anthony)在某些方面借鉴了一部异教的《毕达哥拉斯传》(Life of Pythagoras);这完全不令人惊讶,因为圣徒传记(hagiography)是一种基督徒和异教徒共有的文学体裁——我们在斐罗斯特拉图(Philostratus)的《阿波罗尼乌斯传》(Life of Apollonius)、马里努斯(Marinus)的《普罗克洛传》(Life of Proclus)和尤纳皮乌斯(Eunapius)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传》(Lives of Neoplatonic philosophers)中都能找到异教的样本。但是,正如费斯图日勒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的苦行实践源自异教的模式。确实有少量证据表明,在基督教隐修运动之前有“异教隐士”的存在,但我们不能轻率地断定他们作出的榜样影响了沙漠教父们;我们只能说,同样的心理驱动力可能同时作用于两者。如果真的有一个模范,它更可能源自犹太人而不是异教。
若要理解异教和基督教苦行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翻看《塞克斯图斯格言集》(Sentences of Sextus),这是一部宗教和道德格言集,它以两种形式被保存了下来,一种是一位基督教编纂者在公元2世纪末加工改编后的版本,另一种是几个更为古老的异教版本。异教格言中的苦行主义是温和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乏味:自律是虔诚的基础;我们应该只在饥饿时进食,困倦时才睡觉,避免醉酒,只为生育而发生性关系。但在最后一点上,基督教编纂者持有更为严厉的观点:如果要冒险结婚的话,婚姻应该成为“一场自制力的竞赛”,而自我阉割比不纯洁更为可取。这种观点被基督教和诺斯底教派的严格主义者广为接受,并且有时也付诸实践。盖伦(Galen)和俄利根都证实,许多同时代的基督徒终生禁欲;卒世童贞被视为“至高无上和最完美的成就”;广为流传的《保罗与德克拉行传》(Acts of Paul and Thecla)教导说,只有保持处子之身才能复活;据说马吉安派信徒(Marcionites)拒绝向已婚人士施行圣礼,至于通奸,在早期教会中,它通常被与谋杀和叛教一起列为不可饶恕的罪行。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曾引用过一起自阉未遂的案例并表示认同,而俄利根(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尤西比乌(Eusebius)的话)在还是个孩子时就阉割了自己。在稍后的时期,这类行为在沙漠教父中并不少见;到了公元4世纪,不得不通过教会法来禁止这种行为。关于持续的自残行为,沙漠教父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令人反感的例子:一些人在石柱顶上生活多年,另一个人将自己关在一个无法站立的箱子里,还有一些人永远保持直立姿势;还有一些人给自己戴上沉重的锁链(在埃及发现了其中一人的遗骨,锁链还在身上);其他人则以在整个大斋节(Lent)期间完全禁食等耐力壮举为荣——我不必再列举下去。
这一切疯狂从何而来?我还是不得而知。尽管有赖岑施泰因,以及最近的莱波尔特(Leipoldt)对其研究得出的观点,我还是难以相信它在希腊传统中有实质性的根源。对于上一段描述中的那类想法和实践,我所了解到的希腊的相似案例既不够充分,也缺乏可靠的证据;它们遭到像普鲁塔克和爱比克泰德这样的异教道德说教者的谴责,而且,像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这样具有希腊文化背景的基督徒也坚决抵制它们。它们在《旧约》中找不到根源;我认为在被归于基督教创始人的教导中也找不到根源(除了一段意义存疑的经文外)。至于对童贞所赋予的荒诞不经的价值,似乎主要应归咎于圣保罗,尽管《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暗示,他的观点没有他所针对的社群的观点那么极端。无论如何,那些严格主义者正是从他的作品中摘取文本,来为他们心理上的偏执辩护的。比较理智的人则认为,“教会,应该就像诺亚的方舟一样,必须为不洁和洁净的动物都留有空间”;但是一股强烈的狂热严格主义已经被注入教会的体系中。它像一剂慢性毒药一样在那里徘徊不去,而且(如果一个局外人可以评判的话)至今尚未被排除干净。
然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本章中,我试图展示的是,对人类处境的蔑视和对肉体的憎恶是当时整个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疾病;虽然其更极端的表现主要见于基督教或诺斯底教派,但其症状也以较温和的形式出现在接受纯粹希腊教育的异教徒中;这种疾病在各种各样的神话和幻想中得到表达,有些源自希腊,有些源自东方原型(通常具有不同的意义或强调不同的重点),而有些则显然是新的。我倾向于将整个发展看作更像是一种内源性神经症,而不是来自外部源头的感染,它是普遍而强烈的内疚感的一个迹象。公元3世纪的物质困境当然助长了它,但并非起因,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第二章:人与亚神的世界
我们被那些我们假装理解的力量主宰着。
在第一章中,我描述了在基督教早期的几个世纪中,逐渐演变的贬低宇宙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神性从物质世界的逐步退离),以及相应的对普通人类经验的贬低。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介绍一些从二、三世纪留存下来的记载,这些记载记录了超凡的体验。本章,我首先将引用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定义“亚神”(daemonic)的段落。迪奥蒂玛(Diotima)对苏格拉底说:“所有的亚神,都是介于神明与凡人之间。它向神明传达并解释凡人的愿望,又向凡人传达神明的意志,它填补了两者之间的鸿沟……神明不与凡人直接接触;只有通过亚神,凡人与神明之间才能进行交流和对话,无论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还是在睡梦之中。而擅长这种交流的人就是具有灵力的人(daemonic man),与之相比,那些精通艺术或手工艺的人不过是学徒而已。”在柏拉图的时代,对于模糊术语“亚神”(daemon)和“亚神们”(daemonios——“daemon”一词的复数)的精确定义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尝试,但到了基督纪元后的第二个世纪,它只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表述。几乎每个人,无论是异教徒、犹太人、基督徒还是诺斯底教派信徒,都相信这种生命的存在,以及它们扮演着中间人的职能,无论他们称之为“亚神”(daemons)、“天使”(angels)、“艾咏”(Aion,译者注:古希腊的时间之神,象征着无限、永恒与轮回)或仅仅是“灵”(πνεύματα,译者注:该词为复数形式,单数为“πνεύμα”)。在许多虔诚的异教徒眼中,即使是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在那个时候也不过是在凡人与神明之间负责协调的亚神,他们是由一个隐形的超越凡尘的统治者任命的地方长官。而那些懂得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的“具有灵力的人”,则相应地受到尊崇。
我先从有非凡梦境的人说起。特土良说:“大多数人对神的认知都是来自梦境”——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 B. Tylor)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的确,在所有与超自然接触的方式中,做梦是最普遍的一个,而且在古代也是如此。正如辛奈西斯(Synesius)所说,这是唯一一种奴隶和百万富翁都可以使用的占卜方式,因为它不花分文,也不需要任何器具;暴君也不能禁止它,除非他禁止自己的臣民睡觉。毫无疑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异教占卜实践中,只有做梦被基督教教会所容忍。但是预言性的梦境也有坚实的《圣经》依据:圣彼得自己就引用过先知约珥(Joel)的话:“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至于古典希腊传统中的“神启”或“神谕”梦,我不打算重复拙著《希腊人与非理性》(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中的内容。我只想顺便提一下,在写那本书时,我认为古代记录中如此频繁出现的“神启”梦反映了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实际梦境体验的差异,我现在不像当时那么肯定了。在此期间,杰弗里·戈勒(Geoffrey Gorer)先生向我指出,我们记得住的梦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认为哪些内容值得记住,因此古代的梦境记录可能呈现的是对原始梦经验过度简化后的版本。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决定的可能不是做梦时实际梦到的内容的模式,而仅仅是梦被记住的内容的模式。然而,这只是题外话。现在,我要描述的是从古典时期保存下来的由某个特定的人所经历的漫长系列的梦境。
就在马可·奥勒留记录他的自省和自责的那几年里,他的同时代人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却在写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日记。这不是一本日记,后来辛奈西斯称之为“夜记”:这是他夜复一夜记录的梦境,同时也是他与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交流的记录;据他所说,其中包括“各种治疗、一些对话和连续的演讲、各种幻象、阿斯克勒庇俄斯对各种事情的预言和神谕,有些是散文,另一些是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夜记积累到了惊人的30万行之多。当阿里斯提德斯最终开始整理它们时,他发现很难分类,因为他似乎忘记了给它们标注日期;而且其中一些在一次家庭骚乱中遗失了。但是,从剩下的那些中,再加上他的记忆,他以不太连贯的顺序,整理出现存的五卷《神圣教导》(Sacred Teachings),并在开始撰写第六卷时去世。它们构成了异教世界留给我们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记录宗教体验的自传。
阿里斯提德斯是小亚细亚一位富裕乡绅的儿子;他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师从后来教导马可·奥勒留的同一位导师;二十多岁时,他已经博览群书,游历广泛,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精通最优雅的雅典式文风。26岁那年,他访问了罗马,并在宫廷中被召见;正当他在公共事务领域前途不可限量之际,却遭受了漫长的一系列病痛的第一次打击,这些病痛使他至少在十二年之内成为一个长期病患,并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他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疾病都属于心理作用导致的病症:在他报告的各种症状中,我们可以辨认出急性哮喘和各种形式的高血压,这些引发了剧烈的神经性头痛、失眠和严重的胃部问题。因此,他在睡梦中从医神那里获得的奇怪处方常常能至少暂时缓解最严重的症状,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梦境本身值得专业心理学家的关注,我希望有朝一日它们能得到这样的研究。
这些梦境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令人恐惧的焦虑梦,在这些梦中,他被毒害,或被公牛追赶,或遭到野蛮人的攻击;描述最详细的一个梦是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长长的隧道里,周围是一些持刀的可疑人物,正准备对他下手。第二类是可悲的自负梦,在这些梦中,他受挫的事业得到了奢侈的补偿:白天卧床不起,晚上与皇帝交谈;他得知自己将与亚历山大大帝共享一座公共纪念碑;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向他保证,他是比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更伟大的演说家,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他集柏拉图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于一身。最后一类是数不尽的“神启”梦,在这些梦中,他遇到他的守护神,或者至少从他那里得到暗示。其中大多数,但绝不是全部,都与医疗有关。正如阿里斯提德斯本人所说,梦境里的处方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往往出奇地残忍。当他被迫五年多不能洗热水澡,被迫在冬天赤脚奔跑,冰天雪地时在河中沐浴,在寒风中浸泡泥浆,甚至故意让自己晕船时,我们不禁注意到这些神启处方与伊西斯教徒的苦修和某些基督教苦行僧的自虐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可以猜测它们有着相同的心理起源;对这些人来说,身体或精神健康的代价是对一种无意识罪恶感无休止的赎罪。
同样突出的是一种强迫性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中,他通过有惊无险的象征方式的预演,来躲避某种想象出来的威胁着他的邪恶。因此,他必须经历一次模拟的船难,以逃避真实的船难;他必须用尘土洒在自己身上——用他的话说,是——来“代替埋葬,这样或许也算以某种方式实现了”;“为了整个身体的安全”,他甚至必须牺牲一根手指,尽管最终这被改为牺牲一枚戒指代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最后这个例子与一个在黑暗隧道中被坏人威胁要残害的小男孩有关联。)如果这些个人牺牲还不足以平息命运,他将会牺牲他的朋友。他毫无愧疚地告诉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他的两个朋友如何不自觉地扮演了阿尔克斯特斯(Alcestis),为了他这个阿德墨托斯(Admetus),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他的宝贵生命的替代品而死(译者注:这段典故出自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阿尔克斯特斯曾代替患病的丈夫阿德墨托斯受死)。
面对这样的内容,缺乏耐心的现代读者可能会倾向于将阿里斯提德斯斥为“一个脑筋有问题的人”,只有精神病学家才会对他感兴趣。他的确精神错乱,而且是以一种不太令人愉快的方式,然而,的体验必须被归类为宗教性质的;这就是我在这里介绍他的原因。他相信自己是被神选中的仆人,是伟大医者的“代言人”(hypokrites)。当阿斯克勒庇俄斯在梦中对他说出那串神秘的词语“σὺ ει ειϛ”(“你被特别选中”)时,他感到这补偿了他遭受的所有苦难,并为他的存在赋予了新意义:从此以后,他必须改变,必须与神合为一体,从而超越人类的局限;在这个新生活中,他采用了一个新名字,西奥多罗斯(Theodorus,Elyon译者注:这个名字在希腊文中的含义是“神的馈赠”),因为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从今往后,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没有神的许可,他都不会去做;因为“与服从神相比,任何事都不再重要”。事实上,他已不再孤单,不再被囚禁在神经症可怕的孤独之中;他找到了一位救苦救难的神明,他的出现带来了无以言表的喜悦。
最初,阿斯克勒庇俄斯仅仅是个医疗顾问,但是渐渐地,他对阿里斯提德斯的援助扩展到他的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阅读方面提供指导,激发他的灵感,为他提供演讲的开场段落或诗歌的首行,偶尔还会让他预知未来——主要是以近期天气预报的形式(阿里斯提德斯对天气特别敏感)。我们该如何解读这种人与神之间奇特的共生关系呢?答案的线索也许就在阿里斯提德斯的的一个梦中,在梦里,他见到自己的雕像,然后看着它变成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雕像。对阿里斯提德斯来说,这个梦象征着他与自己的守护神合而为一。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破碎人格重建的象征,这个人格通过将自我认同为理想父亲的形象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阿里斯提德斯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关系在强度和持久度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但这种关系也有许多先例。塞尔修斯明确告诉我们,阿斯克勒庇俄斯曾亲自在“众多希腊人和蛮族人”面前显灵,为他们治疗疾病并预示未来;他的说法得到了许多现存铭文的证实,这些铭文来自心存感恩的病患们的奉献。在阿里斯提德斯的同时代人中,马克西姆斯(Maximus of Tyre)曾在清醒状态下受神的眷顾看到过这样的异象;马可·奥勒留感谢诸神赐予“有益的梦境”,治愈了他的眩晕和咳血;甚至连伟大的医生盖伦也相信,他遵循梦境的指引挽救了许多生命。另一位同时代人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毕生致力于从各种来源收集和分类梦境,以及对它们的解释。阿里斯提德斯的信仰是他那个时代的信仰——用萨姆森·艾特雷姆(Samson Eitrem)的话说,这是一个“白日里的现实不再值得被信任”的时代。
基督教对待梦境的态度在原则上并无不同,只不过——同样出于医疗的目的——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入睡求梦治疗被替换为在供奉殉道者或者圣人的圣祠里的入睡求梦治疗——这种做法至今仍在希腊存在。正如我们所料,在早期教会中,具有宗教内容的梦境很常见,并且被非常严肃地对待。当一位主教梦见末日审判即将来临时,信徒们便停止耕种,全身心投入祷告中。根据俄利根的说法,许多人因梦境或清醒时的幻象而皈依了基督教。对于另一些人而言,梦境标志着他们精神生活中的转折点:纳塔利乌斯(Natalius the Confessor)由于一个梦而脱离了异端,在这个梦中,他被几个神圣的天使彻夜鞭打;贵格利因梦见四十位殉道者斥责他的惰怠,转而过上沉思的生活;一个梦使奥古斯丁的朋友——根拿丢(Gennadius)医生对灵魂不朽确信不疑;甚至像西普良(Cyprian)这样务实的人似乎也经常依照梦的指引行事。我想,有记录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梦境恐怕要数君士坦丁在米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战役前夜的那个梦,在其中,他看到了那个神秘的连字图案——凯乐符号(Chi Rho,译者注:☧,由希腊字母“Χ”(Chi)和“Ρ”(Rho)构成的连字符号,君士坦丁大帝用它代表耶稣基督),并被告知“hoc signo victor eris”【凭借此符,你将无往不胜】。我在此无法深入讨论围绕这个梦境的激烈争论;但我们倒也不必采纳19世纪历史学家的理性主义观点:认为这不过是政治家为了震慑民众而编造的故事。有独立的证据表明君士坦丁确实与他的臣民一样迷信;但像西普良一样,他完全能够将迷信的认知与对政治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他的梦境确实发挥了实际的作用,但这并不证明它是虚构的,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梦是有目的性的。
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里记录的最有趣的基督徒的梦境是那些被归属于圣佩尔佩多亚(St Perpetua)的梦。她是一位22岁的已婚妇女,于公元202至203年间在迦太基殉道。我之所以说“被归属于”,是因为殉道士传记是一类高度可疑的文学类别,在我们接受《佩尔佩多亚受难记》(Passio Perpetuae)的证据之前,需要对其进行讨论。它是基于两份第一人称的文献构建起来的。其中一份据称是佩尔佩多亚在等待处决期间所写的狱中日记;它包括对四个梦境的详细记述,及其相关的情境。另一份包含了以萨提洛斯(Satyrus)的口吻讲述的一个异象,他也在同一刑场殉道。一位匿名的编纂者在这两份文献之外添加了一个殉道者名单、一些关于佩尔佩多亚的事实,以及一份关于实际殉道过程的长篇叙述。整部作品以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版本流传下来。大多数讨论过这份《受难记》的教会历史学家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编纂者的可信性和所包含文献的真实性;但是像爱德华·施瓦茨(Eduard Schwartz)这样的明眼人却认为两份文件都是编者伪造的。对我来说,这份文献的不同元素具有非常不同的价值。编纂者那血淋漓又充满说教的叙述并不能让我信服,尤其是它与后来的《佩尔佩多亚行传》(Acta Perpetuae)中那种直截了当,冷静的对事实的叙述直接冲突。编纂者告诉我们,他是在圣灵的许可下撰写的,看来圣灵一定是向他提供许了多细节——那些旁观者几乎不可能注意到的情节和对话。此外,如同福音书中的叙述一样,某些事件似乎是为了应验预言而被引入的。然而,我们无需关心他的叙述的历史真实性。我对萨提洛斯的幻象也同样持怀疑态度。但有几个很好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佩尔佩多亚的狱中日记基本上是一份真实的记录。
首先,佩尔佩多亚的朴素文风与编纂者的修辞技巧大不相同,这使得一些学者将编纂者认定为特土良。据我看来,现在已有相当把握断定,编纂者使用的原始语言是拉丁语,但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日记原本是用希腊语写的!
其次,这份日记完全没有包含神迹,其中报告的梦境完全符合梦应该有的样子。与萨提洛斯的幻象不同,这些梦是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呈现的,作为监狱生活体验的一部分。前三个梦境是“求得”的梦;它们是由祈祷引起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梦描绘了她即将到来的殉道,第一个梦境中她为了躲避一条蛇,爬上一个危险的梯子到达了一个地方,在那里她遇到了天国里的牧羊人,最后一个梦的意象则是与魔鬼搏斗(以一个可怕的埃及人形象出现)并最终战胜了他。第二个和第三个梦与她早已去世的幼弟狄诺克拉底(Deinocrates)有关,令她惊讶的是,在梦中出现的前一天,他已经闯入了她的清醒意识中。他可能代表了无意识中一个需要关注的元素。伪造者几乎不会编造出这样的细节。而这些梦本身也有真正的梦的那种不合逻辑的特点。在第一个梦中,牧羊人直接从羊身上挤出奶酪,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凝乳,给她吃——这种情节压缩的现象在梦中很常见。在第四个梦中,佩尔佩多亚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男人;这同样也不是一个圣徒传记作者会杜撰的细节。
此外,这些梦境几乎没有我们本应在虔诚的虚构作品中看到的特定的基督教色彩(而在萨提洛斯的幻象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特色)。在天堂吃奶酪完全不符合正统,而且我也怀疑这与被称为“面包奶酪派”(Artotyrites,译者注:是一个早期基督教异端,主张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使用的是含酵母的面包和真正的葡萄酒,而并非无酵饼和水)的一个晦涩异端教派到底有没有关系;该派别首次被提及是在近两个世纪后;而且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域;此外,梦中也缺少了面包这个重要元素。梯子的意象不仅在阿里斯提德斯的梦中有与其相似之处,在密特拉教(Mithraism)中也有;而关于狄诺克拉底受苦的梦,与其说是基于基督教关于炼狱的描绘,不如说是基于古代异教关于口渴的亡者和不幸夭折的逝者的命运的观念。在最后的梦境中,至高无上的审判者并没有被描绘成基督的形象,而是一个角斗士的裁判或教练;胜利者的奖赏不是殉道者的桂冠,而是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的金苹果。这种异教的意象出现在一个刚皈依基督教不久的人的梦中是完全自然的;如果出现在宣传性的启示录中反而会令人惊讶。
因此,我的结论是,在这份狱中日记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位英勇殉道者临终的亲笔记录,真实可信。这是一份关于人性和勇气的感人至深的记录,完全没有像依纳爵(Ignatius)或阿里斯提德斯那种病态的自命不凡。有人将佩尔佩多亚与另一位基督教殉道者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作了一番饶有兴味的比较,朔尔在大约同样的年龄被纳粹处死。朔尔小姐在生命的最后一夜躺在监狱中时也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正在爬一座陡峭的山,怀里抱着一个要受洗的孩子;最终她跌入了一个裂缝,但孩子得救了。这座山及其裂缝对应于佩尔佩多亚梦中危险的梯子;未受洗的孩子让人想起狄诺克拉底,他在七岁时未受洗就夭折了。对于两位梦者来说,孩子都得救了,她们的母性之心得到了慰藉。但是,佩尔佩多亚梦到了一位善良的牧羊人和在竞技场上的象征性的胜利,而索菲·朔尔则满足于看到自己坠入深渊:在二十世纪,要相信未来会有奇迹发生,比在公元3世纪要困难得多。
现在,我必须转而考虑另一种类型的“灵力”人格——即,在光天化日之下,超自然的存在对(或者通过)其讲话的男性或女性。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类人最常充当(尽管并非总是如此)“灵媒”的角色。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称他们为“神之容器”(god-box)。在古代,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果你相信他们的预言,你会称他们为“prophetai”【超自然的发言人】,或者“entheoi”【被神充满的人】;如果你不信,他们就是“被妖魔附身”(daimonontes),这将他们与癫痫患者和偏执狂归为相同的类别。或者你可以使用中性的心理学术语“ekstatikoi”,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其正常意识状态暂时或永久受到干扰的人。通俗的称呼是“engastrimuthoi”,即“腹语者”。《新约》和早期教父们使用“prophetai”一词,有时也使用“pneumatikoi”,即“被圣灵充满的人”,尽管后者也有更广泛的应用。所有这些词都是或可以用于描述同一种心理学类型:容易解离症(dissociation)发作的人。古代的观察者像我们一样,认识到两种程度的解离障碍,一种是主体的正常意识与侵入人格并存,而另一种是更深的恍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正常自我完全被压制,以至于对其间所说所为毫无记忆。在前一种情况下,主体可能只是报告侵入的声音在说什么;在后一种情况下,声音通过主体的嘴唇以第一人称说话,就像“阿波罗”在德尔菲(Delphi)或克拉洛斯(Claros)的神庙里所做的那样。在古代,侵入者通常自称为神明或亚神(daemon);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它才会自称是已故的凡人,就像在现代通灵术中那样:人们更渴望与超自然接触,而不是已故的亲友。
这种渴望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宗教性的;它们往往纯粹出于实际考虑。当时和现在一样,这些第二人格都被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他们能治愈疾病;他们能说天使的语言;他们能读取询问者的想法或密封信件的内容;他们能感知远方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预知未来。官方神谕的声望长期以来一直在衰落;尽管在公元2世纪由于帝国的扶持而有所复苏,但他们从未(可能除了克拉洛斯之外)完全恢复昔日的声望。原因不是人类的好奇心或迷信程度有所减少,而是竞争加剧了。占星术是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未来的书面启示,比如西比拉神谕(Sibylline Oracles)以及众多基督教和诺斯底教派的启示录。据说奥古斯都曾下令收集并烧毁了超过两千份匿名或伪名的预言书。此外,旧的宗教中心不再垄断先知。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bonutichus)的事迹告诉我们,从零起步打造一个全新的神然后在它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神谕并不是难事,而且,在良好人脉(他的女儿嫁给了亚洲总督)的护持下,还可以将其发展成一项红火的生意;在当时只有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和基督徒对他提出了义正言辞的反对。有证据表明,从公元3世纪开始,私人灵媒的使用大大增加了——米努修(Minucius Felix)称他们为“没有神庙的先知”。魔法莎草纸书提供了使这些人进入他们所需要的恍惚状态的秘方。波菲利引用的许多“神谕”似乎来自这类文献;降神者们(theurgists)系统地利用了私人灵媒,并且他们奉一部神智学(theosophical)大杂烩为圣典——它被称为《迦勒底神谕》。
毫无疑问,对神谕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日益增强的不安全感。这一点可以从一份公元3世纪晚期的莎草纸文书得到证实,它记录了向某个神谕提出的21个问题,其中包括这样的问题,如:“我会成为乞丐吗?”、“我会被卖掉吗?”、“我应该逃走吗?”、“我会拿到我的薪水吗?”、“我被下了咒吗?”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人们并非仅仅对这一类问题感兴趣。在第二或第三世纪的某个时候,一位名叫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的人向克拉洛斯神谕提出了一个不那么个人化的问题,他问道,“你是神吗?还是另有其人?”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有点天真:正如法国编辑在退稿单上写的那样,“关于神的问题,缺乏现实意义”。但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切实且重要的——除了求助于受启示的先知,还能从哪里得到答案呢?克拉洛斯神谕提供了一个适合时宜的答案:它说,至高无上的神是艾咏,即“永恒”(Eternity);阿波罗只是他的“天使”或使者之一。这种新颖的“教义型”(Doctrinal)神谕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除此之外,先知主要是在两种背景下发挥了深远的宗教影响力——基督教(包括基督教诺斯底主义)和降神术(theurgy)。
关于降神术,我在别处已有论述,由于它的全盛时期超出了本书所论的时代范围,我不会在此详述。在最早期的教会中,先知们声称受圣灵启示而发话的观念被普遍接受,它有坚实的经文依据:“the pneuma”(圣灵)已降临到使徒身上,并将持续到最后的审判日;据说基督本人也预言了圣灵的到来。就像在异教预言中一样,圣灵可能会通过其人类工具以第一人称说话:《使徒行传》第13章中就有一个例子。当然,需要某种形式的把控来确保启示确实来自圣灵,而不是恶魔。圣保罗认为,辨别不同的灵是一种特别的天赋。在实践中,这种把控起初似乎主要是道德上的:只要四处云游的先知谦卑地生活,不索取任何东西,那他大概就是没问题的;但《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警告不要相信那些受启示索要金钱或一顿美餐的假先知,赫马(Hermas)也警告不要相信那些通过算命来博取名声的先知。塞尔修斯发现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区”有一些假先知,“在神庙内外,”他们“为了一点琐事就会轻易地预言”;根据塞尔修斯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声称自己是神、神之子或圣灵,但毫无疑问,这种声明是由通过他们以第一人称说话的声音作出的。塞尔修斯曾与其中一些人交谈过,他们承认自己是骗子。有时他们被认为是蒙塔努斯派信徒(Montanists),但如果按照塞尔修斯和蒙塔努斯派通常被认定的年代来看,蒙塔努斯派信徒出现在那个区域似乎还为时过早。
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的先知,没有一人为我们留下一份可以与阿里斯提德斯的《神圣教导》相似的经验记录。无论是斐罗斯特拉图的《阿波罗尼乌斯传》那样的虚构传奇,还是赫马的《牧人书》这样的杜撰寓言,都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真实的先知的信息。具有同时代的传记传世的这一类人物中,我们唯一可能找到的样本,就是亚历山大和佩雷格里努斯(Peregrinus);而由于这两本传记都充满敌意,很难分辨其中多少是历史事实,多少是恶意捏造。如果我们相信琉善的说法,亚历山大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招摇撞骗的成功案例。佩雷格里努斯则是一个复杂得多且有趣得多的人物,在琉善的笔下,他有着不同寻常的职业生涯。
佩雷格里努斯出生于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译者注:今天被称为达达尼尔海峡)旁的帕里昂(Parium),家境殷实。年轻时,他因不光彩的情感纠葛,以及与父亲的争吵惹上麻烦,并在涉嫌勒死父亲的情况下离家出走。在巴勒斯坦,他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一名先知和社区领袖;他阐释经文,并撰写了大量著作。作为一名基督徒入狱后,他因坚决不放弃信仰而声名大噪,但最终被一位开明的总督释放。接下来,他自愿回到家乡面对弑父的指控,但他将全部财产捐给城镇用于慈善事业,这令指控者哑口无言。他曾一度得到基督徒的支持,但后来与他们发生争执,并被逼迫到试图索回财产,不过没有成功。之后他去到埃及,在那里他鞭笞自己,用泥巴涂脸,并以最落魄的方式过着犬儒式的生活。从那里,他又去了意大利,在那又因侮辱皇帝而被驱逐;他这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态度再次为他赢得了仰慕者。接下来,他又在希腊定居,在那里他试图发动一场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并公开侮辱慈善家赫罗狄斯·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最后,他以惊世骇俗的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公元165年的奥林匹克节庆期间,他在一群仰慕者面前自焚身亡。随后,他成为一个教派崇拜的对象:他生前携带的手杖以一塔兰同(talent,译者注:古罗马的货币单位,一塔兰同等于6000第纳里)的价格出售;为纪念他而竖立的雕像能够行使奇迹(据一位基督教作家的说法),并吸引了大批朝圣者。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段非凡的人生故事呢?尽管我们不必接受琉善对它们的解释,其中的主要事件还是可能是属实的。琉善会用一种病态的对沽名钓誉的追求来解释从头到尾的所有事情;从他那里,我们或许应该接受的是,佩雷格里努斯除了其他特质以外,确实还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事实上,我们可能禁不住会认为他多少有点疯癫。然而,他生活在希腊时与他相识的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却发现他是“一个严肃且坚定的人”,“有许多有益且发人深省的话要说”;甚至连琉善也证实他被认为是“第二个苏格拉底”或“第二个爱比克泰德”(显然是出于道德而非哲学上的理由)。这或许可以鼓励我们比琉善更深入地探究他的性格。一个可能的线索就隐藏在终其一生都悬在他心头上的那个骇人听闻的指控——弑父。他先是逃避了这一指控,然后又回来面对了它;在他那句出人意料的遗言中——“母亲和父亲的灵魂啊,请你们仁慈地接纳我吧”——他必然回忆起了这段往事。我们不必相信这一指控确有其事,但某些记忆对他来说无比沉重,这不仅反映在他的遗言中,也反映在他在雅典的传道中,奥卢斯·格利乌斯听到了那次讲道,其中心主旨是:“你的秘密罪行终将被揭露”。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比琉善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一生中的两个显著特点——他对权威的敌视态度以及他成为殉道者的决心。不论值不值得一提,我倾向于猜测这两种性格特征都源于他早年与父亲不幸的关系:他必须反抗叙利亚总督、安敦宁·毕尤(Antoninus Pius)以及赫罗狄斯·阿提库斯等人表现出来的父权作风;作为一个严格的平等主义者,他必须蔑视一切传统习俗;但他也必须通过贫穷、鞭笞,最后以死亡来惩罚自己,因为他伤害了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父亲形象。
如果我的看法正确,们就必须把佩雷格里努斯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非一种类型。无论如何,我们几乎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作为基督教先知的那一面:琉善对基督教习俗知之甚少,而且并不关心。如果我们想对基督教的“先知式”话语形成一些概念,我们最好转向那些被归属于蒙塔努斯(Montanus)的言论,尽管同佩雷格里努斯一样,他最终也被教会排斥,而且在他的案例中,关于他的确切情况,我们也(与佩雷格里努斯一样)主要依赖于对其带有敌意的文献资料。蒙塔努斯是一个弗里吉亚人(Phrygian),据说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他曾是阿波罗或大地之母(Magna Mater)的祭司;但他的预言似乎与他的弗里吉亚出身关系不大。大约在公元172年左右,一个并不属于蒙塔努斯本人的声音开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通过他说话。它说:“我是全能的主上帝,此刻居住在一个凡人的体内”;又说,“这不是天使,也不是人类发言人,而是主,是天父。”这个声音进一步解释了这是如何可能的,它说:“看,人就像一把竖琴,我像拨片一样弹奏他:当人睡着时,我是醒着的。看,这是主,他拿走人的心,并给他们放入其他的心。”当然,蒙塔努斯不是在声称自己是上帝,就像现代灵媒也并不会声称自己是孔子或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Myers)一样;是那个外来的声音提出这样的主张。而且这个声明是以传统的比喻做出的:那哥拉(Athenagoras)和《致希腊人的劝告》(Cohortatio ad Graecos)都使用了同样的音乐比喻。不久之后,这个声音开始通过两个女性灵媒(马克西米拉(Maximilla)和普里西拉(Priscilla))说话——预言是会传染的。这些预言都被记录了下来,信徒们认为它们构成了《第三圣约》(译者注:这显然是相对于《旧约》与《新约》而言)。
这部《第三圣约》仅保存了少量残篇,不得不承认,像大多数来自彼岸的信息一样,这些残篇极其令人失望。可能是像伊皮法纽(Epiphanius)这样的批评者并未选择最具有启发性的片段来引用;但我们应该期望特土良(Tertullian),一个蒙塔努斯派的皈依者,向我们展示是什么使他皈依了,而他几乎可以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第三圣约》的主要启示是,新耶路撒冷很快将从天而降,基督在人间的千年统治将开始。当然,基督教预言长期以来一直与千禧年的希望联系在一起:先知们保持了这种希望的活力,而这种希望也维持着先知们的存续。但是,正统的基督徒期待天国之城出现在巴勒斯坦,而蒙塔努斯则以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坚持认为,上帝为它指定的地点是弗里吉亚的一个偏远村庄——佩普扎(Pepuza),所有虔诚的基督徒都应该在那里等待。至于其他方面,正如格林斯莱德教授(Professor Greenslade)所说,“圣灵似乎没有对他的先知们说过任何具有宗教价值或认知价值的东西”。显然,蒙塔努斯只满足于斥责主教们的懈怠,并对被神选中的人群施加一些额外的严酷戒律;根据特土良的说法,他甚至去关心一些琐事,比如:未婚女子佩戴的面纱应该有多长才叫适当。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为成功的“媒介”,自然而然地,蒙塔努斯给予女性的地位远胜过正统基督教所允许的程度——一位女先知甚至在幻像中看到了基督以女性的形象出现。但他最引人注目的创新似乎是一个实际的做法:他似乎是第一个为他的传教士定期支付薪酬的先知。
主教们被蒙塔努斯的批评激怒,并且不愿意承认《新约》之后还有任何新的圣约,于是对他的回应是:开除他的教籍并试图驱逐附身于他的追随者们身上的邪灵。但蒙塔努斯主义没有那么容易被主教们或者他本人的失败预言(关于天国之城将会降临佩普扎)而扼杀。从弗里吉亚开始,它传播到了整个东部,然后传到罗马、北非,甚至远至西班牙。尽管马克西米拉曾宣布,“在我之后,将不再有先知,而是世界的末日”,预言却依然继续。特土良认识一位“与天使甚至有时与主对话”的女性,并且她还见过以身体形态出现的人类灵魂(这让特土良满意地找到了灵魂具有物质性的证明)。一代人之后,西普良(Cyprian)知道有几个孩子不仅在睡梦中,而且在清醒的出神状态中,也得到圣灵赐予的视觉和听觉启示。我们还听说,有一位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n)的女先知,她在公元235年后就开始自行主持圣礼,声称能够引发地震,并提出要带领上帝的子民返回耶路撒冷:从费弥里(Firmilian)的记述来看,马克西米努斯·戴亚(Maximinus Daza)统治下重新开始的迫害,再加上自然灾害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相结合,似乎重新点燃了对千禧年的期望。在君士坦丁大帝获胜后,这样的期望显得不合时宜,但蒙塔努斯主义在其发源的根据地内一直持续到第四和第五世纪。阿卡狄乌斯(Arcadius)下令焚毁蒙塔努斯派的书籍并镇压他们的集会;但直到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统治时期,最后的蒙塔努斯派信徒才将自己锁在教堂里,自焚而死,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落入他们的基督教同道手中。
蒙塔努斯主义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圣灵对依纳爵(Ignatius)低语的睿智忠告中已经预示了:“没有主教的同意,不要做任何事情。”特土良徒劳地抗议说教会不是主教的集合体;爱任纽也徒劳地恳求不要驱逐先知。从等级制度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已经失去了他原始的功能。他在《新约》中根深蒂固,已经无法再被降级,但他在教会的决策中实际上已经不再发挥任何明显的作用。原本由受启示的先知说出神的话语的古老传统,被更方便的观念所取代,即神会持续地,在教会中的重要成员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给予他们指引。预言转入地下,后来在中世纪晚期的“千年王国狂热”(chiliastic manias)中,以及随后的许多福音运动中重新出现: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将会把蒙塔努斯看做是一位志同道合的人,他认为蒙塔努斯是“公元2世纪最圣洁的人之一”。有了这个墓志铭,我们可以让他安息了。
第三章:人与神明的世界
我曾游历于多姿多彩的世界,如今已安居在永恒的中心;那是我被孕育的子宫,也是我的欲望如今归向的地方。
我在第二章中讨论的经历属于边缘经历:它们的宗教地位也模棱两可——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它们为“灵性的”(daemonic)。在我们的文化中,幻视和幻听通常被视为疾病的症状;梦也不再被视为是神与人之间的交流渠道,而是人心理中无意识与有意识部分之间的交流。这类现象在某些个人和某些教派的宗教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们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它们充其量属于宗教病理学的范畴。现在,我打算举例并讨论某一类新的经历,其性质确实是模糊和难以界定的,但其宗教特性和宗教重要性却被普遍承认。
在本章将要考察的所有信仰和体验,都属于一种被笼统地描述为“神秘主义”的类型。但是,“神秘主义”(mysticism)是一个太过于模糊的术语。为了本章的需要,我将采用拉朗德(Lalande)在他的《哲学词典》(Vocabulaire de la Philosophie)中给出的严格定义:神秘主义是“相信人类精神有可能与存在的本源(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being)进行亲密而直接的联结,这种联结同时构成了一种存在模式和一种认知模式,它不同于正常的存在和认知且优于后者。”认为这种联结可能的人,我称之为“神秘主义理论家”;相信他们自己已经体验过它的人,我称之为“神秘主义实践者”:第一类人当然包括第二类人(译者注:此处疑为笔误,应该是第二类包括第一类),但反之则不然。如果我们这样定义我们的术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将下面两种情况区分开来:一种是具体的神秘主义理论和体验,另一种是那些只能在宽泛而非严格的意义上被称为“神秘主义”的体验。在讨论这段时期的宗教现象的著作中,围绕这个话题存在许多混淆。
一个常见的混淆的来源是希腊文中的词语“ekstasis”。由于在中世纪神秘主义的文献中,“ecstasy”(狂喜)是描述神秘联结状态的标准术语,因此很容易将这个含义倒推回到它的希腊词源中。但实际上,“ekstasis”及其关联词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在古典希腊语中,它们用于描述任何偏离正常状态的情况,任何突然的心理或情绪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更具体的含义。它们可以表示敬畏或惊愕的状态,例如当耶稣与医生争论时,旁观者们“existanto”【感到惊讶】。它们可以表示歇斯底里或精神错乱,就像在亚里士多德和医学作家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它们还可以表示被神灵或恶魔附体,前者就如《旧约》先知的情况,后者就如俄利根对阿波罗女祭司(Pythia)的解释,这种用法从斐罗开始就很常见。在这些含义中,“ekstasis”都与神秘联结无关。斐罗用于解释希伯来先知的“ekstasis”有时被错误地与之混淆,这一点从斐罗对这种“ekstasis”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说:“当神灵降临时,我们自己的心灵会被逐出家门,当它离去时又被恢复原状;因为凡人和神明不能共享同一个屋檐。”这不是对神秘结合的描述;它所描述的是一种暂时的“附体”状态,即如今所谓的“出神通灵”(trance-mediumship)。是超自然的精神体降临到人的身体上,而不是人自己提升或被人提升到身体以外的状态。据我所知,这个词最早被用于表示严格意义上的神秘体验是在普罗提诺的一句名言中,其中神秘的联结被描述为“一种‘ekstasis’,一种对自我的简化和舍弃,一种对于接触的渴望,同时,既是一种心如止水的状态,又是一种为了适应它而在精神层面付出的努力”。很显然,这种对“ekstasis”的使用源自普罗提诺,再经过贵格利,最后传到了基督教神秘主义那里。
让我再举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词语的例子。“我即是你,你即是我”这个公式常被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用来表达灵魂与其神圣源头的同一性:例如,13世纪的安吉拉(Angela of Foligno)认为她听到基督对她说:“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现在,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中或者更早一点,有六个这种互为同一的公式的例子;但是它们的含义却与安吉拉的那句话并不相同。例如,我们在一卷魔法莎草纸书中,读到一个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神的召唤,请求他“在魔法师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进入到他的身体中,并执行“他的灵魂的所有愿望”,之后,魔法师宣称“因为你是我,我是你:我说的任何话都必须实现”。显然,这段描述里没有涉及神秘联结:互为同一是通过前面的咒语神奇地诱导出来的;这将持续终生;魔法师诱导它的动机是为了获得个人力量。我们最多只能说,作者可能从宗教来源中借用了一个公式,赋予了它魔法的力量,并为了自己的目的加以利用:魔法莎草纸书经常利用别人的宗教剩下的残骸。更接近安杰拉的说法(至少在表面上)的是诺斯底教派的《皮斯蒂斯·索菲亚》(Pistis Sophia,译者注:这本书的标题同时是书中主角的名字,但是“Pistis”在希腊文中的最初含义是“信仰”,后来引申出其他含义,包括“确信”,“悟性”等等,“Sophia”最初的含义是“智慧”)中的一段,其中耶稣对真正的诺斯底派信徒说:“那个人即是我,我即是那个人”。但这个公式最有趣的例子出现在智蛇派(Ophites,译者注:早期基督教历史中出现的一个属于诺斯底派系中的教派,该宗派崇拜《旧约》中引诱夏娃吃善恶果的那条蛇)的《夏娃福音》(Gospel of Eve)中,其中一个“雷声”说,“我即是你,你即是我: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的存在遍布于万物之中:无论你想去到哪里,你就在哪里聚集我,在汇聚成我的同时,你也在汇聚成你自己。”这不是安吉拉或普罗提诺使用的语言;但这确实像是外向型或泛神论式神秘主义的语言。我将回到这个主题;但我必须先讨论另一种容易与神秘联结相混淆的体验模式。
这就是被称为“神化”(divinisation)(θεὸς γενέσθαι θεοποιεῖσθαι (ἀπο)θεωθῆναι)的体验。人死后可能成为神或精灵的观念当然早已为人所熟知:这种说法经常出现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的异教徒墓碑上。但是,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成为神,正如克莱门特所说的“一个借肉体凡胎行走的神”——若抛开希腊传统和罗马的统治者崇拜的话——对我们来说似乎会显得相当怪异。然而,我们发现这种语言不仅被普罗提诺、波菲利和赫尔墨斯主义者等异教徒反复使用,也被爱任纽和克莱门特、俄利根和贵格利使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当然应该记住,在多神论信仰的社会中,“theos”【希腊文的“神”】这个词并没有像“上帝”这个词那样令我们产生压倒性的敬畏和遥不可及的感觉。在希腊的民间传统中,神与人的主要区别在于神不受死亡的限制,以及这种豁免所赋予他的超自然力量。因此,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凡人是会死的神,而神是永生的凡人”;也因此,如果一个人似乎展现出超自然力量,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神,据说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Lystra)遭遇的就是这种情况,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的几次遭遇也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哲学家们为成为神又增加了另一个条件——即完美的善。他们说,人应该尽其所能地模仿这种神圣的善。这就是被称为“homoiosis”的学说,即“向神同化”(assimilation to God),最初由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提出,并不断被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的——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柏拉图主义者们呼应。这是一种道德而非神秘主义的教义:同化并不等于同一。然而,它将神我同一作为一个理想目标,因此普罗提诺可以说,好人的最终目标不是消极地避免罪恶,而是积极地成为一个神,克莱门特则可以说,这样的人“练习成为神”。在这样的段落中,“神化”似乎只不过是同化在理论上能达到的极限情况:因此,它可以用它来描述理想化的智者,正如波菲利所说,智者将通过“与神相似”来“神化自己”。大概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正统的天主教神学家们才能够谈论“神化”。他们能在《创世记》第1章第26节和《诗篇》第82章第6节中找到这一理念的经文依据。
但是,在异教徒和基督徒的作品中,也有其他一些段落,其中的表达乎意味着一种实际的身份改变,即由神格取代人格,这种改变或是通过魔法仪式实现,或是通过神恩行为实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如费斯图吉耶尔所展示的,这正是《赫尔墨斯文集》中第十三篇短论的要义:它描述了一种重生的经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神和神的儿子,万物皆是如此,由进入其体内的一切神圣力量组成”。这无异于神灵在真正意义上侵入了人的躯体,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与斐罗的“ekstasis”相比较,也可以将它与我们在第二章考察的神灵附体的例子相比较,但它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由此产生的状态是永久性的。赫尔墨斯主义者和克莱门特都教导说,重生者从此以后便是无罪的。对于赫尔墨斯主义者来说,“重生”似乎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授秘密知识的仪式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神恩;可对于克莱门特来说,它依赖于洗礼加上教育再加上恩典;一些基督教诺斯底教徒认为它需要一种特殊的仪式,即第二次洗礼,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获得奥义(gnosis,译者注:在古希腊文中,它表示一种神秘高深只能通过灵修而获取的终极知识,“诺斯底”这个词就是源自它,这种哲学流派认为凡人有可能直接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这种知识)本身就足够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潜在的心理事实似乎是改宗现象,有一种信念总是伴随着它,即过去的一切都被抹去了,以及罪恶的欲望也都神奇地消失了——至少暂时是如此。如果改宗是突然发生的,并且是彻底的皈依,那么主体会觉得自己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存在层次:正如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所表达的那样,意识形态的重大改变需要身份的重大改变。我们在上一章中注意到一些暗示身份危机的迹象:“这是阿里斯提德斯的雕像还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雕像”?“这是蒙塔努斯自己的声音还是那个借用蒙塔努斯说话的声音”?同样,一个人可能会问:“我还是我昨天那个感到不安全和有罪的我吗?难道我不是一个全新的存在,重生为一个安全和无罪的人吗”?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人可以通过内化强大的父亲形象来解决他的危机。从此以后,他便可以像亚当派(Adamites,译者注:在公元2至4世纪出现在北非的一个基督教派系,信徒在宗教仪式中赤身裸体)那样,向“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我们的父”祈祷。
应该明确的是,我一直在讨论的现象与神秘联结完全不同,神秘联结是一种短暂的体验,即使会再次出现,通常也要在很长的间隔后,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再出现。普罗提诺确实可以说,在神秘联结时,灵魂“变成了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神”;但这不是克莱门特或赫尔墨斯主义者所说的“神化”的含义。诺曼·科恩(Norman Cohn)在论及晚期中世纪神秘主义时很好地阐述了这种区别。他先是引用了14世纪的小册子《凯瑟琳姐妹》(Schwester Katrei)中的一句话:“基督使我与他平等,我永远不会失去这种状态”,然后他继续说道:“将这种体验与那些伟大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的体验区别开来的鸿沟当然是巨大的。”教会认可的神秘联结是一种短暂的启示,只是偶尔发生,也许一生也就只有一次。无论它可能释放出怎样的能量,无论它可能给予怎样的保证,经历过它的人并没有因此摆脱其凡人的状态;他仍然必须以一个普通凡人的身份继续过完他的尘世生活。另一方面,异端的神秘主义者则感到自己彻底转变了;他不仅与神合一,而且他就是神,并且将永远如此。”如果我们将其中的“伟大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替换成“普罗提诺”,将“异端神秘主义者”换成“某些赫尔墨斯主义者和基督教诺斯底派教徒”,这种区别将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时期。诺斯底教派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召唤神的降临,普罗提诺也坚决反对这种狂妄自大的主张。对他来说,神对所有的存在都是临在的,而能够意识到这种临在的能力是一种“所有人都拥有,但很少有人使用”的能力(1,vi,8.24)。他对诺斯底教派说:“如果神不在世界中,那么他也不在你们体内,你们就没有任何资格谈论他”(2, ix, 16.25)。
现在我将要集中讨论真正意义上的神秘联结,它是一个艰涩的主题。在这个议题里,也有必要作出一些区分。在最近出版的两本重要著作中,罗伯特·查勒(Robert Charles Zaehner)教授的《神圣与世俗的神秘主义》(Mysticism Sacred and Profane)和瓦尔特·斯泰斯(Walter Terence Stace)教授的《神秘主义与哲学》(Mysticism and Philosophy),作者都试图建立一种神秘主义的形态学。两位作者使用不同的术语并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他们一致同意区分两种主要的体验类型,即外向型(查勒称之为“自然神秘主义”)和内向型。下面我引用斯泰斯的定义:
外向型体验通过感官向外求索,而内向型体验则向内探入心灵。两者最终都通达一种对终极统一的感知,感知者在这种统一中意识到自己与之联结甚至同一。但是,外向型神秘主义者使用他们的生理感官,去感受外在物质对象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多样性能够折射出神秘地转变其面貌的“太一”(the One),或者“统一体”(the Unity)。相反,内向型神秘主义者则通过刻意关闭感官……潜入自己内心的深处。
关于斯泰斯的观点就论述至此。我认为,一个人能够在这两种模式中的哪一个中找到统一体,这一部分取决于个人气质,还有一部分取决于文化因素。从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我们讨论的这个时代的主要趋势更倾向于内向型而非外向型的方法。有一种“宇宙乐观主义”的潮流,即在可见宇宙面前油然而生的一种敬畏情愫,它起源自《蒂迈欧篇》,并被所有斯多葛学派或多或少地传承,它开始逐渐消退,尽管从未完全消失,而相反的“宇宙悲观主义”潮流则在稳步增强。在马可·奥勒留那里,一种对事物神圣有序统一的古老感觉依然鲜活而且有力,比如他说道,“一个包含一切的世界,一个渗透一切的神,一种实质和一个法则”。他提醒自己与它的统一:“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神,是神性的漫溢”;将自己与神之城割裂的人就像自然之母的面庞上的一个叛逆的毒瘤。但这些都是传统的思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个人的神秘体验。他所反复强调的退回到内在生活的需要,退回到“那个小小的自我领域”,这些都更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征。他说:“向内挖掘”;“善的源泉在内心,只要你不停挖掘,它就会随时冒出来。”有一次他甚至胜利地宣称:“今天我摆脱了所有的境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驱逐了所有的境遇;因为它不在我之外,而是在我内心的想法中。”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普罗提诺:当马可的外在自我有效地与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作战时,他的内在自我却在进行一场内心的旅程。然而,我甚至还是不愿称他为“神秘主义理论家”。他只是关注如何使自己从对外部世界的情感依附中解脱出来。马可可以说“善的源泉在内心”,但还不能像普罗提诺那样说“一切都在内心”。对他来说,无论外部世界多么令人反感,它仍然是坚实且不可穿透的。
更能体现外向型神秘体验的是我从诺斯底教派的《夏娃福音》中引用的那段话。我将把它与《赫尔墨斯文集》中第十一篇短论中诺斯(Nous)对赫尔墨斯说的一段话作比较:
若你不使自己同等于神,便无法领悟神,因同类方能领悟同类。超越一切形体,将自己扩展至无边无际;超越所有时间,化身为永恒:如此,你方能领悟神……将万物之感官融入己身,无论火与水,无论干燥与湿润;同时存在于海陆空;既是无生,又在母腹,既是年少,又是垂暮,既是死亡,又超越死亡;若你能将这一切融于思绪,时空与物质,质量与数量,那么你便能领悟神。但若你以将灵魂囿于肉身而贬低灵魂,若你说“我一无所知,我一事无成;我畏惧海洋,我无法攀天;我不知我过去为何,亦不知我未来将何”,那么,你与神何干?
这究竟只是一段华而不实的话术,还是对德国人所说的“共情”(Einfühlung)的一种认真的演练(实际上是一种外向的神秘主义实践)呢?作者是否经历过类似阿尔斯特小说家福雷斯特·里德(Forrest Reid)所描述的那种体验呢?在那种体验中,“仿佛一切看似外在和围绕着我的事物突然间都进入到我之内。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我之内。树木在我之内摇曳着它们的绿枝,云雀在我之内歌唱,烈日在我之内照耀,阴影在我之内清凉。”这便是赫尔墨斯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境界吗?对此我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只能引用费斯图日勒在他关于赫尔墨斯文集的伟大著作结尾所说的话,“历史学家只知道他被告知的内容;他无法洞察心灵的秘密。”
但无论如何,将这段赫尔墨斯的文字与普罗提诺所规定的一种练习进行比较是很有启发性的。普罗提诺说:
每一个灵魂都应该思考这一点:正是她自己创造了所有有生命的事物,向它们注入生命的本源;陆地和海洋所孕育的生物,空中所有的生物,以及天堂中神圣的星辰,都是她创造的;太阳是她创造的,这个巨大的穹苍是她造就的;除了她,没有谁能为它赋予秩序,除了她,没有谁能让它在指定的轨道上运行;然而,灵魂本身却不同于她所装扮、驱动和赋予生命的一切事物。
这两段文字都源于对所有生命的统一性的相同感受;两者都认可了自我可以无限扩展这一悖论。但是,赫尔墨斯主义者满足于将自我等同于自然(Nature)的各个方面,而普罗提诺则将其等同于自然背后的因果力量。这还不是全部:对赫尔墨斯主义者来说是最终成就的事情,对普罗提诺而言只是升华的开始。从对自然的观照,我们必须转向对“可理解的宇宙”的观照,每个人的自我中都映射着这样一个由纯粹关系构成的网络(译者注:这个“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指的是完美的、抽象的理念或理型之间的关系,“理念”、“理型”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在这个网络的核心,我们必须发现“旋转世界中的那个静止点”,即最内在的自我,它很可能就是普罗提诺所说的那个无名力量源泉,他称之为“太一”(the One)、“善”(the Good)或有时称为“神”(God)。对普罗提诺来说,灵魂的旅程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它将到达的不是别处,而是它自身”。他的座右铭是“万物皆在我们之中”(“Panta eiso”,译者注:希腊原文是“Πάντα εἴσω”,“πάντα”的含义是“一切事物”,“εἴσω”的含义是“在……之中”):如果我们希望认识终极真实(the Real),我们只需向内审视自己。换言之,他是内向型神秘主义者的完美典范。
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内,在如此多的文字记载中,只有他和他的学生波菲利两人被明确记录曾经体验过神秘联结。据波菲利所说,在两人共事的六年里,“普罗提诺通过冥想和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指出的方法,曾四次将自己提升到了原初和超凡的通神境界”;波菲利本人也在许多年后达到了同样的境界,但仅此一次。我们还有普罗提诺自己的记述,在一段独特的自传性的段落中,他提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从自己的身体中觉醒,再进入到自我,外在于所有其他事物,而又内在于自我,我看到了一种奇妙的美,我从未像那时那般确信,我属于更崇高的层次,那时我积极地享受着最高贵的生活方式,那时我与神合一并永固其中”。在其他地方,普罗提诺用令人难忘的散文至少描述了——纵使不是神秘联结本身——通向神秘联结的步骤。他告诉我们,当我们通过智识和道德的自我训练获得了适当的心性后,我们必须进行一种摒弃的修炼:我们要摒弃世界在物质层面的浑浊,摒弃时空的参照系,最终甚至要摒弃内在的关系网络。剩下的还有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有剩下,除了一个潜在的但尚未实际成为绝对精神(the Absolute)的意识中心。
这种体验的最后阶段并非由任何意志驱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达成,普罗提诺说:“我们必须静静地等待它的出现,并做好去观照它的准备,就像眼睛等待日出一样。”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能真正用视觉或任何正常的认知行为来描述;因为主体和客体的区别消失了。我引用普罗提诺对此的一次描述尝试:
灵魂突然看到神在其内部显现,因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它们不再是两个,而是合而为一;这种状态持续时,你无法区分它们。这就是肉体上的情爱(当渴望与对方融为一体时)所效仿的那种结合。灵魂不再意识到自己处于肉身之中,也不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是人或是生物,事物或万物的总和…因为看见神的灵魂在那一刻无暇他顾。在这种状态下,灵魂不会为了世间的任何东西而放弃当前的状态,即便是给它一个统领了所有天界的王国也不会:因为这就是“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这段描述与许多其他神秘主义思想家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所注意到的有许多共同的特征。退隐到自我之中,以及为了让神能够充满自我而将自我清空;对安静和被动的需求;个人身份感的消失;突然而又强烈的彻底的满足感;意识到这种体验与其他任何体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并因此难以言传——从古代印度到现代美国,所有这些都被反复描述过,而且用的都是大致相同的术语。在我看来,无论给它帖上多少不同的注解,也无论它(被认为)所印证的各种神学彼此有多么不相容,从心理学的层面讲,在所有地方对它的描述都指向同一种体验。
在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中,带有鲜明的普罗提诺特色(也许我们应该说,鲜明的希腊特色)的,不是体验本身,而是他获得这种体验的方法和他对这种体验的解读。他的方法是高度智力性的,而不是像一些东方教派那样是生理性的,也不像某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那样是仪式性的。他没有规定呼吸练习、肚脐冥想或对神圣音节的催眠性重复;也不需要仪式来触动这种体验。在他偶尔推荐的纯粹心理练习中,他依赖于三个传统的认知神的方法:否定之道(也许起源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类比之道(基于柏拉图关于太阳和善的类比)以及飞升之道(基于柏拉图《会饮篇》中向绝对美的升华)。这些方法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被阿尔比努斯(Albinus)列出。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波菲利的记述,普罗提诺是通过最后一种方式实现了他个人的神秘联结体验;但在他的教导中,他也自由地使用了其他两种方法。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普罗提诺不会同意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观点,即“对于一体性思维(integral thinking,译者注:在这里,它并非是指任何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玄学式的认知方法,即认为人的灵魂与宇宙、存在本源或万物源头有某种联结,一切都是一体的,有一点接近中国儒家的天人感应)的直觉而言,分析性思维(analytical thought)的习惯是致命的”。相反,对普罗提诺来说,分析思维的习惯是一种必要且有价值的训练,是心灵必须进行的一种“净化”(katharsis),在尝试赫胥黎所谓的“一体性思维”和普罗提诺所谓的“领悟”(noesis)之前,心智必须进行这种训练。对他来说,就像对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沉思者的训练应该从数学开始,进而到辩证法:神秘联结不是智力修行的替代品,而是其巅峰和目标。它也不是道德修行的替代品,因为在某些诺斯底教派中,可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没有真正的美德,所有关于神的讨论都不过是空谈”。想要获得这种体验的人必须是道德上的艺术家:“他必须不断地雕琢自己的形象,剥离所有多余之物,纠正所有扭曲之处”,直到没有外物混入纯净的自我,阻碍其统一。
比起正统的基督教观点,普罗提诺对于这种体验的解读更接近某些印度神秘主义者。首先,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自然事件,而非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理论中那样是一种超自然的恩典。它的自然根源在于灵魂与其神性本源的潜在同一性,以及万物倾向于回归其源头的普遍法则。这是对某种只待被实现的潜能的现实化,是对永恒事实的瞬间启示。普罗提诺说:“太一始终在场,因为它不包含他性;但只有当我们摆脱他性时,我们才在场。”他还补充道:“太一并不渴望我们,使我们成为它的中心;但我们渴望它,将它实现为我们的中心。事实上,它一直都是我们的中心,只是我们并不总是将目光聚焦在这个中心上。”这是普罗提诺对神秘联结的描述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就像在他的体系中,所有较低层次与较高层次之间的关系都是单向的、没有互动的。灵魂体验到对太一的爱欲(eros),可以说,就像亚里士多德的神一样,通过作为世界欲望的对象来推动世界运转。但“太一”不能体验欲望,因为欲望是不完整的标志;被创造的生物,即:果,不能反过来影响其因。普罗提诺多次明确地告诉我们,“太一”不需要它的产物,即使它没有这些产物也不会在意。他确实可以称之为“爱欲”(Eros),但仅限于“自爱”(amor sui)的意义上。如果我们能在普罗提诺那里找到任何类似“恩典”的东西,那也只是建立在神性在所有人中永久存在的意义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不懈努力在罕见的情况下有意识地体验到这种存在。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在基督教神学甚至许多异教作家那里遇到的个别恩典行为的概念。但我要重申,这仅仅是解读上的差异。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正如某些天主教作家所做的那样——这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例如,查勒教授告诉我,虽然一元论神秘主义者(monistic mystic)“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解脱,而在有神论的神秘主义者(theistic mystic)那里,总是上帝先迈出第一步”,我不禁怀疑他这是将对于这种体验的神学解释强加到体验本身之中。
这不是探讨普罗提诺独特神学的来源或评估其宗教价值的地方。我们只需说明,他认为自己在柏拉图那里找到了这种神学的依据,而事实上,其大部分要素散见于公元2世纪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中,尽管还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体系。对我当前的目的来说,更切合的问题是:普罗提诺的神秘体验是否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种异于常人的人格结构的偶然产物,或者,它会不会是一种迹象,告诉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独立于普罗提诺斯的作家身上也能找到内向型神秘主义倾向。在寻找答案时,我们应该记住,神秘体验并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它在强度和完整性上允许很大程度的变化。既然如此,就应该首先指出,中期柏拉图主义思辨开始重新重视对神的个人求索。
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与犹太人德理夫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见证,描述了作者在寻找神的过程中,起初试图从斯多葛派、亚里士多德派和毕达哥拉斯派那里了解神,但都没有结果,最终他参加了一位柏拉图主义者的讲座,后者至少给了他亲眼见到神的希望,他说,“因为这是柏拉图哲学的目标”。事实上,似乎正是游斯丁那个时代的柏拉图主义者们阐述了我刚才提到的认知神的三种途径的学说——这一学说后来在中世纪被基督徒纳入到基督教哲学中。我们不仅在阿尔比努斯对柏拉图的系统化的整理中看到了这一学说,它在塞尔修斯那里也以不同的术语出现,而马克西姆斯则以更通俗的形式阐述了它。对于普通人来说,“哲学”一词越来越多地意味着对神的求索:正如赫尔墨斯派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作者所表达的,“哲学仅仅在于通过习惯性的沉思和虔诚的奉献来学习了解神明”。在马克西姆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已然形成的内省式沉思练习的传统。我们要“堵上耳朵,将视觉和其他感官转向内在的自我”;这将使我们能够借助真正的理性和激情的欲望(逻各斯和爱欲)的翅膀飞向天外的宁静之地。马克西姆斯说,“剥去其他的外衣,在心中消除对视觉的依赖和它带来的外界干扰,在剩下的东西中,你将看到你真正渴望的对象。”
这听起来非常像普罗提诺的语言,但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神秘体验。费斯图日勒说得很对,这种教义的根源在于对柏拉图某些段落的玄学化的解读——《斐多篇》中关于灵魂退隐的教导,《会饮篇》中的飞升,《斐德罗篇》中的神话,以及《第七封信》中关于灵魂中被点燃的火花。我们或许可以在努米尼乌斯的一个片段中察觉到一种更个人化的语调,这位公元2世纪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的作品在普罗提诺的学园里被阅读,而普罗提诺还被指控剽窃他的思想。努米尼乌斯将沉思者比作站在高处的守望者,瞭望着空寂的海面,突然看到一叶孤舟:“同样地”,他说,“一个人必须远离感官事物,进入与“善”的孤独交流之中,在那里,没有人类,也没有其他任何生物,或大小形体,只有某种无法言说或描述的神圣荒凉,“善”在那里出没,在那里栖息,在那里绽放光辉,“善”本身在和善中休憩,至高的本源在现实的波涛之上平静地行驶。”正如我在别处试图指出的那样,普罗提诺在很多地方回应了这段非凡的文字,我认为可以合理地假设,他将其理解为对神秘联结的描述。我们知道,努米尼乌斯主张灵魂与其神圣本源(archai)的“不可区分的同一性(indistinguishable identity)”;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灵魂在某种意义上都包含着“可知世界(the Intelligible World)、诸神和亚神、‘善’,以及所有形式的先天存在”。这是普罗提诺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普罗提诺是从努米尼乌斯那里继承了这一理论,那么至少有可能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实践方法。
我想顺便请读着注意普罗提诺和犹太神秘思想之间一个奇特的联系。在他最早的著作《论美》中,普罗提诺将灵魂为神秘联结做准备而进行的“剥离”(stripping)比作那些进入“神庙圣所”的人必须“脱掉先前所着的衣服”的做法。评论家们没有注意到,同样的比喻也出现在斐罗的著作中。在谈到将肉体的激情从灵魂中剥离时,斐罗说:“这就是为什么大祭司不会穿着圣袍进入至圣所,而是脱去灵魂的观点和意象的外衣……以不带任何色彩和声音的状态进入”。虽然普罗提诺避免使用具体的犹太术语,但想法是相同的。但如今没有人认为普罗提诺读过斐罗的作品;我们倒也不必这么认为。克莱门特保留的一段来自一位瓦伦丁派作者的文字提供了线索,让我们看到直接启发了普罗提诺的源头的特质。那里说,犹太大祭司进入至圣所象征着灵魂进入可知世界:正如祭司脱下他的仪式长袍,灵魂也使自己赤裸;作者说,“人类,成为神的载体,直接受到主的塑造,仿佛成为他的身体”。这段文字超越了斐罗:大祭司的行为现在被明确解释为神秘体验的象征,正如在普罗提诺那里一样。这可能就是普罗提诺的来源:他与诺斯底教派最终决裂后写的《驳诺斯底主义者》似乎显示出他对瓦伦丁派教义相当熟悉。但我们也可以考虑努米尼乌斯作为一个中间媒介的可能性,因为努米尼乌斯对犹太事物的特别兴趣是有据可查的。
基督教教会内部的神秘主义又是怎样的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很多关于向神同化的讨论,尤其是在柏拉图主义影响强烈的地方,甚至在某些作者中,还讨论到了肉身尚存时的“神化”。克莱门特喜欢将希腊神秘仪式(Greek Mysteries)的传统语言应用于基督教的宗教体验:例如,他常常提到看见神的“幻象”(epopteia),尽管通常语焉不详。《塞克斯图斯格言集》告诉我们,“在看到上帝时,你将看到你自己”,反之亦然,“智者的灵魂是上帝的镜子”:这种表述方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阿尔基比亚德前篇》(First Alcibiades),它被认为是柏拉图的作品,另一个是圣保罗的《哥林多后书》。然而,我们在异教作者中观察到同样的迈向(虽然是在广义上的)神秘主义的总体趋势,但据我目前所读到的,在这一时期中,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位基督教作家明确提到过在现世实现神秘联结的可能。
有时,俄利根被认为是一个例外;但作为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沃尔克(Walther Völker)最多只能证明俄利根有时使用了可以用来描述神秘联结的术语,而这些术语后来确实被其他人这样应用。只有一个来自俄利根的段落被沃尔克声称是对神秘联结的描述,但结果证明它只不过是俄利根在讨论圣保罗的一段话时对它的转述。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论第一原理》(De Principiis,译者注:英文译名为“On the First Principles”)中的一段话,俄利根在其中描绘了一种状态,“心灵将不再意识到神之外或任何不同于神的事物,而是思考神、看见神、持守神,神将成为其每一个动作的方式和尺度。”但这是对最终圆满状态的描绘,它是基于《约翰福音》的一节经文;并且这段话附带着一个警告,即这样的极乐,即使在死后,还没离开肉身的灵魂也不应期待,更不用说生前了。正如达尼埃鲁神父所说,这似乎“是一种理论推测……而不是对神秘体验的描述”。然而,最近亨瑞·克鲁泽尔(Henri Crouzel)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作者的著作中出现如此多后来基督教神秘主义使用的语言,是否很可能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却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实践者。他提醒人们注意俄利根少数几处谈及自己经历的段落之一:在一篇关于《雅歌》的讲道中,他说,“上帝为证,我常常感觉到新郎在接近我,并且他尽可能地与我同在;然后他突然消失,我找不到我所寻求的东西。”他还补充说,这种期待和失望在某些情况下反复出现多次。根据这一证据,俄利根或许应该被归类为一个失败的神秘主义者。当然,他掌握了神秘联结的概念,并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因此,他为贵格利铺平了道路,后者深受其影响,通常被称为第一位基督教神秘主义者。
在这里我不能详细讨论贵格利的神秘主义,况且,无论如何他也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的范围。这个问题从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在我看来,无论在措辞还是想法上,两者都有相似之处,这似乎足以证明贵格利至少读过普罗提诺一两篇较为流行的文章。例如,他和普罗提诺一样,认为灵魂与上帝自然地联结在一起,并将灵魂堕落的状态比作一个浑身是泥的人,必须先洗净污泥才能返回自然状态。但是,当普罗提诺说“他的任务是回到他曾经的样子”时,贵格利默默地做了修正:他坚持认为,回归“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上帝的任务。这种对恩典干预的坚持似乎是区分贵格利的神秘主义与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对神秘联结的描述上,两位作者非常一致,我很难接受达尼埃鲁的观点,即认为这种语言上的共识“掩盖了完全不同的现实”。和普罗提诺一样,贵格利将其描述为从身体中觉醒,或上升到一个守望之地;和普罗提诺一样,它与其说是一种视觉,不如说是对上帝临在的感知;和普罗提诺一样,灵魂变得单纯和统一,并获得光的特质,与它所领悟的事物同一。我认为贵格利经历了与普罗提诺相同的体验;但我还认为他也知道普罗提诺对此的描述,并且借用了他的描述性词汇。在这个程度上,且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神秘主义源于异教。
总结一下。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内,只有普罗提诺和波菲利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但神秘体验有程度之分,普罗提诺式的神秘主义并非孤立现象。公元2世纪的哲学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内向型神秘主义理论的倾向,至少在努米尼乌斯那里,它以暗示实际体验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还看到,类似于外向型神秘主义的东西出现在一部诺斯底教派的著作和一部赫尔墨斯主义者的著作中。如果我们接受“神秘主义”的广义的定义,即所有试图在人与神之间建立心理桥梁的尝试,那么可以说,几乎在整个时期的所有宗教思想中都普遍存在着神秘主义,从马可·奥勒留到普罗提诺,从游斯丁到俄利根,其势头在不断增长。我们也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还是费斯图日勒一语中的:“苦难和神秘主义是相伴的现实”。公元3世纪的世界,在智识上贫乏、在物质上匮乏,并充满恐惧和仇恨,任何能够让人脱离苦海的法门都必然吸引认真求索的灵魂。除普罗提诺外,许多人一定给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那句话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逃回自己的国家吧”。这句忠告可以作为整个时代的座右铭。整个文化,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在进入一个宗教与生活共存的阶段,对神的求索将笼罩所有其他人类活动。
第四章:异教与基督教的对话
单一的道路无法通往如此伟大的奥秘。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讨论的那些态度和经历大多数都是异教徒和基督徒共同持有的——至少是一些异教徒和一些基督徒共有的。但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在我看来,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里,异教和基督教之间没有重要的差异。在这最后一章中,我将谈谈当时文献中所呈现出来的异教徒对基督教的看法以及基督徒对异教的看法。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要全面地讨论它,需要一整个系列的讲座。因此,我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几个首要的主题上;在选择这些主题时,我将较少地关注教义上的争论,而更多地关注那些构成心理分界线的感受差异。
在开始之前,我们应该先明确两点。首先,这场论战是在许多不同的智识层次和社会层面进行的。它吸引了像俄利根和波菲利这样有修养的学者的关注;但它也一定经常而激烈地发生在希腊城市的议事厅、北非村庄的市场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家里。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层面的对话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我们所知道或推测出的内容不应与那些饱学之士的更复杂的对话一起被混为一谈。其次,这是一场持续变动且经年累月的论战。在整个时期,基督教和异教哲学都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我们可以在它们关系的发展中区分出三个阶段。
在这个时期之初,无论是异教思想还是基督教思想,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封闭或统一的体系。希腊哲学正朝着普罗提诺一个世纪后将要实现的宗教融合摸索前行,当时柏拉图主义正日渐盛行,但即便如此,在它的追随者中也还没有多少共识。至于基督徒,根据塞尔修斯的说法,他们分裂成许多相互对立的派系,除了基督徒这个名字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无疑是夸张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权威的基督教信条,也没有固定的基督教经文正典。《穆拉多利残篇》(Muratorian fragment)——通常被认为写于公元180年左右——排除了《希伯来书》(Epistle to the Hebrews),却包括了《彼得启示录》(Apocalypse of Peter);一些罗马的教会成员仍然拒绝接受《约翰福音》,许多人拒绝《约翰启示录》(Apocalypse of John);另一方面,就连俄利根也认为赫马是受到神启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外典福音书、使徒行传和启示录在信徒之间流传[1]。甚至连福音书作者的文本也可能被篡改:马吉安重写了《路加福音》,而克莱门特知道《马可福音》有一个“秘密”版本,他认为这个版本基本上是真实的,尽管诺斯底教派为了他们邪恶的目的而对其插入了一些内容[2]。正统与异端之间的界限尚未明确划分,信徒很容易从一个滑向另一个,就像塔提安(Tatian)从正统转向瓦伦丁主义(Valentinianism),特土良转向了蒙塔努斯主义。如果塞尔修斯有时将基督教与诺斯底教派混淆,正如俄利根所说的那样,很可能许多当时的基督徒也有同样的困惑。
正是在这个时候,与异教的对话开始了。“使徒教父们”只为他们的同道们写作。现在,“护教士”从他们的意识形态隔离区中走出来,首次向受过教育的异教徒陈述基督教的立场——倒不是期望能够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而是希望说服他们停止对基督教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间歇性地方迫害。同样是在公元2世纪后期,一位异教的知识分子第一次严肃认真地对待基督教。对小普林尼来说,这只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行政问题;对琉善,甚至对盖伦来说,这也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好奇;但在塞尔修斯看来,基督教却似乎是对帝国的稳定和安全的真实威胁:他以非凡的先见之明看到教会是一个潜在的国中之国,其持续增长在他看来将瓦解社会的纽带,最终将招致野蛮人的入侵。他在一本名为《真正的教导》(The True Teaching)的书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本书既旨在遏制基督教的传播,也试图劝说基督徒成为更好的公民。这本书被认为是在马可·奥勒留治下出版的,可能是在公元178年左右。如果这个日期是正确的,那么这本书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显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第二阶段从公元203年开始——这一年年轻的俄利根在亚历山大港开始教学,一直延续到公元248年左右——当时年迈的他发表了《驳塞尔修斯》(Contra Celsum)。对于帝国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和苦难加深的时期;对于教会而言,这是一个相对没有迫害的时期,信众数量稳步增长,最重要的是智识水平突飞猛进。克莱门特意识到,如果基督教要在未受教育的群体以外发展,它就必须与希腊哲学和希腊科学达成共识;头脑简单的基督徒不能再“像孩子害怕稻草人一样害怕哲学”;特土良的格言“在基督耶稣之后,我们不需要好奇心”被认为是阻碍有学识和智慧的人皈依的致命障碍。俄利根跟随异教哲学家阿摩尼阿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学习,萨卡斯后来也是普罗提诺的老师。他自己的学生不仅学习哲学,还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的教育计划基于柏拉图的方案,在本质上与普罗提诺的并无不同。从此以后,与异教的对话将成为智识水平相当的信徒之间的对话;事实上,在《驳塞尔修斯》中,俄利根采取了一种智识上带有优越感的口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关于他对柏拉图主义所做的广泛让步,我将在后面详述。
在异教徒方面,这段时期内出现了一些迹象,显示出他们有意愿将基督吸收进现有文化制度之中,就像许多早期的神明被吸收进去一样,或者至少是提出可以考虑和平共处的条件。很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罗马皇帝的母亲尤利亚·玛麦亚(Julia Mamaea)邀请俄利根到她的宫廷;据说她的儿子——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在他的私人小教堂里保存着亚伯拉罕、俄耳甫斯(Orpheus)、基督和阿波罗尼乌斯的雕像,他对这四位非凡的先知给与等同的尊崇。他并非唯一持这种态度的人:大约在同一时期,诺斯底教派的卡普克拉特(Carpocrates)也在宣扬一种类似的兼容并包的宗教——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爱任纽和奥古斯丁的话,他的追随者崇拜荷马、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和圣保罗的形象。塞拉皮翁(Serapion,一个叙利亚人)的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书信也展现了同样的精神,他在信中将基督——“犹太人的智慧之王”——与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作为相似案例并列在一起,他们都是伟大的智者,而他们的教导在遭受了不公正的迫害后仍然流传了下来。波菲利在他早期的《论神谕的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Oracles)中引用了两个赫卡特(Hecate)的神谕,它们可能也属于这一时期。在回答基督是否是神的问题时,赫卡忒回答说,基督实质上是一个极其虔诚的人,但他的追随者误认为他是神,因此犯了严重的错误。波菲利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应该诋毁基督,而应该同情人类的愚昧”。
第三阶段的氛围非常不同。它始于德西乌斯(Decius)在公元249年的迫害,这是第一次系统性地试图通过铲除教会领袖来肃清基督教的行动,如果不是因为德西乌斯在战斗中阵亡,这次迫害或许可能成功。这一阶段结束于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伽列里乌斯(Galerius)统治下的“大迫害”(Great Persecution),这场迫害造成了无数的叛教者,但未能动摇信徒的核心群体,尽管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基督徒被视作不法之徒。在两次迫害中间的间隔期里,即从公元250年至284年间,得益于恶劣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教会在人数和影响力上迅速增长。正是在这个间隔期,大约在公元270年,波菲利撰写了他那本尖刻的《驳基督徒》(Against the Christians),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很多作者仿效这本书,但也引发了基督教方面的许多回应。他在书中表达出了当时所有具有宗教思想的异教徒所感受到的警觉。他说,基督教的教义都已经传播到了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他注意到,在罗马,对耶稣的崇拜正在取代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他还注意到基督徒的自信与财富的新标志——他们正在各地兴建大型教堂。他并没有呼吁迫害;事实上,他似乎对许多因教会的教导而“受到不人道惩罚”的基督徒表示同情。他的继任者们就没有那么顾忌了。希洛克勒斯(Hierocles),著有《热爱真理的人》(The Lovers of Truth)一书,在其中他推崇阿波罗尼乌斯为基督的竞争对手,他也是大迫害的煽动者之一,并且作为行省总督还积极参与了迫害的执行。他不仅体现了异教知识分子与当权体制的联盟,也体现了新柏拉图主义向宗教的转型,这个宗教也拥有自己的圣徒和行使神迹的人。这两者都是对基督教的发展壮大的防御性反应;在尤利安(Julian)皇帝短暂的统治期内,这两者都在更大规模上得到了体现。
自然而然地,这些不断变化的关系也伴随着争论在性质上的某些变化,尽管旧的论点在失去其说服力后仍然经常被重复。至于大众层面的对话,“争论”这个词几乎并不恰当:它主要由谩骂构成。从塔西佗到俄利根,我们能看到的所有权威人士都见证了基督教在异教群众中激起的强烈敌意。塔西佗说,基督徒“因其恶行而被憎恨”;他们被认为是人类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容易地接受了他们应该对大火负责的说法。俄利根带着一丝自豪说,“基督的子民被所有民族憎恨,甚至包括那些住在世界最偏远角落的人。”在公元177年的里昂,如果不是当局干预并用合法的酷刑取代私刑的话,整个基督教社区的信徒就都会被暴民从他们的房子里拖出来殴打致死。似乎很有可能,在公元2世纪,许多地方性的迫害是被民众的情绪所推动,迫使不情愿的地方总督采取行动。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面对匿名举报,其中包含长长的名单,图拉真(Trajan)不失公允地建议他不予理会;在里昂,异教奴隶告发他们的基督徒主人;甚至在德西乌斯开展系统性迫害之前,亚历山大港就已经发生了暴民暴力事件。
为何基督徒如此不受欢迎?除了人性中普遍存在但未被承认的那种需要找人发泄不满的普遍倾向外,证据还指向了其他一些原因。最初,毫无疑问,犹太人长期不受欢迎,基督徒也继承了这一点,似乎他们在异教徒的记录中首次出现时,是被描述为一个与主流有分歧的犹太教派,因一位名为“克雷斯托斯”(Chrestos,译者注:这里指的是耶稣,这个词是“基督”在希腊文中的另一种拼写方式)的人的煽动,与他们的犹太同胞在罗马街头发生了帮派斗殴。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似乎是“无神论者”,对神像和神庙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但是,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因此在宗教事务上,法律允许他们遵循他们祖先的习俗,然而,基督徒是一个由混合族裔组成的新兴教派,则不配享有这种特权。此外,他们似乎构成了一个秘密社团,成员之间通过私人标志相互识别,就像今天的吉普赛人一样,并通过某种神秘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米努修作品中的异教徒说:(指基督徒)“他们是一群躲躲藏藏的人,他们躲避白昼的光明。”当未受洗的人被拒之门外时,他们在紧闭的门后有些什么勾当呢?人们向来对秘密组织持有黑暗的猜疑,针对基督徒的这类猜疑很容易就被激发了出来:据说,他们像公元前186年被镇压的酒神崇拜团体(Dionysiac societies)一样沉迷于乱伦的狂欢,又像喀提林党人(Catilinarians)一样在仪式中食用婴儿。这些想必就是塔西佗心目中的“罪恶”(flagitia)。普林尼认为有责任调查这些指控,但不得不上报说,即使动用酷刑,他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尽管如此,这些指控还是被马可·奥勒留的导师弗朗托当作事实引用,我们从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那里得知,直到公元180年左右,这些指控仍被广泛相信,甚至受过教育的人也相信。所有的护教士都认为有必要回应这些指控,俄利根告诉我们,在他那个年代,这些指控仍然阻碍了一些人与基督徒打交道;然而,塞尔修斯和波菲利却明智地忽视了它们。
除了关于基督教道德的虚假信息外,还有对基督教政治的误解。难道这个教派的经文不是预言罗马帝国将迅速灭亡吗?难道它不是预言罗马帝国将被上帝的统治取而代之吗?护教士们可能会解释说,他们所期待的王国是纯粹精神上的,但他们的话能被相信吗?基督徒的行为并不像忠诚的公民。基督徒拒绝在皇帝生日那天烧几粒香,在一般的异教徒看来,这必定是刻意在表达不忠,而且还很傲慢,就像在国歌奏响时拒绝起立一样。护教士们试图解释说,他们对国家象征并无不敬之意,他们很乐意为皇帝祈祷,并承认他仅次于上帝的地位。但这对群众和法律来说都不够。对现代学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只要有一点诚意就能达成合理妥协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基督徒表现出“不可战胜的顽固”,普林尼认为这种顽固是他们最令人反感的地方。无疑,他们的发言人觉得,即使是对异教崇拜最形式化的让步,最终也会导致基督教被无所不包的希腊-罗马异教吞噬和消化,就像其他的东方宗教被吸收那样。塞尔修斯指责他们“与世隔绝”。塞尔修斯还埋怨道,在帝国面临蛮族严重威胁的时刻,基督徒逃避作为公民的职责,他们拒绝服兵役,甚至拒绝承担民事职务。俄利根的回应是,基督徒通过祈祷对帝国所做的贡献胜过那些“看似在战斗的人”,这很难让普通民众信服;他声称基督徒通过服务于教会来服务社会,这样的观点更加令人不安心。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教会的立场被它自己的追随者所迫。基督徒也需要谋生:俄利根的和平主义是不切实际的,特土良的严格主义更是如此,后者会导致基督徒被排除在许多职业之外,甚至包括教学。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至少在第3世纪初,就已经有基督徒在军队中服役;到了这个世纪末,基督徒的数量多到让戴克里先感到有必要进行一次清洗。到了波菲利的时代,针对基督徒不够爱国的指控已经过时了,而且显然被抛弃了。
更加持久的,同时也——因为不那么理性——更难根除的原因是,认为基督徒要对每一次自然灾害负责的观念:他们的“无神论”冒犯了众神。特土良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诙谐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台伯河淹没了城镇,或者尼罗河没有灌溉农田,如果天空静止不动,或者大地震动,如果发生饥荒,如果瘟疫流行,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拿基督徒去喂给狮子!’”在整个第三世纪,当灾难频发而救济措施不足或根本没有时,基督徒成为了压力重重的政府的方便的替罪羊。在公元235年,小亚细亚的一系列地震引发了当地的迫害;在公元248年,甚至人为引起的灾难——内战——也被一些人归咎于基督徒;大约在公元270年,波菲利将在罗马频繁发生的瘟疫与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后来,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也用类似的指控支持他的迫害活动。有时,过错被归咎于基督徒的魔法:如果占卜出了任何问题,就说是某个基督徒通过秘密地划十字架的符号破坏了仪式。奥古斯丁引用了一句流行的说法:“多亏了基督徒,干旱还在持续”。
另一个引起不满的理由,虽然最近的学者很少强调,但无疑同样重要,那就是基督教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像所有要求个人完全忠诚的信仰体系一样——例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共产主义——早期的基督教是一种强大的分裂力量。尤西比乌说,每个城镇和每个家庭都被基督徒和拜偶像者之间的“内战”而分裂。游斯丁讲述了一位基督徒妻子被她的异教丈告发的故事;特土良提到有妻子因改信基督教而被休弃或儿子因成为基督徒而被剥夺继承权的案例;在佩尔佩多亚描述她与父亲关系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个家庭如何被宗教分歧撕裂。对于这样的情况,责难自然落在了基督教传教士身上。塞尔修斯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虽然太长不便引用,讲的是基督徒如何拉拢异教徒的孩子,鼓励他们违抗父亲和学校老师,诱骗他们参加基督教的秘密集会;他们经常也对妇女施展同样的招数。俄利根并没有否认这类事情的发生;后来耶柔米(Jerome)也描绘了一幅同样不利的画面,即狂热的僧侣们如何渗透到贵族家庭中,利用妇女的负罪感(传教)。基督教,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总会在家庭种制造麻烦。
然而,在如此强大的偏见的重压之下,基督教依然生存下来并传播开来。我稍后将提到一些有利于其发展的因素。但首先,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在饱学之士的水平上的对话,这样会比较方便,在这个层面上,尽管双方互相谩骂,但仍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理性辩论。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涉及的问题远比我在这里能提到的多;但主要的议题并不是现代基督徒会想到的那些。首先,这不是一场一神论与多神论之间的辩论。有人不无道理地认为,塞尔修斯信奉的一神论比俄利根信奉的更加严格,他肯定认为,基督徒把另一个存在与至高神并列在同等地位,这样的做法亵渎神明。诚然,他自己保留了一种残余的多神论:他认为我们也应该尊重次等神或亚神,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和部下。但俄利根也相信,上帝雇用“看不见的农夫和其他统治者”,并且这些存在不仅控制着“土地的产出,还控制所有流动的水和空气”,从而取代了异教的丰饶之神。他也像几乎所有的基督徒一样,相信异教神灵的真实性和力量;他只是把正号换成了负号——它们不是神,而是恶魔或堕落的天使。俄利根的世界里充满了大量的超自然存在:每个民族,如同每个个体一样,都有一个好的天使和一个坏的天使。在波菲利的世界里,也有类似的各种生物混居的情况,他说,基督徒称他们为天使;我们称他们为神,因为他们接近神性——但为什么要为一个名字而争执呢?他同塞尔修斯一样捍卫民间向这些超自然存在献祭的习俗,他称其为“善意和感激的象征”,但这并不构成他个人宗教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唯一真正的献祭是灵魂与至高神的独处交流。关于这位至高神的本质,异教和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之间也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上帝是没有实体的、无情、不变,并超越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极限,这是塞尔修斯和俄利根共同的观点;他们都抨击普通民众将神人格化的观念。不同的族群用不同的名字称呼这个神;根据异教思想家的说法,这也只是一场词语之争。这样一个神会以人的形态出现并遭受俗世的羞辱,对异教徒来说自然是不可理解的。为了应对这种诘难,俄利根和护教士们都淡化了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一面,而是强调他是某种希腊化过的“第二位神”,即永恒的逻各斯,那个上帝创造和统治宇宙的代理。在这一时期的宣传中,耶稣的人类特质和在凡间遭受的苦难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戏份;在面对异教徒的批评时,这些都令基督徒感到尴尬。
同样,这场争论也不是基督教的严格主义和异教的放纵主义之间的较量。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代中,基督教伦理和柏拉图主义伦理并不容易区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两者来说,理想的目标都是“向神同化”;两者都关注个体灵魂的救赎,而非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通过比较基督教版本和异教版本的《塞克斯图斯格言集》(我在第一章提到过)中的格言,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有多少共通的实用训诫。塞尔修斯认为基督教伦理平庸陈腐:它们“没有令人印象深刻或新颖的教导”;关于转过另一边脸给人打的建议实在是老生常谈,柏拉图的表达则更好。俄利根本人对此也并不否认:他说,区别在于基督教传教士是在“为普罗大众烹饪”,而柏拉图则对同样的菜肴加以调味,以取悦上流社会人士。他对柏拉图的钦佩丝毫不亚于塞尔修斯;但只有有学问的人才会读柏拉图的著作——他似乎有时暗示,基督教是面向大众的柏拉图主义。
在公元2世纪,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异教徒如果被要求用几句话来解释他自己的世界观与基督教世界观的区别,他可能会回答说,这是“理性思考”(logismos)与“信仰”(pistis)的区别,即有理有据的信念和盲目的相信之间的区别。对于任何接受过古典希腊哲学教育的人来说,“信仰”意味着最低级的认知:这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们根据道听途说相信事物,而不能给出他们相信的理由。另一方面,圣保罗遵循犹太传统,将“信仰”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基石。让所有早期异教观察者(包括琉善、盖伦、塞尔修斯和马可·奥勒留)感到惊讶的是,基督徒完全依赖未经证实的说法,他们愿意为不可证实的事物而赴死。相对来说,盖伦是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观察者,在他看来,基督徒具备四种主要美德中的三种:他们展现出勇气、自制和公义;他们所缺乏的是“实践智慧”(phronesis),即理性的洞察力,这是其他三种美德的理性基础。对于塞尔修斯来说,他们是科学的敌人:他们就像那些江湖郎中,警告人们不要去看医生,说知识对灵魂的健康有害。随后,波菲利似乎也对这种“非理性和未经检验的‘信仰’”提出了同样的批判;而尤利安则感叹道:“你们的哲学除了‘相信!’这个词之外,再无其他了”。但到了波菲利的时代,尤其到尤利安的时代,情况已经从两个方面发生了改变。
首先,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基督徒现在已准备好提出有理有据的辩驳。那哥拉已经认识到“理性思考”的必要性;俄利根准备逐点反驳异教徒,为此他从希腊哲那里借来了所有可以用于武装自己的武器。他对纯粹的“信仰”的蔑视几乎不亚于塞尔修斯。他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它对大众有用处”,这是能够为他们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因为一部分是由于生活的需要,一部分是由于人类的弱点,很少有人热衷于理性思考”。他接着指出,异教徒并非总是基于纯粹理性来选择他们的哲学。
事实上,虽然俄利根和他的后辈们正努力用理性来弥补权威的不足,但异教哲学却反而越来越倾向于用权威取代理性——这种权威不只限于柏拉图,还有俄耳甫斯诗歌、赫尔墨斯的神智学,以及像《迦勒底神谕》这样的晦涩启示。普罗提诺拒绝接受这类启示,并给他的学生们布置任务,叫他们去戳穿它们;但在普罗提诺之后,新柏拉图主义转变了,与其说它是一种哲学,不如说它是一种宗教,其信徒像基督徒一样,忙于阐释和调和神圣的经文。对他们来说,“信仰”也成为了一项基本要求。波菲利在晚年将“信仰”作为灵魂接近神的首要条件,“因为我们必须“相信”(pisteusai),转向神是我们唯一的救赎”——没有这种信仰,我们就无法达到真理、爱或希望。在普罗克洛斯的著作中,也有几次将“信仰”与真理和爱联系在一起。有些人认为这是在有意地借鉴基督教,但我自己更愿意将其视为一句古老而真实的谚语的一个验证:“我们变成我们所憎恨的模样”。如果要在平等的条件下对抗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就必须成为一种宗教;而没有任何宗教能够摒弃“信仰”——《迦勒底神谕》和《赫尔墨斯文集》中的一些篇章已经对这种信仰有所要求。
早期的护教士们很少谈论耶稣的人格或救赎的教义。相反,他们主要依赖于两项论证:神迹论证和预言论证,现代的继承者大多已经放弃了这两个论证。当然,他们是在效仿《新约》作者的做法。但神迹在各种异教崇拜的宣传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古代关于神迹的论战主要是两种不同信徒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信徒与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令现代读者感到好奇的是,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里,双方都不准备言之凿凿地声称对方的神迹是虚构的。最早的护教士,夸德拉图斯(Quadratus of Athens)认为耶稣的治愈神迹比异教的神迹更胜一筹,不是因为它们更真实,而是因为它们更持久,似乎早期的基督徒,像优秀的医生一样,会跟进他们的病例。即使俄利根也没有否认在埃及的安提诺乌斯(Antinous)圣祠发生的神迹,他认为这些奇迹是由于“一个恶魔在那里”,并得到了“埃及魔法和咒语”的帮助。他更经常向读者提供替代观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迹治愈和阿波罗女祭司的神启很可能不是真实的,但如果是真实的,那就是由恶灵引起的。俄利根没有办法对神谕持完全怀疑的态度;尤西比乌可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通过酷刑从官方先知那里得到了欺诈神谕的供词。异教的立场非常相似。对于塞尔修斯来说,《新约》中的神迹是“怪诞的故事”,但即使它们是真的,也不能证明耶稣的神性,就像埃及魔术师的做法一样,它们可能只是“被恶魔附身的邪恶之人的行为”。波菲利承认,基督徒“通过他们的魔法艺术表演了一些神迹”,但补充说:“表演神迹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阿波罗尼乌斯和阿普列尤斯(Apuleius)以及无数其他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行神迹并非难事”(Non est grande Jacere signa),在一个所有人都相信魔法的世界里,神迹既司空见惯,同时也在道德上很可疑;它们可以用来打动大众,但基于它们的论证不可避免地是双刃剑。
在游斯丁的著作中,预言论证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俄利根也反复强调。塞尔修斯在回应中指出,《旧约》中的预言含糊其辞、笼统不清。但毕竟他对《圣经》的了解有限,俄利根能够指出他遗漏了重要细节。波菲利则是一位更强劲的对手。作为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他擅长批判文献证据,对新旧约了如指掌,并且比俄利根更了解希伯来语。塞尔修斯满足于泛泛而谈,且往往缺乏深入了解,而波菲利则处处引用《圣经》文本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以学者的志趣,揭露福音书作者对希伯来先知的错误引用,指出不同福音叙事之间的矛盾,并戳破圣保罗前后不一之处。他也有学者典型的缺点:有些批评过于细枝末节,比如他抱怨“加利利海”不是海而是湖,因此不太可能遭遇风暴;另一些批评则显得粗俗、缺乏想象力,比如他说他无法理解天国如何可以被比喻成一粒芥菜种。但在他最好的状态下,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批评家。他利用朱拜勒的斐罗(Philo of Byblos)来核实《旧约》的历史陈述,并且他在合理的历史依据上将《但以理书》的年代推定到安条克·伊皮法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时期,这一点预见了现代学者的观点。事实上,就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将历史批评的规则用于《圣经》的人。
在基督教这一方,这场对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是俄利根在《论第一原理》中所做的宏大尝试,即试图将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融合在一起。我在此无法充分阐述这本杰出的著作,但即使是快速的浏览也足以显示他对异教观点的让步是多么深远。他不仅(正如我们所见)接受了柏拉图神学的实质内容,还接受了柏拉图式的世界观。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由逻各斯维持并保持其存在,其功能类似于柏拉图的世界灵魂。在宇宙中还有许多其他生命体,包括星辰,它们本身就有灵魂,它们可能为某些人类灵魂提供未来的归宿。宇宙确实有一个开端,也将有一个终结,但之后会有一系列其他世界相继出现:因此,复活被贬低为宇宙历史中的一个插曲;最终的“万物复归”(apocatastasis),即所有事物都回归其原始状态,则是无限遥远的。
《论第一原理》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心理学,它更接近普罗提诺而不是圣保罗。灵魂不仅在后世是永恒的(a parte post),在生前也是一直存在的(a parte ante),并且也不仅仅是通过神的恩典,也是通过其本质属性。它确实是一个受造之物,但正如在普罗提诺的理论中,它的创造本身是发生在时间之外的。每个灵魂最初都是纯粹的智慧体,每个灵魂最终都将恢复到这种状态。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必须经历多次飞升和堕落,在救赎这场竞赛中,每个人的起跑线都并不相同,如果想要将神圣正义(divine justice)的观念与这个事实相调和,就只能假设我们在前世犯下的罪行对这一世有影响。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升华到天使的地位或堕落到魔鬼的地位;俄利根肯定也考量过柏拉图的这一观点:即灵魂可以转生为动物。在转世之间,其命运取决于它在人世间所过的生活。恶人将遭受涤罪过程(purgation),但这不是永恒的,因为神圣的正义总是纠错性的,而不是报复性的。地狱并非永恒的烈火,而是一种心灵的状态,它代表了俄利根所谓的“灵魂因缺乏凝聚力而招致的惩罚和折磨”。善良的人将在人间的天堂居住一段时间;在那里,上帝将为灵魂设立一所学校,由天使教导,他们将为灵魂解答他们在人世间的所有困惑。俄利根提供了一份课程大纲,灵魂最终将接受考核;通过者将被提升到更高的领域修习更高级的课程:天堂是一所永无止境的大学。在这种状态下,灵魂将被赋予新的身体,它由比我们更精细的物质构成,但随着它们通过各个领域上升,这些身体将逐渐脱落(异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最终的状态可能会是无实体的,圣保罗所说的“灵性的躯体”只是一个暂时的折衷。
这种对《新约》基督教的大胆改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巧妙地运用了历史悠久的寓言式解读法。这种扭曲文本的艺术最初是为了从荷马史诗中读出深刻真理而发明的,长期以来一直在亚历山大港被使用:犹太人将其应用于《旧约》,诺斯底教派将其应用于《新约》;克莱门特和俄利根又先后从他们那里传承了这一方法。对于富有思辨精神的人来说,想要摆脱字面意义的专制,这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尽管它在缺乏历史真实性这一点上已经无药可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却是一种进步的工具。塞尔修斯已经注意到,“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中,更理性的人以寓言的方式解释这些事情”。他指责他们滥用这种方法,波菲利后来也提出同样的批判。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者们的立场站不住脚,塞尔修斯和波菲利自己也曾使用同样的方法在荷马史诗中寻找柏拉图主义。基督徒和异教徒同样都生活在象牙塔里,他们无法挑战古代文本的权威;他们只能通过将自己的思想回读到这些文本中来规避这种权威。
当俄利根撰写《论第一原理》时,基督教的末世论观念仍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而且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如此。近两个世纪后,两位基督教主教,辛奈西斯和尼梅修斯(Nemesius),仍然可以宣称相信灵魂的预先存在;前者仍然可以质疑躯体的复活和宇宙的最终毁灭。甚至在俄利根离世一个多世纪之后,圣洁的贵格利仍然可以拒绝永恒惩罚的观念,认为所有灵魂最终都会恢复到它们原初在天堂一般的状态。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最后一个观点未能被教会接受似乎是一场重大的历史灾难。但圣经的权威过于强大。经过三个世纪的争论,在公元543年,查士丁尼一世在一道敕令中几乎将俄利根的所有创新都贬斥为异端。为西方基督教划定未来方向的,不是俄利根,而是奥古斯丁。尼尔森哀叹教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不仅抛弃了晚期异教的迷信,还抛弃了“古代科学的坚实内核”。然而,人们可能会质疑,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内核到底还能不能被拯救?在公元4世纪,异教似乎是一具行尸走肉,国家一旦撤回对它的扶持,它就开始崩溃。即使尤利安能多活一阵子来执行他的复兴计划——即将神秘主义和布道相结合——也很难相信他的尝试能够取得任何持久的成功。活力已然消失,帕拉达斯代表最后几代受过教育的异教徒说道:“如果我们还活着,那么就是生活本身已经死了。”基督教成功的一个原因仅仅是对手的虚弱和疲惫,异教既失去了对科学的信心,也失去了对自身的信心。
另一方面,基督教被认为值得为之而活,是因为它被视为值得为之而死。很明显,尽管琉善、马可·奥勒留、盖伦和塞尔苏斯自己不情愿承认,但他们都被基督徒面对死亡和酷刑时展现出的勇气所打动。这种勇气必定是许多皈依的起点(贾斯汀的皈依就是一个例子)。从现代政治殉难的经验中,我们知道,殉道者的鲜血确实是教会的种子,只要这种子落在适宜的土地上,并且不是播撒得太密集。但在基督教统治下的异教殉道者很少——这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更加宽容,而是因为那时的异教已经贫乏到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
当然,基督教成功还有其他原因。我不会讨论基督教信条的内在价值;但我会在本章结尾简要提及一些有利于其发展并促成其胜利的心理条件。
首先,基督教的排他性——它拒绝承认任何其他形式的崇拜的价值——在今天通常被视为一种缺陷,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一个力量之源。在希腊和罗马,宗教宽容是常规的政策,但是,这种做法所累积起来的大量选择反而令人感到困惑。有太多的宗教、太多的神秘仪式、太多的人生哲学可供选择,你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将一种宗教保险叠加在另一种宗教保险之上,但却仍然没有安全感。基督教彻底扫清了这一切。它从个体的肩膀上卸下了自由的重担:仅此一个选择,一个再也无法回头的选择,通往救赎的道路从此变得清晰了。异教批评家可能会嘲笑基督教的不宽容,但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任何“极权主义”的信条都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我们只需要想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共产主义对许多迷茫的灵魂的吸引力,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
其次,基督教对所有人都开放。原则上,它不做社会区分;它接纳体力劳动者、奴隶、被社会排挤的人、有前科的罪犯;尽管在我们探讨的时期内,它发展出了一个强大的等级结构,但其等级制度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开放的职业发展机会。最重要的是,与新柏拉图主义不同,基督教不要求受过教育。克莱门特可能会对单纯的信徒(simpliciore)的古怪信仰付之一笑,俄利根可能会宣称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只限于“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但是,“在侍奉上帝中获得认可,获得荣誉”(正如阿瑟·诺克(Arthur Nock)曾表述的那样),这一观念原本是与基督教精神格格不入的,而且总体上保持如此。在公元2世纪甚至3世纪,基督教教会仍然是一个主要(尽管有许多例外)由失意不得志之人组成的队伍。
最后,在一个世俗生活越发不值得留恋、负罪感普遍存在的时期,基督教向失意的人群承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将能过得更好,当然,这个承诺是有条件的。它的一些异教对手也提供了类似的承诺。但基督教挥舞着更大的棍棒和更诱人的胡萝卜。它被指责为一种操弄恐惧的宗教,无疑,在严格主义者手中确实是这样。但它也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希望的宗教,无论是在帕皮亚的语言粗糙的描述中,还是在克莱门特和俄利根提供的理性化版本中。波菲利曾评论说——正如后来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只有病态的灵魂才需要基督教。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代,有太多病态的灵魂,佩雷格里努斯和阿里斯提德斯并非奇葩的个别案例;波菲利自己也曾病到考虑自杀,有证据表明,在这几个世纪里,许多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迷恋死亡。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殉道的机会——带来今世的名声和来世的幸福——只会增加基督教的吸引力。
但是最后,成为基督徒的好处不仅限于来世。作为一种社区,基督教团体从一开始就比任何伊西斯密教或密特拉信徒的相应团体更完整地实现了社区的意义。它的成员不仅通过共同的仪式联系在一起,还通过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正如塞尔修斯敏锐地察觉到的)通过他们共同面临的危险联系在一起。他们迅速地为被囚禁或处于其他困境中的弟兄姐妹提供物质帮助,这不仅在基督徒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证实,也在琉善(一位对基督徒并无同情的见证人)的作品中得到了证实。爱邻如己并非基督教独有的美德,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基督徒似乎比任何其他群体更有效地实践了这一美德。教会提供了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面:它照顾寡妇、孤儿、老人、失业者和残疾人;它为穷人提供丧葬资金,在瘟疫时期提供护理服务。但我认为,比这些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社区能给予的归属感。现代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对归属感的需求”的普遍性,以及它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人类行为,特别是对在大城市中无依无靠的居民而言。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古代情况会有所不同:爱比克泰德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置身在人群之中可能感受到的那种可怕的孤独。这种孤独感必定被数百万人体验过——城市化的部落民、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民、退伍军人、因通货膨胀而破产的食利者,以及获释的奴隶。对于身处这种境况的人来说,加入基督教社区可能是维持自尊并赋予生活些许意义的唯一方式。在社区内部,有人间的温情,有人关心他们,无论是在眼前还是在来世。因此,基督教最早和最显著的进展是在像安提阿、罗马、亚历山大港这样的大城市中取得的,这并不奇怪。在更深层次上,基督徒是“同气连枝”(members one of another)的:我认为这是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决定性最强的一个原因。
原文注释
第四章
-
拒绝《约翰福音》,见伊皮法纽的《驳异端》,第51章,第3节;接受赫马,见爱任纽的《驳异端》4.20.2;见俄利根的《论第一原理》,4.2.4。参见尤西比乌的《基督教会史》,第3章,第25节,和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在《新约圣经的起源》(Origin of the New Testament)(英译本,1925年)中的讨论。重要的是,到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的末期,圣约翰似乎成为最受推崇的福音书作者。他的道成肉身(Logos)的学说吸引了哲学家们:普罗提诺的学生阿梅利乌斯(Amelius)引用了它并大加赞赏(根据尤西比乌的《福音的准备》(Preparation for the Gospel),第11卷,第19章,第1节);一位被奥古斯丁引用的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约翰福音》开篇的词句“应该用金字书写,并悬挂在所有教堂的最高处供人阅读”(《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第10章,第29节)。
-
这一点在最近发现的一封克莱门特的书信中有所提及:参见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Early Christianity and Greek Paideia)(1962年),第56页和第132页。参见塞尔修斯的说法:一些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地篡改福音书的原文,改变其性质,以便在面对批评时否认其中的难题。”(《驳塞尔苏斯》,第2章,第27节)
译后记
“亚神” vs. “精灵” vs. “半神” vs. “天使”
在第二章开篇中,作者引用《会饮篇》时,将一个关键的希腊词汇译作“daemon”,这个词在现代英文中已经被简化为“demon”,而且,多数情况下它表达的是负面的含义,通常被译作“妖魔”,但是其古希腊词源则并非如此。对于这个词汇的翻译,我不得不考虑两点:1. 它在《会饮篇》和本书中的含义是指神明和凡人之间的存在,而且负责为两者的沟通传递信息;2. 我们需要一个跨越宗教和文化的词汇,来让读者不至于得到远比原意更为狭窄的解读。
从协调沟通的职能的角度讲,“天使”确实很适合,但是它局限于犹太-基督教的背景;从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存在等级来讲,“半神”似乎更贴切,但是他局限于古希腊的宗教神话,而且源自一种多神论背景(柏拉图的语境则是暗示只有一位至高神),而且通常是指神明与凡人交合之后诞下的混血,这类角色在希腊神话中也被称作“英雄”;“精灵”符合超自然力量高于人类又低于神明的设定,而且这个词有一定包容性,因为它既是对北欧神话中的“elves”的翻译,也是对阿拉伯神话中的“genie”的翻译,但是它的灵活性也仅限于此,依然有很强的背景暗示。
最终,我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亚神”,用来表达原文“daemon”所表达的含义。